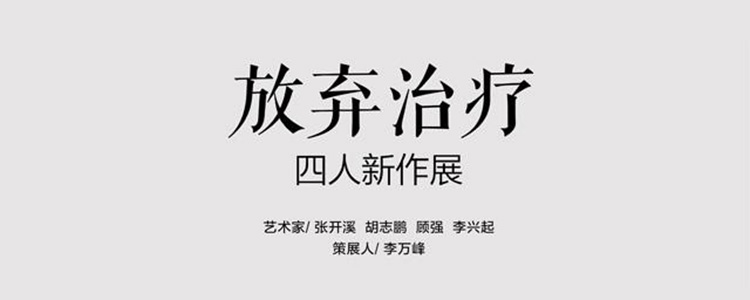
在图像的一亩三分地,深耕细作不免是产出好东西的前提。与普通意义上的耕种不一样的是,如果说艺术家种出宝石才算数,但从来就没有宝石的种子。
艺术家有的是电子媒介对人性的合围、伦理塌陷过程中的道德困境、再也无法对想象力供血的被过度认知了的存在,有的是虚荣和妄念对个性的干扰、私密空间遭到的彻底侵犯,有的是正确的风格、漂亮的理论和愚蠢对自由的保驾护航,但从来也没有产生宝石的地质条件以及漫长的时间。
所谓艺术品,就是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玩意儿。一个人挥掷完天赋和光阴,能问心无愧就很不容易了,何况违背造物的意思,当真搞出什么名堂来,不竭尽全力又如何可能呢。
这次“放弃治疗”的四个人,在我的观察中,算得上孤注一掷的艺术家。他们或许有各自的方式和主张,但呈现出来,却有同样的笃定气息。他们否认既有的美学,又恬不知耻地使用其中的技巧,以嘲笑甚至蔑视来对待前辈的经验和自身的经验,又持续关注始终在这里面进行的微妙变化。他们的作品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承认自己全部的可笑之处,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些作品并非创造力的集合,而是力所不逮的整体,给出的希望都带着分崩离析的绝望气质。
以前我说张开溪“有意识地放大某种以美好为底色的丑陋,任由无限膨胀的欲望继续无限膨胀,把现代社会所有虚弱不堪的东西归结到他的色彩里头。同时他也在祝福,态度暧昧,他所捍卫的写实得到了平静的绚烂和略显迟疑的旁观者的节奏,用一种不可能的方式给人以尊严,迫使我们回味无穷并且看见自己。”
说得比较含糊。张开溪建构了独特的否定的螺旋,可能他看不上的东西海了去了,不如此难以说服自己。虽然我相信他仍然心存软肋,但他的画面中确实没有。他倒是有浅薄的地方,过分地执迷于有关世俗和集权的恶趣味。他最近的一张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又把暧昧给弄清晰了,把所有人都当做一个人来表现,去除外在的差异,揭示当代人本质的相同,感叹个性产生与存活之艰难,却又不着力于这一点,让力量指向四面八方,探讨的问题之繁复,以至于他自己可能也无法悉数罗列,然而如实拿出了厌恶与悲悯共同作为主要构成的态度。
相比之下,胡志鹏作品中的桎梏要多一些,在往常,理性压制了某些更重要的内容,如《饕餮盛宴》时期,就为了让自己的作品不可能被挂在客厅里面,这么一个执着而悲情的理由,反而失去了对生命魅力的多维度采撷。事到如今,又要在作品中逐一反对经过艰深学习得来的经典套路,以完成崭新的画面,非壮士断腕般的决心不能为之。
同样用一张作品来说明,胡志鹏的《幸福》做到了真正的开拓。首先是整体不知名的绚烂,其次是对笔触的全盘否决,顺便玩了一把童真。绚烂从何而来,我们可以归功于色彩,却不能把色彩当做唯一甚至重要的原因。关键在于艺术家本人得到解放,蓬勃的精神和战斗意志随即起了作用。
至于笔触,纯属技术(媒介)而非情感的范畴,在虚弱和不真诚的气氛之下,很多画家喜欢以此来做支撑,为自己一无所有的画面增添一点合法性。胡志鹏深知自己之前有些沉迷于技术,不惜矫枉过正,也要跟陈旧的至少于他无用的东西划清界限。这个决定无论是怎么下的,哪怕艺术家自以为剑走偏锋,其产生的事实无疑具备充分的说服力,接续了艺术的正道。
童真的可贵不在于对童真的模仿,在于对童真的使用。胡志鹏直接把颜料挤在画布上,是为了以此解决自身的问题,绝非强调这就是价值所在。这个作画过程仅仅让他可以单纯地思考而已。所追求的越来越少,自然是一个艺术家趋于成熟的标志。
顾强当得起才华横溢这几个字,之前几年的作品就呈现了各种强烈而有针对性的风格。假如放在北京,大概随便一种也就勉强够用了,但因为偏安一隅的关系,在成都,艺术家的时间好像要充裕些,可以多想想自己真正的潜力在哪儿。一经推敲,结果确实比较遗憾,顾强之前的各种风格于他本人而言,大概都是不成立的,所见多为妥协和服从,作品并没有充分地与他的个体生命发生联系。
我们最缺少的当然还是个人主义。现在对于年青一代人格与思想的独立,不少方家都有盲目乐观的趋向,把狭隘和表面化的态度当作从核心涌出来的真实。殊不知年青一代在里子几无改变的情况下,反倒以为自由已经水到渠成,不必做太多思考,不必怎么争取就可以坦然享用。艺术家更应该警惕这一点,从尽可能多的角度琢磨自身的症结所在。顾强正是借此发力,在画布上只做单纯的工作,拿出了《园中的果树》这样的作品。
并不经典的构图,色彩不讲究,题材不新颖,细节也说不上精彩,但《园中的果树》偏偏营造出了鲜活的气氛,情感充沛,意义模糊,并且有稍微做了些隐藏的病态,同时饱含艺术家对生命的误解——是笨拙而非聪明,在我们的语境下,可怕的恰恰是正确和聪明。顾强以一己之力,向我们呈现了艺术不可言说的部分。
而李兴起则重新声明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没有能力向大自然学习,到了一定程度后,甚至无需向大自然学习。李兴起就是李忠,云南人。他以前画了一些山,最近画了一些树,比如《三棵树》《一棵大树》等等。看上去是丢不掉前青春期的生存烙印,无法从以旧物给回忆立传的老腔调中脱离出来,实则李兴起并没有在画面中流连往日的世界,而是以探讨生命关系为出发点,重申创造力的贫乏与光荣。其贫乏在于,艺术家终究难与造物匹敌,特别是在目前普遍的混沌状态之中,李兴起直接承认了个人的欠缺,以真诚去做了些经营。
创造力之光荣则被忽视已久。当我们谈论李兴起的树,与谈论一棵长在家门口的树,其实没有本质的不同。人为的图像同样可以作为事实被传达,可以交流,可以作为自然存在的替代品,甚至优于自然存在,可以容纳更为壮阔的欲望和荒芜。这个维度正好可与人性遭摧毁的过程相呼应,无论李兴起的情感倾向如何,都无改其作品的意义。
2016.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