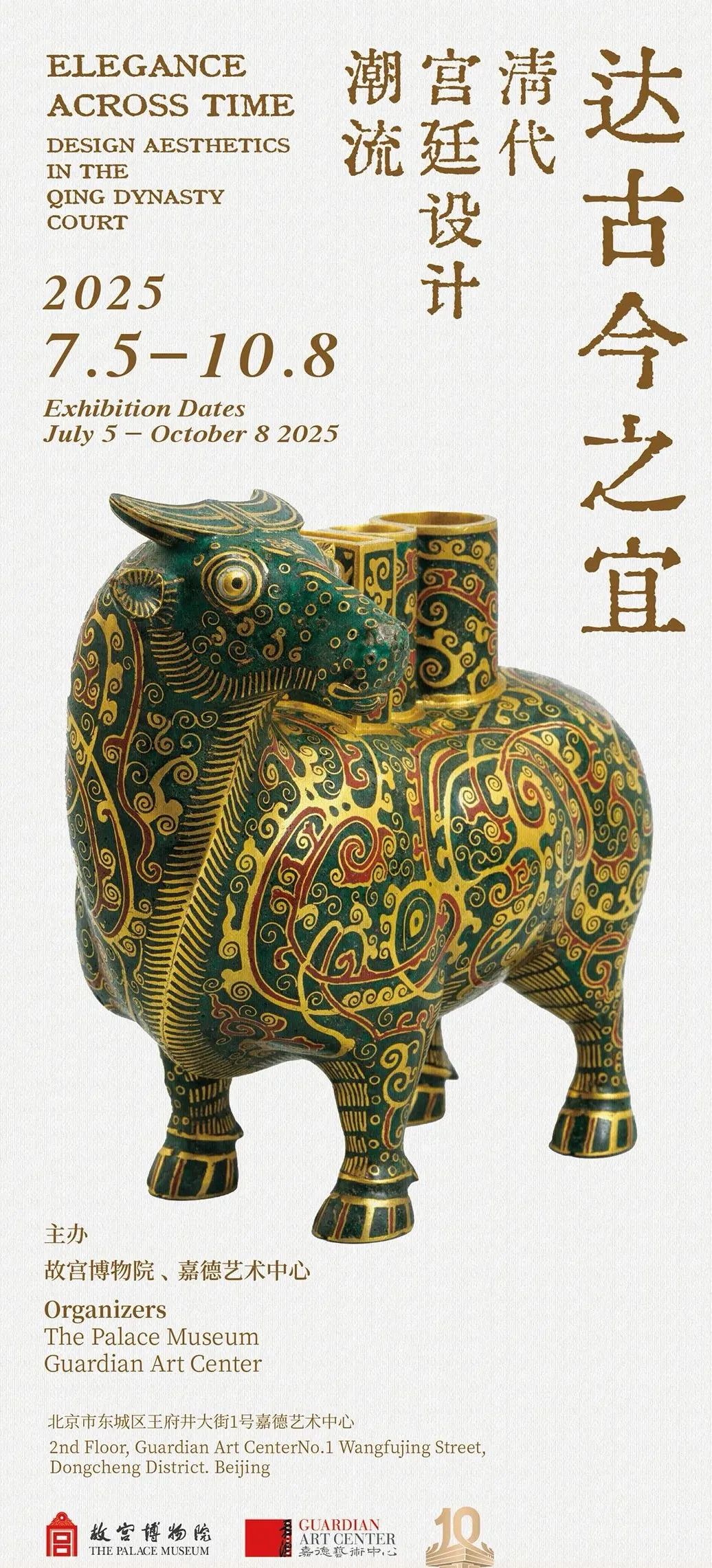艺术对我来说与其是体现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情结。当我从受艺术教育到自由创作时,自然溯源记忆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片刻。最早的记忆推到三岁多,记得在一九七六年的春天,妈妈要走长途去父亲船队停靠的地方,要走几十里毛马路,由表哥护送,挑着箩筐,一只箩筐里放着冬瓜南瓜,另一个箩筐里放着我。拖拉机擦筐经过发出震耳的轰鸣,把我从昏睡中惊醒。山与山之间引水的石拱桥下飞跨天穹。经过采石场,我们提前被吆喝留步,而后耳闻爆破声,看见惊鸟一样飞翔的石块,最后是石块不断下落的撞击声。我不知道这印象多少是缘于目击还是依赖后来想象的介入,以及格物式一次次重新审思。拖拉机、毛马路、采石场构成的原初震撼在二00六年的某一天才得用油画、水墨、诗歌回应,从相逢到表达三十年过去了,而后不觉画了二十年,经过打石场、桃花源,城市。或在一只青蛙的视角从一片萝卜叶下窥见飞驰的拖拉机。从春日开到冬日的雪原,或在黑夜中独行。或冒着白烟在青山绿水之间驰骋,一群穿背心的少年追随着它,"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要去哪里。”
上一篇: 塑形:手指证件照
下一篇: 古妙方新——当代书画名家题拓展

最新展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