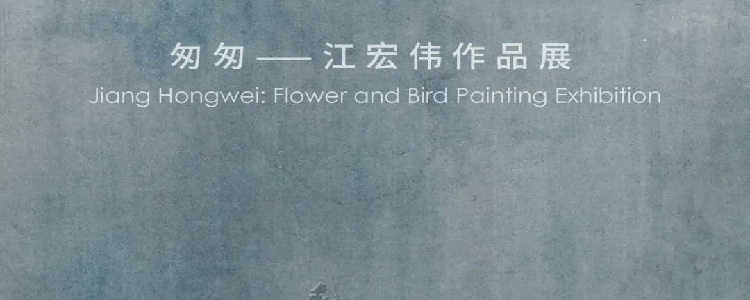
江宏伟的生活极为单纯,画画、游泳、见见朋友。一根烟、一杯酒,他的笑声爽朗而坦诚,时不时杂着些睿智的金句。虽然在北京退了休,他却很少北上,只是在南京的宅院中,守着花开花落之间的岁月荣枯。二十多年前我在南京读书时,也时常这般地在他家中,看他画画,并一起感知窗外的时光流逝。彼时,他的年龄如我之今日,而我则是二十出头的小伙。转眼间,那段金陵往昔已然远去。世事沧桑而人事纷杂,花荣月缺而聚散离合。然而,江老师的心境,却似乎一直未曾改变。面对窗外倏然而过的繁华与萧瑟,他依旧如故,伏案勾填,在一笔一痕的“劳作”中,体察并表述着他捕捉到的片刻流光。
或许因为这一点,有人习惯以宋画为参照,来阅读他的作品。确实,说起感知自然的执着与专注,他与宋人极为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就是宋画的延续。记得多年前,我俩在谈别的事时,他曾说“一代人糊一代人的墙”。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自己与不同年龄段画家的差异,更为具体的所指已经记不清了。不过这句话,似乎也可以解释他与宋画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是糊墙,手法与方式却截然不同。不谈笔线造型,单就对色彩的理解,他和宋画就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宋画没有调和色的概念,因为那时候没有西画,更没有印象派,而江宏伟成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者在中国恰是风头正健。
今天回望八十年代,很容易带着一种滤镜——剔除它的问题,然后用怀念的腔调娓娓道来,仿佛天然具有一种煽情的基因。但即便如此,今天的我们还是可以煽情一下,怀念那个时代的自由与开放。彼时美术界,在关乎形式美的激烈争论中,悄然告别了艺术服务政治的绝对话语。一时间,以语言自觉为代表的形式现代性,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方向。本该1930年代就在中国开花的印象派、后印象派,沉寂了半个世纪后,突然又火热起来。梵高的精神病,成为一种神话,更是激励了一代的艺术青年。他们不留个长发,不搞些与众不同的事情,都不好意思说是艺术家。于是,叛逆成为他们的青春话语,哪怕有些不明就里,也必须如此。一夜之间,那些曾经伟光正的主题叙事,在他们眼中成为俗不可耐的革命对象。毫无疑问,形式的美学独立,正是他们最为重要的武器之一。而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更是连印象派都一跃而过,直接拥抱了波洛克的抽象。
显然,那时的江宏伟,不属于冲在最前的激进青年。对形式独立的美学意趣,也似乎并非他主动思考的内容。但不可怀疑的是,身处那个狂飙突进的岁月中,仍然年轻的他,绝不会绝缘于现代性的诱惑。彼时,与南京最拉风的青年大咖朱新建的交往,抑或正是生性有些内敛的江宏伟,与时代激浪对接的端口之一。于是,因为老实接受学校安排的印染专业课程而画工笔花鸟的江宏伟,并没有沿着陈之佛的脚步亦步亦趋。在那个充满急剧变革的时代,他看上去选择了一个保守的方向,却也不安分于“过去”。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种艺术史现象,即一个时代的伟大变革,绝不仅仅表现为那些紧扣时代命脉的显性革命,也体现为那些看似游离革命浪潮的隐性变革。江宏伟,正如此。在不为“前卫”所看重的画种里,以常人难以体察的细节之变,呼应了时代变革的内在逻辑。或许,如此之变,比显性革命更为困难,犹如在细微的音阶变化中演奏出跌宕的旋律。
庆幸的是,江宏伟不仅是一个细致入微的人,还是充满耐心与定力的人。面对身旁潮起潮落的时代波澜,他一头扎入自己的“小水塘”,一点一滴地寻找着属于他个人的视觉配方。一遍一遍地尝试,在画脏了的画面上用水洗,调出心仪的色彩再一次覆盖,甚至用木板的纹理介入视觉语言的生产。身处八十年代那个日新月异的激荡岁月中,他躲在黄瓜园的宿舍里,默默面对自己的“残纸剩色”,有些孤独却也自在。终于,一种特殊的“宋画”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并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美术界引发关注。之所以说是特殊的“宋画”,是因为它看似延续了宋画察物的传统,却与“宋画”相去甚远。江宏伟的画面并非一种纯色,而是类似于印象派的灰色调性——在细微的关系中营造氛围与气息。这种并非中国传统的色彩感觉,被包裹在了看似传统的意趣与味道之中。将他的画与于非闇等二十世纪工笔画家比较,这种独特性显而易见。
今天,重新审视这种差异,我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八十年代的时代律动,对于青年江宏伟的影响:他从语言入手的视觉改造,恰是八十年代形式美讨论所带来的一种关乎现代性的理解方向;他流连于西方色彩观所带来的全新感官,正是八十年代的开放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一种全球化景观。虽然,他不曾站在时代的风头浪尖,却始终保持了一种敏感的开放性。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对艺术史研究而言,预设的逻辑框架,往往让我们习惯将目光投诸断裂式的振臂一呼。殊不知,历史真正的脚步,却时常隐匿在看似平静的角落中,细水涓流地日夜奔流。对今日之中国而言,尤为如此。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身负五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将以怎样一种方式融汇进全球化的时代命题,是值得我们反思并期待的。显然,狂飙突进的颠覆与瓦解,并不适用。那么,在开放的框架下重新理解自身,似乎成为一条无法回避的道路。艺术的选择,亦然。或许,这也是生活在这一特定时空的我们,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之一。
对此,江宏伟似乎不愿从理论层面加以回答。他看重的,是自己一笔一划的绘画行为。一起聊天时,他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手艺人。表面上看,这是谦虚,其实却是针对空洞化理论表述的骄傲。不过,无论他承认还是不承认,从八十年代一路走来的他,上述理论话语并没有远离他。当不满足于陈之佛、于非闇等前辈画家的表达方式时,他就开始了答案的寻找。从一张《百花图卷》到莫兰迪,江宏伟在多元化的视觉凝视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选择。或可以说,既不算封闭也不算激进的南京,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接触大时代的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如,面对窗外的岁月枯荣,他一方面倾心投入,体察那白驹过隙的时光幻化;一方面却又始终不喜不悲,置身事外。他的事业,是笔下的一花一叶,没有追赶潮流的时尚话语,只有内心的坚持,竟然也就逐渐地那般荣辱不惊了。
于是,宅在庭院里的江宏伟,抽抽烟、游游泳,见见朋友,不管窗外的时风骤变、山旗幻灭,他依旧十数年如一日地伏案观景。从某种角度看,他的窗户离这个世界很近,却又永远保持着那份距离。这不仅是他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艺术立场。
或许因为这一点,有人习惯以宋画为参照,来阅读他的作品。确实,说起感知自然的执着与专注,他与宋人极为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就是宋画的延续。记得多年前,我俩在谈别的事时,他曾说“一代人糊一代人的墙”。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自己与不同年龄段画家的差异,更为具体的所指已经记不清了。不过这句话,似乎也可以解释他与宋画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是糊墙,手法与方式却截然不同。不谈笔线造型,单就对色彩的理解,他和宋画就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宋画没有调和色的概念,因为那时候没有西画,更没有印象派,而江宏伟成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者在中国恰是风头正健。
今天回望八十年代,很容易带着一种滤镜——剔除它的问题,然后用怀念的腔调娓娓道来,仿佛天然具有一种煽情的基因。但即便如此,今天的我们还是可以煽情一下,怀念那个时代的自由与开放。彼时美术界,在关乎形式美的激烈争论中,悄然告别了艺术服务政治的绝对话语。一时间,以语言自觉为代表的形式现代性,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方向。本该1930年代就在中国开花的印象派、后印象派,沉寂了半个世纪后,突然又火热起来。梵高的精神病,成为一种神话,更是激励了一代的艺术青年。他们不留个长发,不搞些与众不同的事情,都不好意思说是艺术家。于是,叛逆成为他们的青春话语,哪怕有些不明就里,也必须如此。一夜之间,那些曾经伟光正的主题叙事,在他们眼中成为俗不可耐的革命对象。毫无疑问,形式的美学独立,正是他们最为重要的武器之一。而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更是连印象派都一跃而过,直接拥抱了波洛克的抽象。
显然,那时的江宏伟,不属于冲在最前的激进青年。对形式独立的美学意趣,也似乎并非他主动思考的内容。但不可怀疑的是,身处那个狂飙突进的岁月中,仍然年轻的他,绝不会绝缘于现代性的诱惑。彼时,与南京最拉风的青年大咖朱新建的交往,抑或正是生性有些内敛的江宏伟,与时代激浪对接的端口之一。于是,因为老实接受学校安排的印染专业课程而画工笔花鸟的江宏伟,并没有沿着陈之佛的脚步亦步亦趋。在那个充满急剧变革的时代,他看上去选择了一个保守的方向,却也不安分于“过去”。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种艺术史现象,即一个时代的伟大变革,绝不仅仅表现为那些紧扣时代命脉的显性革命,也体现为那些看似游离革命浪潮的隐性变革。江宏伟,正如此。在不为“前卫”所看重的画种里,以常人难以体察的细节之变,呼应了时代变革的内在逻辑。或许,如此之变,比显性革命更为困难,犹如在细微的音阶变化中演奏出跌宕的旋律。
庆幸的是,江宏伟不仅是一个细致入微的人,还是充满耐心与定力的人。面对身旁潮起潮落的时代波澜,他一头扎入自己的“小水塘”,一点一滴地寻找着属于他个人的视觉配方。一遍一遍地尝试,在画脏了的画面上用水洗,调出心仪的色彩再一次覆盖,甚至用木板的纹理介入视觉语言的生产。身处八十年代那个日新月异的激荡岁月中,他躲在黄瓜园的宿舍里,默默面对自己的“残纸剩色”,有些孤独却也自在。终于,一种特殊的“宋画”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并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美术界引发关注。之所以说是特殊的“宋画”,是因为它看似延续了宋画察物的传统,却与“宋画”相去甚远。江宏伟的画面并非一种纯色,而是类似于印象派的灰色调性——在细微的关系中营造氛围与气息。这种并非中国传统的色彩感觉,被包裹在了看似传统的意趣与味道之中。将他的画与于非闇等二十世纪工笔画家比较,这种独特性显而易见。
今天,重新审视这种差异,我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八十年代的时代律动,对于青年江宏伟的影响:他从语言入手的视觉改造,恰是八十年代形式美讨论所带来的一种关乎现代性的理解方向;他流连于西方色彩观所带来的全新感官,正是八十年代的开放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一种全球化景观。虽然,他不曾站在时代的风头浪尖,却始终保持了一种敏感的开放性。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对艺术史研究而言,预设的逻辑框架,往往让我们习惯将目光投诸断裂式的振臂一呼。殊不知,历史真正的脚步,却时常隐匿在看似平静的角落中,细水涓流地日夜奔流。对今日之中国而言,尤为如此。无论是主动抑或被动,身负五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将以怎样一种方式融汇进全球化的时代命题,是值得我们反思并期待的。显然,狂飙突进的颠覆与瓦解,并不适用。那么,在开放的框架下重新理解自身,似乎成为一条无法回避的道路。艺术的选择,亦然。或许,这也是生活在这一特定时空的我们,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之一。
对此,江宏伟似乎不愿从理论层面加以回答。他看重的,是自己一笔一划的绘画行为。一起聊天时,他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手艺人。表面上看,这是谦虚,其实却是针对空洞化理论表述的骄傲。不过,无论他承认还是不承认,从八十年代一路走来的他,上述理论话语并没有远离他。当不满足于陈之佛、于非闇等前辈画家的表达方式时,他就开始了答案的寻找。从一张《百花图卷》到莫兰迪,江宏伟在多元化的视觉凝视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选择。或可以说,既不算封闭也不算激进的南京,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接触大时代的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如,面对窗外的岁月枯荣,他一方面倾心投入,体察那白驹过隙的时光幻化;一方面却又始终不喜不悲,置身事外。他的事业,是笔下的一花一叶,没有追赶潮流的时尚话语,只有内心的坚持,竟然也就逐渐地那般荣辱不惊了。
于是,宅在庭院里的江宏伟,抽抽烟、游游泳,见见朋友,不管窗外的时风骤变、山旗幻灭,他依旧十数年如一日地伏案观景。从某种角度看,他的窗户离这个世界很近,却又永远保持着那份距离。这不仅是他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艺术立场。
杭春晓
2022年6月27日于后沙峪
上一篇: 周岩:欹梅
下一篇: Downsizing·平行世界的我——Zoe微缩摄影个人展

最新展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