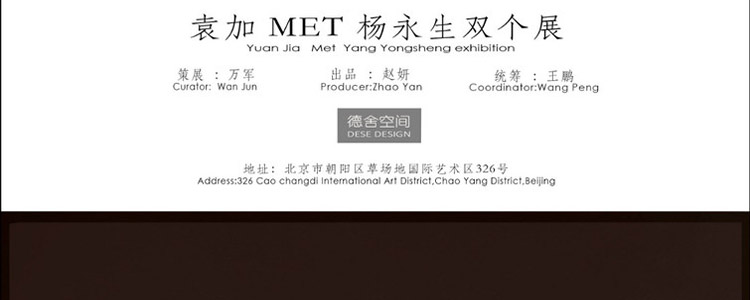
像陶渊明一样画画
杨永生
2003年我稀里糊涂的考上中央美院第一届博士生,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上博士对我的艺术道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本是一个读书不多的人,读书少的原因是读书需要大量的时间,画画也是需要大量时间,理所当然我就把时间让位给了画画。并且当年画画的氛围也是强调感受和激情,对理论不屑一顾。读博士被迫需要读很多书,写很多文章,这样硬着头皮慢慢的读了一些书,读多了渐渐地也开始享受起读书的快感。
读书潜移默化影响了我对绘画的思考,我开始在绘画里寻找绘画的根源,这样不知不觉走向“仿古”的道路。刚开始我把画的题目都起为“向大师致敬”,就是改编大师的作品。彭峰老师看到我的画跟我开玩笑说,你后现代啦!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并不是后现代。
我是用了后现代拼贴改编的因素,但我完全没有在画面里嬉戏,而是想从画面里找到出处,就像写文章要找到出处,就像明清大师绘画都是要根据前人的绘画画自己的作品,也就是仿的概念。
我“仿”不限于西方或中国,只要是我感兴趣的经典都想去仿。我在2008年画过《西山行旅图》系列,就有仿国画古意的味道,只是当时没有那么明确的目标和思路。2015年左右明确了“仿”的概念。当代艺术家做“仿”的也不少,尤其是仿古画意境的,我非常不喜欢。很多艺术家都直接照搬古代画面的元素,更拙劣的是在自己画里画古人,穿着长衫,梳着发髻,牵着白马。最后把色调画成褪色的、偏色的,好像这样就追随古意了。当然我也不知道怎样“仿”才是对的,但我认为我们永远都无法再回到过去了,古人的心境、气质如果真到现在的话也应该是改变的,我觉得应该按照延续的方式进行“仿”。
今年本想着到山里去写生,“仿”古人山水画来着,没想疫情这么严重哪都去不了,干脆就在画室里画静物,也就算是仿古人的“花鸟”吧。疫情让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自己在画室里画静物颇有躲在世外练功的感觉。陶渊明是古人出世追求田园生活的代表,其实无论古今,无论是谁,都有一处自己内心深处的“桃花源”。像陶渊明作诗一样画画,其实也是每个艺术家内心深处的追求,我的梦想也是像陶渊明一样画画。
过去在绘画上特别重视自己的“当代性”,强烈的个人风格,拒绝中庸。随着心境的改变,画画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现在越来越不在意自己是否当代,是否有风格。我必需承认风格是一个艺术家至关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当代艺术家。但我现在认为比风格更加重要的是全神贯注地观察事物的本身,耐心地观察对象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块物质质感的不同,时间凝聚在物体上的固化。
我想只要你画的足够的好,绘画本身会超越表现形式。就像你在看梵高画的向日葵,透过弯曲的笔触和跳跃的色彩,你看到的还是向日葵本身。宋代的绘画,画面可能只有一只小鸟,不看签名我们很难认出这是出自哪位画家之手。但小鸟表现的生动的劲,让你忘记关于这幅画本身之外的其它一切东西,忘记了风格,甚至忘记这是一幅艺术品,能感受到的就是画家专注的精神。当达到这种专注度的时候,就无关形式和内容了,眼前一切皆可以来表现,这时,我认为绘画超越了表面的风格,这就是一个画家对世界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