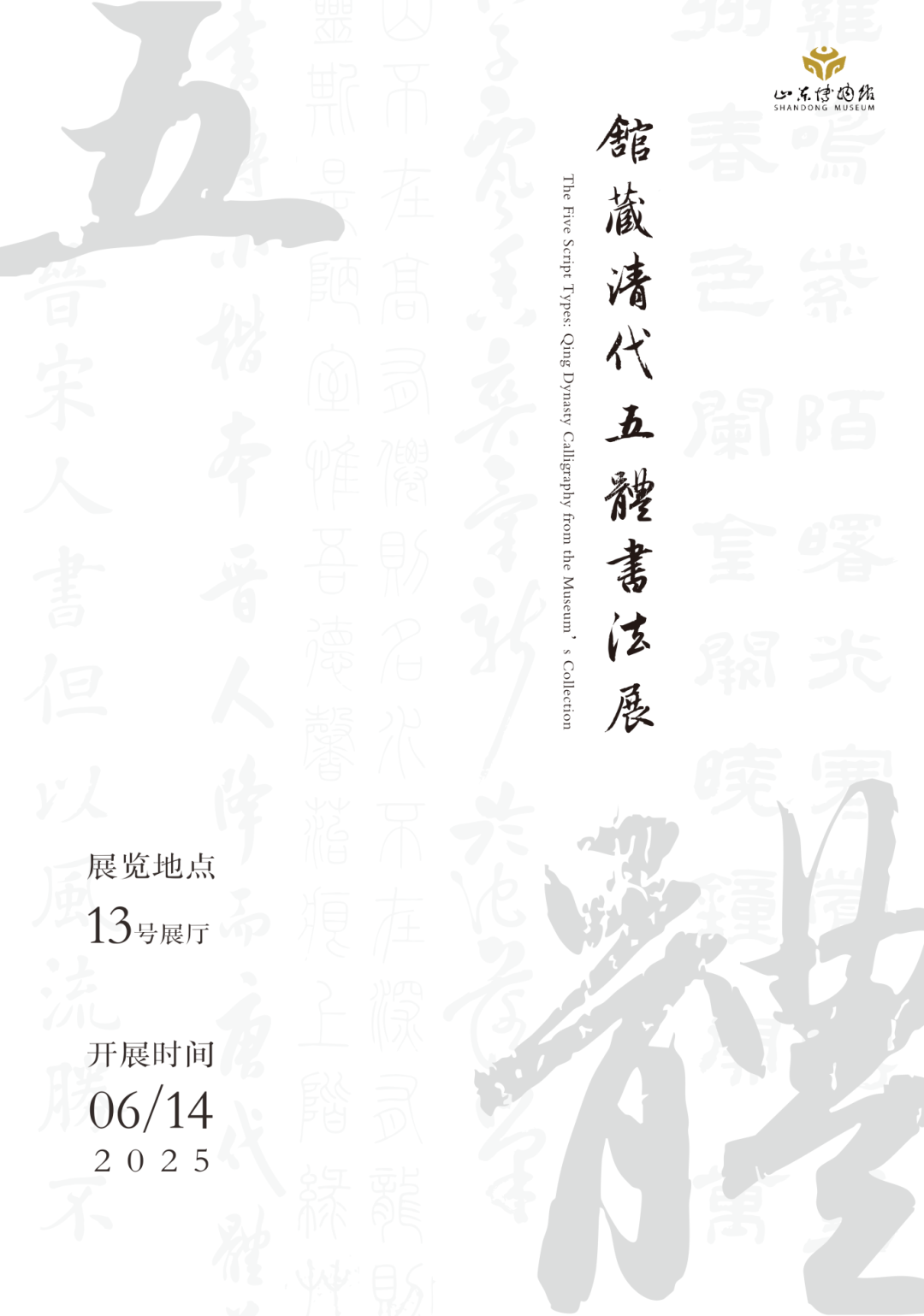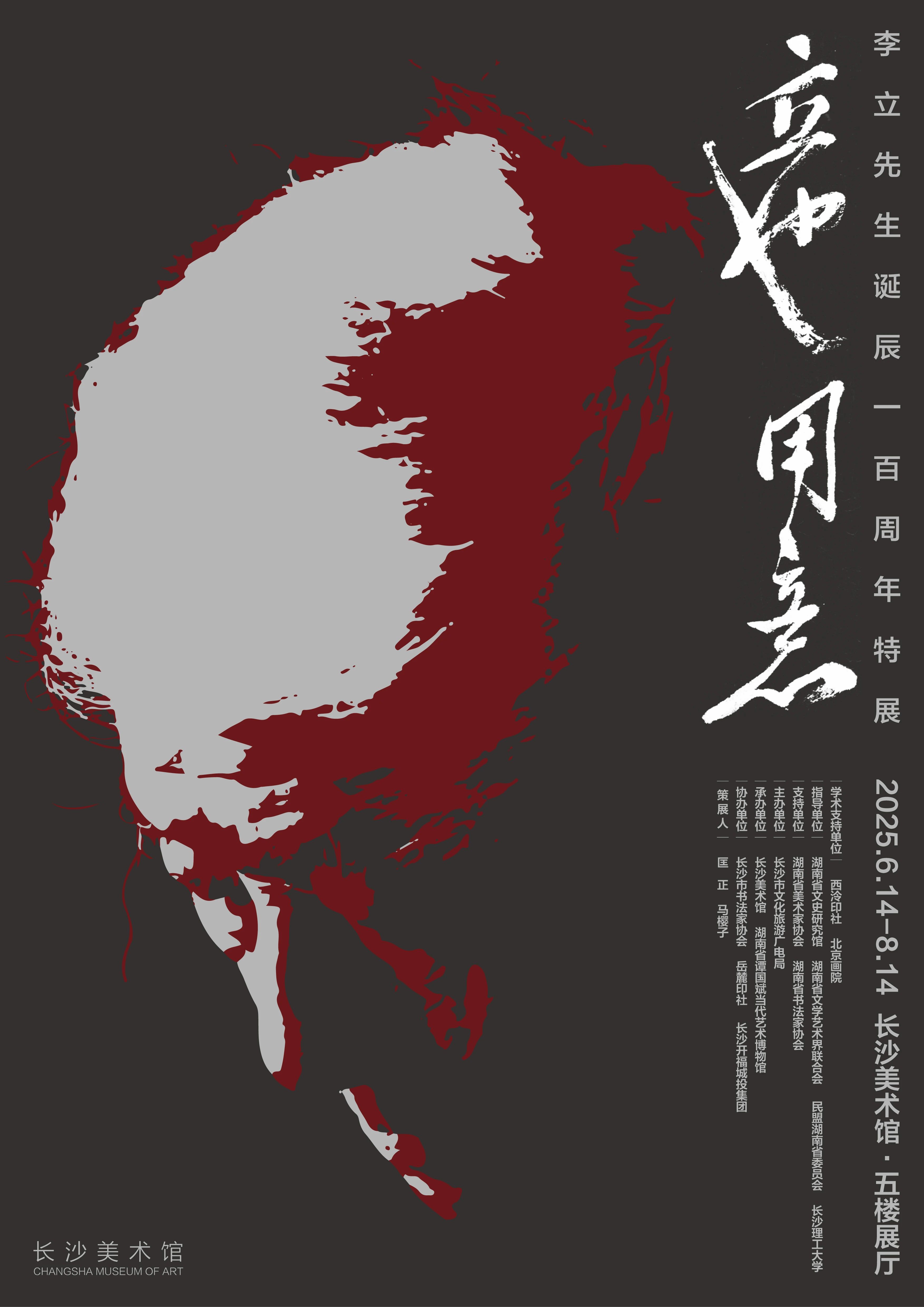唐意胡风的冠冕
文:小巍
艺术家李晶彬虔诚于传统绘画线条的一颦一笑,又或是一嗔一怒。毛笔的痕迹在传统纸材上婉转自如,蓄含谨严,倏或如一首线条谱就的优美乐章,发丝与衣褶之间,节奏和韵律在灵动地流淌,起承转合,百转千回。
小唐人系列的新作,延承了艺术家年年嗜有新意的初心。大块富丽华美的青绿色和胭脂,还有金粉若隐若现的点缀,更加对比了黑白灰各种墨色的宁静,浓淡疏密,你侬我侬。既是对传统工笔绘画的强大的艺术表现力的传承,也是对水墨趣味的礼赞。
现世的满足和对美好的憧憬。
小唐人的意旨在于为古是新,古典元素极巧妙地营造出空灵飘逸的现代气质。古意褪去沉重,笔简意巧的小唐人终是现代的。
逍遥的供养
文 小巍
初春的季节,李晶彬从印度回来,朋友圈里几次被要求讲一讲在那个神秘又奇葩的国度里最有趣的见闻。他每一次都提到那个国家里令他无数次动容的印度式的微笑。他说无论在城市、在乡村,贫富贵贱,男女老幼,随处都绽开的笑颜,既不是粉饰太平,也没有特意掩盖他们的喜怒哀乐。印度人在信仰中获得尊严、自足与活着的希望,多了今世的几分洒脱。微笑的印度人安贫乐道,活得逍遥自在。
再然后是看到了这几幅《逍遥游》。云龙宣纹路极白,纹理飘逸生动,透纸欲出。画中的线条想象着是从吴道子到陈老莲的手中,从敦煌的洞窟到永乐宫墙壁上,饱蘸墨汁的笔尖,或灵巧或敦实,提按、行顿、转折、轻重、疾徐,于是乎线条长短、粗细、简繁、疏密、浓淡、虚实、交错、顾盼、呼应,一根根错错落落,简简单单又气象万千。几只大鸟,是不是庄子笔下的大鹏鸟?有一只已经飞到半空了,身后是若隐若现的浮云,淡墨轻染勾勒,仿佛刚刚飘过来。阿睹朝天,脱却了现世的嘈杂和羁绊,是玩腻了蝉翳叶的顾恺之还是更加逗比的王子猷,赤了脚,羽化了大罗神仙?
逍遥,对于大鹏鸟可能是着了明亮的青绿色九万里的高空。对于凡人,这是一如既往的难得企及的境界。当我们熙熙攘攘,或为利来或为利往,或纠结于身前身后名,少了一份真正说服内心的神往和笃定,如何还能创造出一个超越的世界,获得那一份逍遥自在呢?印度人却是有逍遥的。逍遥是一份神往,更是一份笃定。是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是对来世的真诚向往。定是受了那里的感染,画家从《魏晋风流》的士子嬉笑怒骂、放浪形骸里看到了神来神往,也让人窥见这温润玉质的水墨世界原来就是他的逍遥游了。
借花
文 李晶彬
谈女人,这是个让人有些畏惧的事。我总觉得,人生的终极问题除了那三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第四个便是男人和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两个都撞在地球上,好像火药味十足。所以,我总觉得这是个挺大的问题。
好在这个展览的问题不是谈男人与女人,而是男人眼中的女人、是男艺术家眼中的女人。
女人这个问题上艺术家似乎有一种默认的特权,特别是男性艺术家,那个她是他永恒的话语主题。
虽然如此,还是完全脱不开男人和女人。男女彼此是有间隔的不太真切的彼岸。古人说: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两者之间要么是现实,要么是神话。人是活在现实中的,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女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人。
我们的时代女子比较流行审美“女汉子”,独立以及独立带来的压力、困境使然。过得慢慢的古人,还在那里合香、女红。很慢,很慢,所以采荇菜的淑女,只“窈窕”二字,“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女人是男人的一切爱意。那个时代的男性视角的美人是女为悦己者容,男人回报她为士为知己者死。
男性艺术家的角度却可以更跳脱:可以更审美,可以更欣赏。
但现实中男女之间,难免恩怨情仇。遇到了,已有了半腹旧情,难割舍。而这个时代男人往往认为女人是近于完美的,而女人认为女人往往是不情愿于完美的。男人看来女人未免矫情,而在女人看来男人辛苦卓绝的还远远不够。
古代女子以秀发相赠, 笃定情长,剪下一缕青丝当做信物赠给情人时,她并不知道那丝丝缕缕最终缠住的只是自己。木心说,那个时代,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
其实艺术只是复写之后的复写。艺术家只不过在青山四起之中,烟云如目而已。那个佳人在水一方, 朦胧、飘逸,可望而不可及。
美人自美,如花自香。
《簪花仕女图》的仕女还在调胭脂,辛夷花还在角落里花儿自开花自落。
我们只如一个借花人,临走留下一张泥金纸笺,而花于我,则缀我衣裳,簪我发旁。
女人是男人最终的港湾,哪怕她只是波提切利画笔下维纳斯足下巨大的海贝。
她也是唐伯虎的桃花庵: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令我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些《诗经》中的女子。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有这样一群无邪的、自然的、舒展的女子。
晏叔原的《长相思》说: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
一转眼,悠悠已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