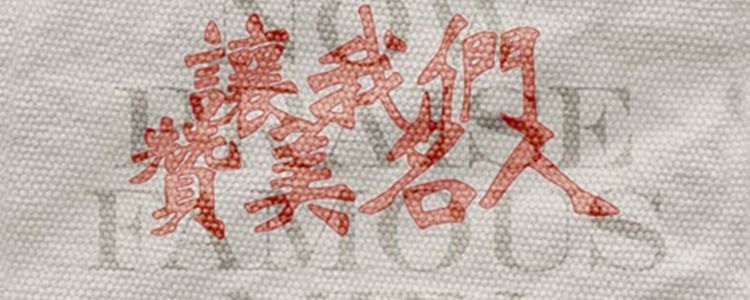
摄影家任曙林的《先进个人》系列拍摄于1977年初。当时他是位于永定河畔的北京第二机床厂铸造分厂机修车间的维修钳工。因为爱好摄影,所以工厂里的宣传部把拍摄1976年度先进生产者肖像的“任务”交给了他。据他回忆说,他在拍摄这批照片时,想要以照相馆的拍摄方式来完成任务。因此,他在拍摄时煞有介事地模仿、践行照相馆的人像美学。尽管设备简陋,任曙林仍然试图以戏剧性的用光为先进生产者们造像。他搞到了两个灯,把光线分成最基本的主光与副光。从现在的照片看,他的这批照片至少在用光方式上受到了照相馆美学的影响。
完成拍摄后,这些照片经过裁剪,在去掉了简陋的背景布的破绽后,放在工厂区里的宣传橱窗里展出。据他说,少有拍摄肖像的机会的先进生产者们,对于自己以如此隆重的方式上墙,还是兴高采烈的。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工厂里的“名人”,而且是大家身边的“名人”。他们的形象在工厂里的公共空间供大家观看,起到一种激励作用。而这种激励渗透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在每天去食堂的路上,在上下班的路上,在去另外的车间或科室办事的时候,他们都有可能与这些身边的“名人”形象接触。不但如此,他们也有在生产活动中实际接触这些“名人”的机会。
任曙林当时没有办法像照相馆那样修涂底片,对人物形象进行修描。因此照相机镜头的不讲情面,在任曙林的照片里得到充分反映。工人们饱经风霜的面孔与粗糙的皮肤得到了纤毫毕现的展示,而后面背景布的起伏褶绉,在丰富了画面肌理的同时,也与脸部的纹理相互映衬,构成一种丰富的视觉对比。而工人们的复杂表情,反映了他们与摄影这一观看方式的紧张关系。对于当时的工人来说,摄影仍然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事物,他们不会放松自如地面对照相机镜头。从照片看,他们的表情,或紧张、或惶恐、有时努力维持平静,有时显得老练,但也不时流露某种尴尬。这些先进生产者们,有的一望而知来自农村,与宣传中的“工人阶级”形象大相径庭,有的形象比较洗练,城市化程度较高,有的更有知识分子气。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事是,当时毛泽东逝世不久,在他们的表情中,还含有一种作为时代遗孤的惶然若失的神情。他们的表情都没有通常宣传摄影与宣传画中的所见的那种高亢,形象也显得普通而又平凡。
于是,特定的时代因素、设备的简陋、摄影的观看特性、工人与照相机的关系等几个因素的复杂纠结,结果,任曙林实际上不自觉地拍摄了一批实际上是反英雄(没有蓄意美化对象)、反戏剧性(也是反照相馆美学)的人物肖像。这些属于广义的“工人阶级”的人物形象,基本上无从反映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反而以某种摄影的真实呈现打破了宣传中的“工人阶级”的神话,还原了作为人的工人的真面目,而不是巩固有关一个阶级的已经破产的政治神话。
事隔三十年后,这批照片被任曙林重新整理并展出。不过,在展出时,他把底片的整个画幅全部放出,这样的处理,既包括了他对于这组照片的重新认识,也是一种对于集体记忆的清理,并给了我们以重新审视时代与照片中的人的机会。
美国艺术家、艺术评论家阿伦·塞库拉(Allan Sekula)曾经把肖像摄影分为“尊称的”与“压迫的”两类。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摄影作为一种布尔乔亚的肖像手段,就是为中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提出令人尊敬的形象,为提升他们的自信提供帮助。而作为一种社会调查与控制的手段,则是对于社会的无用者(如犯人、病人、外国人移民等)的形象记录与备案。
作为宣传任务,“先进人物照”就是要给出令大家尊崇的先进形象。拍摄者应该以影像中的人物肖像来提示影像外的人,这是一些比其他人“先进”了一些的人。他应该尽可能美化他的拍摄对象,以达成让众人尊崇的目的。但在那个时代,由于照相机仍然代表某种观看的习惯与特权,因此出于尊崇目的的拍摄结果对于他的同事们反而成为了一种压抑。任曙林的拍摄,既要努力遵守照相馆美学的规训(这没有做到多少)来尊崇他的伙伴们,又因为照相机的权力性的存在而令自己的伙伴们变得压抑。他的摄影,其实就反映了这么一种复杂的观看政治学。
与任曙林拍摄的身边的“名人”不同,艺术家周铁海绘制的“社会主义美人照”中的电影明星,可说是遥远的名人。
周铁海的这个明星系列的形象素材来源于电影杂志。1990年代末,周铁海在静安区万春街的工作室因为拆迁而遭毁灭。这时,他偶然发现邻居废墟里的一捆杂志。那是当时的《大众电影》杂志。这批杂志中的明星照片,唤醒了1965年出生的周铁海的青春记忆。陈冲、龚雪、刘晓庆、吴海燕、张瑜、李秀明、郭凯敏等曾经名满天下的电影明星,哪个不与当时的中国青年的梦想相联?而邓丽君的形象,则是樊篱之外的女神,体现了另外一种女性美学,也成为一时风骚。以机智地挪用现成图像而著称的周铁海,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批明星影像作为某个特定时代的一种梦想与美学趣味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他以他惯有的制图方式,重绘了这批以清纯为主要诉求的“社会主义美女照”(socialism pinup)。这既是把属于某个特定时代的大众集体记忆的回收,也是把凝聚于明星影像中的集体记忆的重塑与回放。
当代日本文化评论家、艺术史家多木浩二(Taki Kouji)在《美女照的修辞学》一文中指出:“不管是内容浓烈的还是稀薄的,社会上一般把作为娱乐而传播的情欲性的影像总称为‘美女照’”。
比对多木(Taki)的这个“美女照”定义,周铁海的作品显然有所不符,需要稍作修正。周铁海所依据的这批中国“美女照”的原形是电影演员照片,其生产(拍摄)、流通、接受与消费发生于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时代的末期。其时改革开放已经启动,社会也已开始向大众传播与消费社会迈进。但文化的生产、人们的审美意识等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毛泽东时代的影响。从当时生产制作的这类明星演员影像的目的看,似乎也就简单停留于电影宣传的层面,虽不乏打造明星之意,但囿于意识形态的钳制,还无法像今天这般明目张胆地实施明星包装与打造,只是简单地以演员照为幌子,扩大影片的影响,兼而传播演员的名声。照片的制作者所拍摄的不是如多木所说的“情欲性的影像”,而是反而把可能唤起情欲的因素加以过滤。从这些影像本身来看,煽动、撩拨情欲的成份也确实并不明显。当然,对于影像的接受者与消费者来说,是否视其为“情欲性的影像”与欲望投射的对象,那是各人自便。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星照片的拍摄方式可说是照相馆美学的极致。戏剧性的用光,柔焦、以及对于所有细节的控制(排除),使得照片成为了一种现实的真空。它们仿佛来自现实,但其实已经没有现实感。
不过,即使在照片制作当时还没有包装、打造、营销之说,但对于当时的大众来说,陈冲、张瑜、刘晓庆等也是遥不可及的名人。而飞速发展的中国现实,也令这些名人们迅即成为昨日黄花,在今天,那些影像也一并成为倾诉乡愁的对象。
周铁海的这批明星作品,是在这种性质的明星影像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再次加以打磨。虽然在拍摄时摄影师可能使用了柔焦手法,但经过周铁海的绘画处理,照相机镜头所具有的成像锐度再度柔软化。因此,他的这组作品,其实经过了两度打磨,一次是拍摄时的“去刺点”的摄影操控,经过这样的视觉卫生打扫,照片已然成为了空洞的物品。而当周铁海再次以喷笔将影像从纸张移植到画布上加以重新绘制时,图像本身又经历了一次打磨。经过这第二次打磨,画面气氛更其朦胧暧昧,人物形象显得更其飘忽,不可捉摸,越来越趋近于一种幻影式的存在。不过,经过周铁海的这次打磨,本来照片中相对低下的情欲性反而有所提高。我们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照片情欲度的提升似乎与影像的清晰成反比。在这里,他通过喷笔在弱化了照片的摄影性的同时,也通过这种处理使乡愁成为照片的主调。
任曙林与周铁海两人的作品,一个呈现身边的“名人”先进生产者,一个展示遥不可及的“社会主义美人照”中的电影明星,一个关涉理论上的领导阶级但实际上的社会大多数,一个有关身处社会焦点与公众关注中的大众名人,一个属于官式群众动员所需的非消费影像,一个属于大众文化生产一环的具消费性质的图像,一个属于某个阶级的集体记忆,一个属于消费大众的集体记忆,而这两类“名人”形象分别象征了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制像美学观的两极。因此,在表面上看,出自不同艺术家之手的人物肖像作品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是强烈的对立。但就是这两者的强烈的对立关系,在今天奇怪地构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的呼应关系,也形成一种美学上的张力。它们在今天都具备了一种历史的乡愁,一起成为了我们记忆的一部分,引人审视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而两者所唤起的乡愁的质地却有本质不同。一种以质朴见长,以可触性强烈的影像来引起乡愁,一种是空泛取胜,以光滑而无法深入的影像来诱发乡愁。但不管怎么样,作为时代的产物,这些肖像作品都负载了特定时代的信息与趣味,并且穿越时空,进驻当代生活的精神内存。
1936年夏天,美国摄影家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与作家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奉《财富》杂志之命,深入到当时经济大萧条重灾区的美国南方,寄居于三家贫苦农户家庭,展开拍摄与写作。其时正是罗斯福总统应对美国经济大萧条施行“新政”(NEW DEAL)之时。1941年,两人以《让我们现在就赞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一书出版。作为文学作品,此书现已成为“美国经典”(The American Classic)。而作为纪实摄影作品,埃文斯拍摄的美国农民照片也已有公论,同样成为经典。他们采用的这个书名,出典来自于被称为圣经外传的“德训篇”(Ecclesiaticus),他们借此表达一种对于权力与作为摄影的权力的质疑。阿吉认为基于报导的这个跨界作品,将成为“一个对于人类神性的某种标准的困境的独立质询。”(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certain normal predicaments of human divinity,此处英语原文只供翻译者用,不属于正文内容,不要刊出)他们通过自己对于农民的深入观察与描绘,将被人类历史所忽视的人抬升到“名人”的高度加以“赞美”。
虽然任曙林与周铁海的作品,与埃文斯和阿吉的作品相比,从出发点与制作目的看都不相同,但只是从他们制作(摄制与绘制)名人形象(无论是有名无实的“名人”还是真正的名人)看,他们的作品仍然具备展开质询图像生产机制、审视官式群众动员方式与大众文化生产方式的潜在可能。这种质询与审视也包括了将两组差异很大的作品以并置一堂的方式建立起展开某种更为深入的质询的空间的尝试。至于这种通过包括了并置展出两人作品在内的质询本身会激发什么样的思考能量,打开什么样的思考空间,我们更寄希望于观众与这些作品的独立对话。
顾铮
2009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