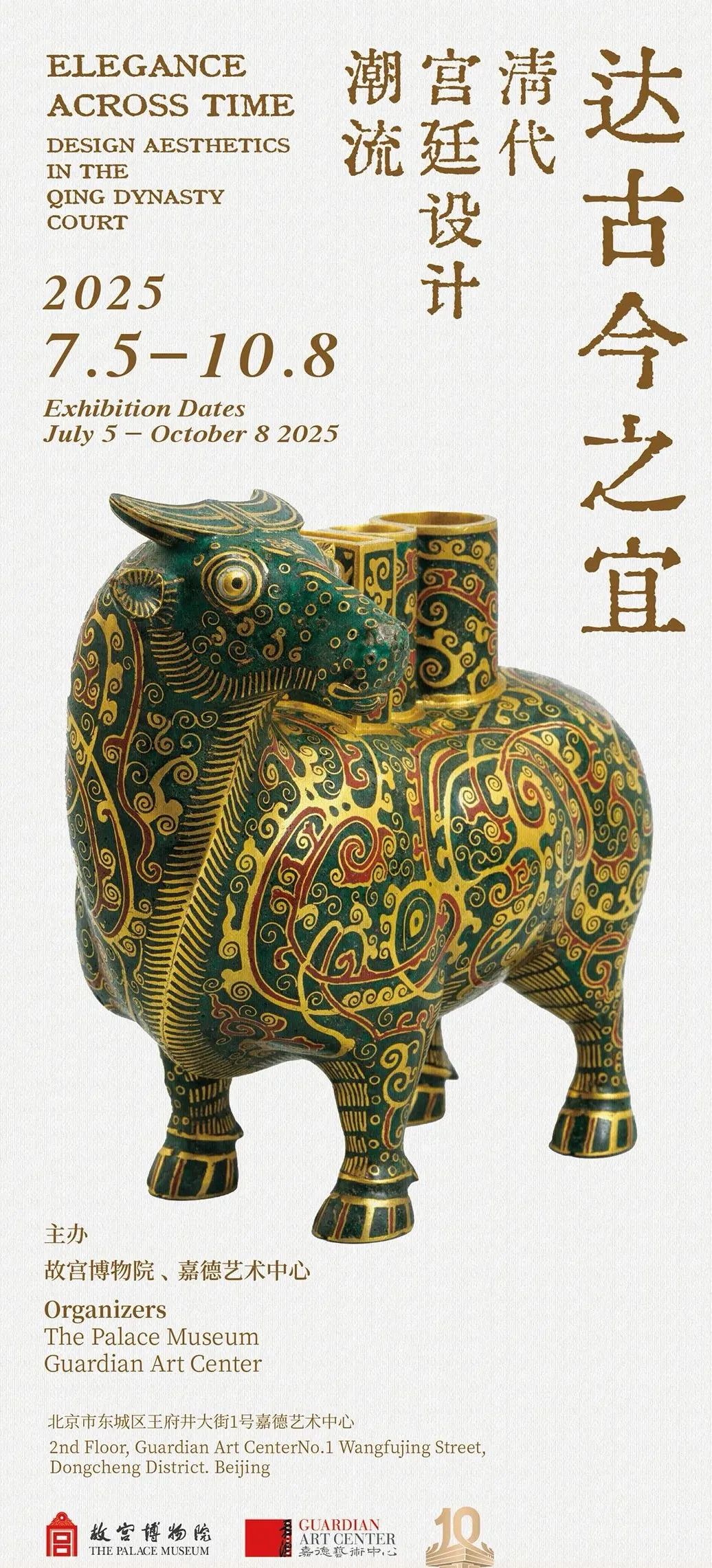前言
吴洪亮
这个展名为“缺题”,是个冲击力不会很强的展览。像梁铨先生以及他的作品,等待着历史的聚焦。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程而言,他从未缺席。他只是拒绝在漩涡的中心劲舞或是抢占风口去狂欢罢了,梁先生自有他的想法、节拍器与表达方式,这个展览在2 0 2 1 年于广东美术馆举行,可视为一例。
本次展览的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有题目,一类没题目。有题目的,在符合中国人对文字与绘画合一的想象外,酷,而有情;没题目的,冠以“无题”,按梁先生的老师赵无极的说法是想给观者更多理解的可能性。我却认为,这其实是梁先生给看画的人设了个迷局,同时也给自己建了道防火墙。这种直钩钓鱼的游戏,很久远。那年姜子牙7 2 岁,今年梁铨7 3 岁。至于展览的名字“缺题”又与“无题”稍有差异。“缺”并非等同于没有,仅是不求全,更具某些主动性。老子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引这么长的一段,其实只是想引出最后这一句:清静为天下正。艺术家不是统治者,他们的“天下”即是艺术。从这个角度讲,“清静”与“正”的关系,很像作为艺术家的梁铨,至少像梁铨所追求的。进而我们要感叹他的画如其名。梁是要有担当的,铨乃衡量。梁先生在自持的那份责任中铨衡与坚守。这种不妥协,导致在今天读懂他的人不会很多,就像梁先生说的:“其实不缺,但是总有人认为缺什么。”的确,这个门槛有些高,然而一旦跨过、读懂,便会爱得很深。如同梁铨爱那位曾经孤独的美国艺术家艾格尼丝·马丁。至于梁铨的作品,那些看似轻薄、平静的源自洗衣板的平行线以及淡淡的色块,仿佛端出一方“清静”的湖水。而此处的“清静”是如老子那样断然被表达出来的。再细读,它们的边缘常常是坚定甚至是锋利的,而内部是生动甚至激荡的。这种矛盾性的博弈,在梁先生的建构下达到了画面上恰切。我无须说那是对中庸的追寻,或是接近了所谓阴阳平衡。因为,这些都是内置于中国人基因中的东西,加之梁先生对2 0 世纪以来人类在视觉艺术研究成果的运用,乃至作为版画出身的他,都不是问题。故而,在此我也不想多谈所谓抽象、构成、拼贴以及在时代藩篱中的水墨画等问题。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从他的作品里,我们能感受到,梁铨对理性的追求本身依然是非常感性的。只有感性倾泻出来的东西才会有所谓真的禅意。作品传递得虽慢,但不滞,虽需等待或细纠,但必有可期的惊喜。仿佛淡墨在宣纸上渗开的过程,是自然而舒缓地扩散。其实,如在高倍放大镜底下,那状态的涌出也会像钱塘江潮一样浩荡。所有表面上的澹泊,恐怕是另一种强烈的苛求所致。
如前所述,梁铨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同行者,但并没有很多同道人。他从’85 新潮的杭州到美国,再回杭州,然后到北京看了一眼,转头决定长居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远离艺术生态中心的深圳。这一时期所跨越的几十年,正是本次展览作品生成的阶段。他的画作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越来越浅淡了,哪怕是黑色为主的画面,黑的都很怡然。此中的真味如好茶,再陈,色再重,依然是清透的。梁铨作品的质感,越来越如玉,在坚冷的质地中充溢着活力因子,而且已然有了包浆。所以,为了更为准确地呈现本次展览的理念,梁先生说展厅要干净,拒绝所有矫饰,安然品读为上。对此,我非常赞同。我们只需把画挂正,静待观众,旁观会心者能有几人就好。
在梁铨先生发我的展览作品目录中,最后一件是《寒山寺》。这是由多件小幅作品组合成的画作。我请教此作的由来,梁先生回答说,因为母亲曾给他讲过张继的《枫桥夜泊》那首诗,不仅非常有情境感,而且对夜中船上之人的心上之秋,满怀悲悯。依此,我的思绪却牵出了另一件事情,就是与寒山寺及其名颇有渊源的那位唐朝的诗人,僧人寒山。他曾隐居天台山寒岩,题诗作偈。其白话状态的文字与意涵,不仅被胡适所推崇,在上世纪5 0 年代还远播至美国。他甚至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偶像。提此旧事,不为别的,是在梁铨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同样的力量以及深切的、迷蒙的问题感。“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知。”再荡开一下,如果用个不高级的谐音梗,梁铨似凉泉,可与寒山互文。而梁铨不在寒岩,在很热、很闹的深圳。他在大隐中“日日试”着“新泉”。“试”与 “缺题”一样是态度,意味着自由,何缺之有?
2021年6月30日于北京画院
自述
梁铨
现代艺术中禅宗哲学的回响微乎其微,不冷不热,可能油尽灯枯,销声匿迹,都是禅的境界。一直以来我都以禅宗的信徒自居,但真正将之印证到自己的创作上,也就是这几年的事。翻看十多年前的作品,如烟的往事虚无缥缈得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些五彩斑斓的经营位置和年轻时的豪情壮志,遥远得好像是别人的事。我已经从一个阶段迈向了另一个阶段。我的画面不再固守于面面俱到的“满”,而转向对于“空”的追求,风格转变之时,我的心情很平静,甚至没有任何心情。
以画面来实现“空”的境界,可以说易如灵机一动,也可以说难如看山跑马。这种“空”和文人画的“空”不尽相同。文人画的以“空”表现“实”,但是如果单纯想表现“空”本身,又当如何行事呢?它绝非是落一笔那么简单,但是如若落了一笔,这一笔落在何处?落笔之处顿时就失去了“空”。落与不落之间不能有任何区别,否则一念之差,全局的境界也就随之成为梦幻泡影了。
很长时间,这种“空”的悬而未决成为了我的一块心病。在逐渐转化风格和苦思冥想之中,时光如同旋风般的飞逝,我进入了一个面壁参禅的阶段。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某一天,我在河岸信步游荡,看见某处的荒地上杂草无处不在,草的形状没有任何规律,看的久了,什么都像,但实际上还是什么都不像。我突然觉得有了一点头绪,虽然依然很飘忽,但是大局已定,其它的就可以不用担心了,你看,小河边的土堤翠绿欲滴,有着飘拂的垂柳和鲜嫩的青草。
这些在风中微微飘荡的野草,看上去是那么的清新,那么的脆弱,那么的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是一种魅力,至少是为了自己而开放。我在如地毯般的一片新绿中选了一株纤细的车前子,它那羽毛般细小的叶和穗因为隔得远,看得不甚清楚。我盯着它看了半分钟,然后将视线移开。仅仅一会儿,我已经不能从这一片纷乱的绿色中再将它辨认出来了:世界是细致而真实的,看起来所有的事物都微不足道。
确实如此,世界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它肯定是细致而真实的……
用微妙细节的喋喋不休来互相抵消实际效果,以期实现整体上的空泛化,这未尝不是实现“空”的一种思路。一如文人画以“空”来表现“实”;而反其道而行之,处理得当的话,恰到好处的“实”同样能够表现“空”的境界。杂草丛生的地面,任何一株草都自然而然,它们不必成为其他草的榜样或是规则,它们的鳞次栉比也并没有寓含着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意义。世界的原本意味就在于此:毫无意义的细节各自存在,这世界上原来没有那么多规律可讲究。
以细节的堆砌来实现“空”的境界,平静、无规律而静谧的线条必须要彼此抵消引人注目的效果,才能够给人以一种平心静气的禅心之感,才能够让人感觉它们只是自己呈现在那里。
这些林林总总的线条,它们各自存在时看似没有意义,但是当它们毫无规律地组成一个整体的时候,画面就完整了。“丰富”和“空”在这里实现了统一。平平淡淡和轰轰烈烈并无任何不同,对“空”的追求使我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以为那是比在艺术上的探索更重要的事情,实际上,这两者也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曾几何时候,我也学会了像那些普通的老年人那样每天出去散步,去河边的花园,时而静静地坐在树下,神思不属。心情平静,已经过了喜欢深思的年龄、只是坐在那里而已。有些时间里,我都不思考;也有的时候,纷繁芜杂的念头接踵而来。这些念头来去如风,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它们只是对往事的一种非此即彼的回忆碎片而已。这种毫无规则的回忆碎片,它们的出现和消失,呈现一片没有任何规则的乱数效果。某一瞬间,我会回忆起很多年前的一天,那一天没有发生任何事:下一刻来临之前,它(这段回忆)转眼间已经烟消云散,另一天的回忆则随即浮现在眼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并不是刚刚想起的“那一天”的延续。即非它的“明天”,也不是它的“昨天”,而是不知道是前是后以及相隔多久,彼此之间难以构成任何关系。而这一天,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的创作还在喋喋不休中继续着,但是我觉得自己现在很好。我等待着、思索着,思索着、等待着。忐忑不安,我已经想不起任何问题,抑或是那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也有可能从头到尾就根本没有存在过任何问题。置身于这个毫无规律的、细致而又真实的“空”的世界里,我对于自己现在这种胸无大志的因循自守、宁静内敛也相当满意:我没有做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