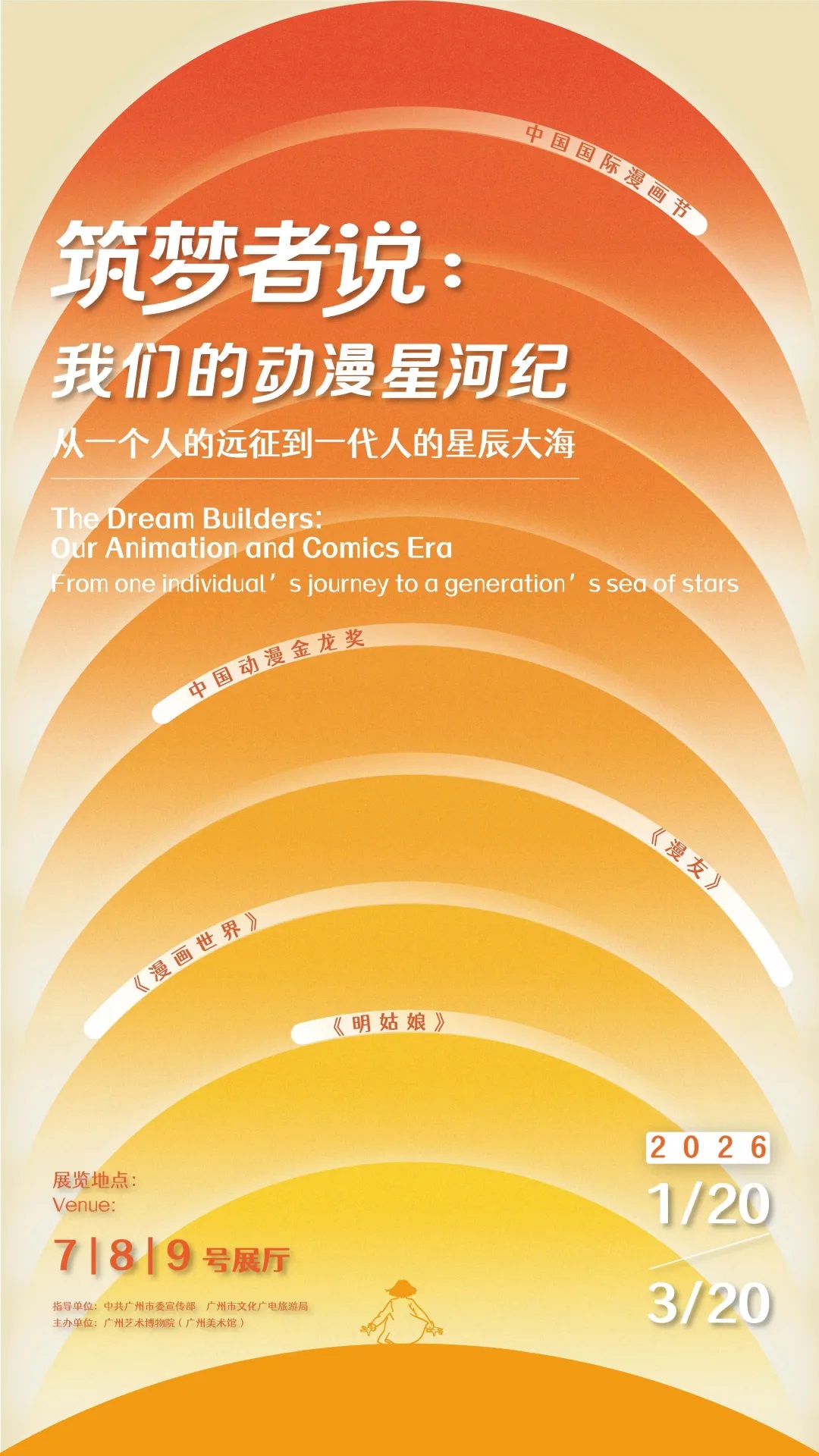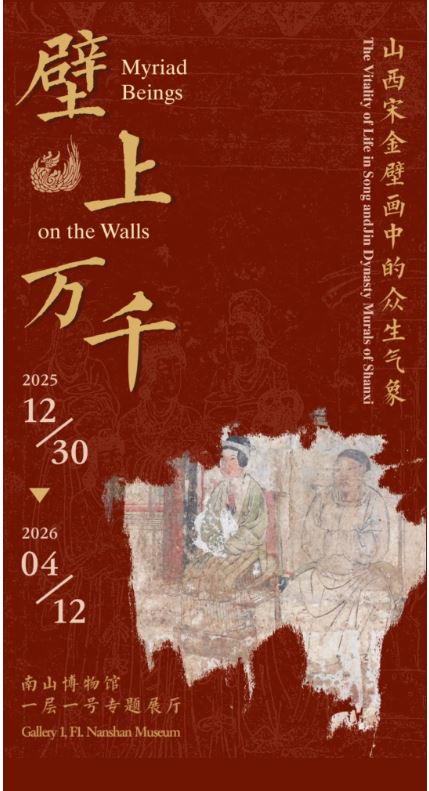前 言
风色:从行迈靡靡到中心如醉
对于人的认识而言,世界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但对于个人的记忆、想象与自我的确立来说,世界又是在不断折叠、重构的。当展开的世界因其知识化的结构而逐渐僵化人的感知能力时,那折叠的世界里所蕴藏的神秘重构力量就会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它常常意味着自我与他者、与群体的某种疏离,也意味着个体更为决然隐秘的自在状态,以至于很多时候,呈现即是遮蔽,因为无论人们言说还是描绘,都会催生重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借助艺术作品来谈论艺术家个人生活的企图,往往都是很无聊而又无效的。但通过作品所呈现的独特视界,我们确实有可能触及甚至进入艺术家那相对隐秘的精神世界。反过来说,通过对艺术家精神世界的探索,我们也可以发现其艺术风格与方法的精神根源,同时还能在作品的艺术效果中充分体会到艺术家在精神上所执著追求的那一切的气息与温度。
以艺术家王冠英为例,如果我们只是通过在各种展览上看到的那些作品来了解他的艺术创作,那么就很容易得出简单化的判断:他在观念与方法上是相对传统的,其创作变化是缓慢的,作品风格与精神取向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在总体上他是那种中规中矩的艺术家类型——但,果真如此么?答案是否定的。当我们越过他的日常展开面,进入其工作室,耐心寻找其创作的非常态折叠面,就惊讶地发现,他的艺术线索并非之前我们以为的那么简明单一,相反,恰恰是多线索的,是有隐有显的,而这些线索里面形成的作品还有着微妙的互文性,也就是说,只有当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时,我们才能忽然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发现导致了策划王冠英此次个展《风色》的诞生。我们希望能把这个展览做成能让人们重新认识王冠英的艺术世界的现场。
事实上,在王冠英的作品里,给我留下最初印象的,就是那件大幅油画《惊蛰》。它之所以会让我印象深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对于日常世界的隐秘戏剧性的独特揭示与不同寻常的呈现。
王冠英在这幅画里最让人有些意外的并不是他采用了一个反常的视角——让床上场景立起来形成一种悬挂的状态,而是让自己获得了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发现这个场景实际上是两个世界的并置:一个是安然熟睡的妻子和那些或醒或睡的小狗的世界,一个是只在画面上占了很小空间的丈夫自己沉睡的世界。前者无论是在色彩上还是光线上都是充溢着爱意、生机与母性圣洁感的,我们完全可以从那些小狗的神情中看出某种情感意义上的归属感;而相形之下,后者却是黯淡、粗糙、倦怠的,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个旁观角度在暗示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并置,似乎并不意味着融合,而恰恰意味着一种错位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王冠英眼中,那个只属于妻子的世界在日常状态下几乎是无法进入的,但在艺术的状态下却是完全可能的,当他将自己从日常时空里抽离出来,以旁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并构建这个悬置的视界时,那个在日常中已然失落的世界终于在艺术状态下回归了,而无论是场景中的那个男人,还是那个隐藏在旁观视角里的人,同时也包括作者本人,似乎都因此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整个场景里所蕴含的戏剧性,及其背后的某种微妙的不确定性,也正因如此才变得相当的丰富,而我们甚至能从中读出某种在传统基督教世界里才会有那种关于爱与救赎的圣洁意味,以及颇为含蓄的审美化了的忏悔意味。
而在另一幅作品《夏至》中,面对差不多同样的场景内容,王冠英却又出人意料地采取了另外一个视角——日常俯瞰的视角,这一次,非常显然的是,他将熟睡中的妻子重新还原为日常状态下的会自然衰老也会做梦的女人,那个丈夫的角色感觉也不再刻意压低,他也有自己的梦境,但是两个人在此是处在同一个日常世界里的,他们是有着可以沟通的日常语言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可以相互谅解的日常世界,因此在这里也不再需要忏悔、圣洁与救赎,而这里也不再是个多有秘密的世界,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但,当我们如此说的时候,也能够听到在《惊蛰》中完全敞开的空间已悄然关闭。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王冠英其它类型的以人物为主题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他会选择将自我主观意图遮蔽起来,并出离了那种探索自我与他者的充满矛盾和戏剧性的情感、精神世界关系的角度,而是选择了一种相当日常化的视角,就像我们在《朋友》系列肖像画中所看到的那样,一种摄影留念式的描绘状态,我猜他是在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意图日常化、表面化,从而使得自己更像一个他者,由此完成对自我世界的某种掩蔽。
场景的戏剧性与自我世界的掩蔽性,并非只有通过人物才能呈现出来,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数量颇多的“玉米”系列里就能看出王冠英在这两个方面所做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在处理自己非常熟悉的“玉米”系列这种北方题材时,会非常自觉地通过不同的角度来构建某种与人的潜意识相关的场景戏剧性,并折射被遮蔽的自我世界。在这个领域里他在手法与风格上做了相当多的探索,从《魂牵》系列到《梦》系列,从《玉米》到《苞米》、《苞芦》、《玉麦》、《粟米》、《西天麦》、《玉蜀秫》、《玉黍》、《御麦》、《纤粟》、《戎菽》以及《玉露秫秫》等等,围绕着东北那盛产玉米等作物的原野空间,王冠英有时像个萨满巫师,仿佛将那些作物作为献祭之物,他肢解它们、打碎它们、重组它们,让它们的气息与肢体一起作神秘之舞;有时又像个孤独的热爱土地的农民,独自在四季原野里体会着种种变化与可能;有时也像一个试图在那些农作物的躯体里发现生命的欲望与火焰的游离者……无论是什么人,所有这一切,都像不同类型的戏剧,在这东北的原野上,在只属于王冠英自己的记忆与想象的乡土上,不断上演着。其中总是蕴含着作者的隐秘情感、种种欲望、某些领悟以及神秘暧昧的想象,那是个热烈的、生机勃勃的世界,也是个会凋零萧条的世界,那是个孤独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而作为创作主体的那个自我,则像无形流动的风,不断触动它们,又不断离开它们,使它们鲜明、使它们暗淡,有时如火,有时如土,或有声有色,或化为虚空。
在王冠英的艺术世界里,除开戏剧性与掩蔽性之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那就是他对于女性世界的想象。在圣洁与日常之间,还有一个更为宽阔莫名的领域,这里不仅充满了不确定性、神秘性,也多有女性身体之美,同时也是释放想象的地方。例如在《戏水》系列水粉画里,我们就不难发现,王冠英以非常游刃有余的水粉画技法掌控着画面的生成,那些在游泳状态中的女性裸体的姿态就像是不同的梦境,都有某种视觉逼迫感,或陶醉、或沉迷、或感动、或不安,尽管角度不同,但是,这里面透露出来的,却是作者在渴望女性身体之美的过程中自然生发的距离意识,似乎一旦距离感消失那么审美的可能也就随之消失了。而事实上他是渴望着能不断陶醉其中的,可是显然,他是会不时摇摆于性情与理性之间的。但不管怎么说,《戏水》系列的视觉冲击力是相当强烈的,以水粉方式达成如此效果,是会让人意外的,这说明作者的才华与想象力刚好在这个领域里得到了理想的释放。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前面不同系列的作品比喻为不同的文体——有的是散文,有的是随笔,有的是诗,有的是戏剧,有的是小说,那么在王冠英的作品里,还有一种文体是很少有人知道的,那就是“日记”,它们其实就是他平时画下的大量速写,是以女人体为主要内容的速写。有意思的是,这些数量巨大的女人体速写比之于前面提到的《戏水》系列,有着很明显的不同。在这些速写里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画它们时一定是内心宁静的,没有任何情绪,没有任何心绪的波动,甚至没有欲望,也没有任何关于女人本身的臆想与渴望,换句话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将物质意义上的自我抽离了,而只留下审美的那个自我,在不断用自由的线条描绘女人身体之美的种种状态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与那种美相伴随的,是灵魂与内心实现平衡的可能。因此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些速写看作是王冠英的艺术日记,它们记录的是他对绘画艺术最基本元素的反复而深入的思考和实践。它们常常是鲜活的,也是率意自然的,通过它们我们不难感觉到作者在画的过程中是怎样醉心并享受着绘画本身的乐趣。或者换个角度说,在它们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王冠英绘画语言与风格的全部基因和密码。
作为一个艺术家,王冠英显然是个有耐心走远路的人。而眼下的这个展览既是对其艺术创作的一次重要回顾,更主要的,还是构建新的起点。接下来他的道路将会延伸向何处?他将如何从以往的思维习惯与解决问题的模式中跳脱出来,毫无顾忌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释放?这让我忽然想起《诗经-王风-黍离》里的一句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在这里我用一种断章取义的方式来加以阐释:人只有在如醉如痴的状态下,才能走很长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