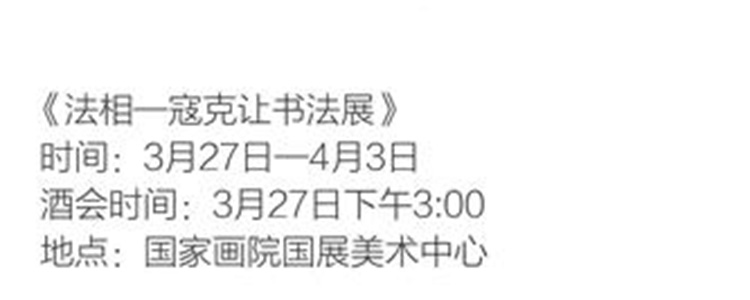
佛家言相,《金刚经》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而释典如《大般若经》、《方光庄严经》、《菩萨善戒经》阐说佛有三十二相。
自佛教传入中国,盛况超迈西土。不仅教义广布,文章家遣词立说,亦援佛典。最早见于书法文献者,当属崔瑗《草书势》。崔氏以法象指称草书千变万化之状,云:“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如此铺排,文思方肇其端,尔后崔氏巧设比况,黼黻辞藻,意犹未尽处以“略举大较,仿佛若斯”憾然煞尾。
且书法之象,虽通感于世界万象,其实悬隔。大约与《草书势》同时有纬书《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仓颉仿象。”明言仓颉以天才仿万象,并非照搬。又同时辞赋家赵壹《非草书》云:“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其本意虽在诘难,其实也道出书法之象不等同自然之象。
如此看来,只有以无边佛法比附万难名状之书法。法象即法相,观其法象,即观览书法无尽意象。
以“法相”状书法,果真与释典相出入?窃谓其事大抵不诬。当时辞赋家张衡《西京赋》所谓“桑门”,即后世译经之沙门,甚至有说《史记·始皇本纪》中“羡门”亦即沙门,此则不敢遽定尔尔者。
但书之法相自汉以下深入书史则属显见。唐张怀瓘《书议》云:“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不惟以相论书远绍崔子玉法象说,至于法相生成,其思想观念亦出于传承。张氏本文之中另有“探于万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最为近也”之说,无疑似汉代文献六百年后之翻版。
我习草书二十余年,资性愚钝,所获甚浅,而于笔下法相灿然亦颇真心期许。自甲午至于乙未,砥砺切磋未尝废日。一朝得悟法相可观必于忘我而或庶几其万一。《金刚经》所谓“不生法相”是此境地。《优婆塞戒经》备论三十二相之修得缘起始末,其中每一相,无不出于动机纯正,修行不止。惟其如此,草书之法相,或可以如张怀瓘《玉堂禁经》所言“异状之变,无溺荒僻”。
我以张氏此言自励。
寇克让,乙未农历二月初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