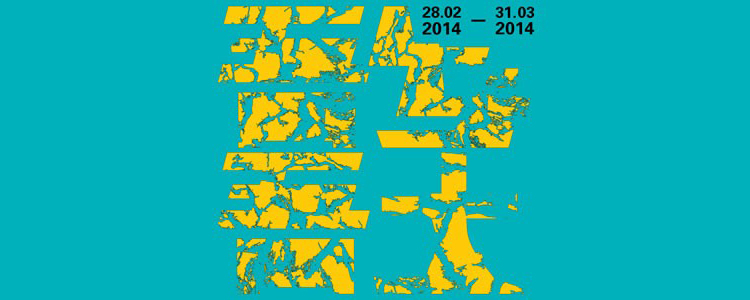
2014年2月28日,马拉喀什国际双年展·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主题展馆「吾乡吾土」展于摩洛哥马拉喀什博物馆正式开幕。作为马拉喀什双年展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参展美术馆,喜玛拉雅美术馆在“我们现在何处”的第五届双年展主题下,以“吾乡吾土”为题,通过四位关注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展示,推动乡土问题的国际交流与探讨。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前身为创建于2005年的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Zendai Museum of Modern Art),从事艺术收藏、展览、教育、研究与学术交流的民营非营利性公益艺术机构。自成立以来,美术馆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以开放的姿态和前瞻性的视野探索美术馆的新模式,重视学术梳理、尝试打通学科壁垒、努力连接当代与传统、推进国际文化艺术交流。
首次参加马拉喀什双年展,喜玛拉雅美术馆邀请袁顺、王南溟、倪卫华、王久良四位艺术家,分享自己对“吾乡吾土”的思考。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观察乡土,以摄影、水墨、影像、装置、行为等不同媒介,运用各自的艺术书写方式进行反思与讨论。其中,艺术家袁顺与100位摩洛哥当地孩子一起展开其装置“Mind Land”的创作,让从未到过中国的孩子用撒哈拉沙漠的沙子,阿特拉斯山的泥土,制作一件想象中的中国自然景观,并与自己作品一同展出。
正如策展人在展览前言中写的那样:“吾乡吾土的高楼美厦相对垃圾雾霾;新兴的城市人造风景线相对不断消失的自然风景。这些艺术家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无意嘲讽,而是试图传达一种直面现实的批判艺术精神,分享自己对“吾乡吾土”的思考体悟以及对于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艺术家的责任的反思。”喜玛拉雅美术馆希望能与各国艺术家和学者们交流不同文化与地域的发展之路和经验,共同探讨人类生存的现状,尝试解答“我们现在何处”。
【马拉喀什双年展简介】
成立于2004年,马拉喀什双年展希望通过艺术对社会问题进行探讨,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建立交流的桥梁。如今,该双年展已成为马拉喀什这个城市及地中海地区两年一度的盛会,也激发了该区域的的艺术活力与创意。成立初期,马拉喀什双年展重点关注于文艺及展览活动,之后的发展壮大中,出色的视觉艺术展示及文学项目的推进为其赢得全球的关注度。在2014年2月底开幕的第五届马拉喀什双年展中,表演艺术成为其新的版块。
吾乡吾土 – “我们现在何处”
龚迎春 孙鹏
前言:第五届马拉喀什双年展的主题是“我们现在何处”。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参展的四位中国艺术家用不同的方式观察乡土,用摄影、水墨、影像、装置、行为等不同媒介解读了这一命题。吾乡吾土的高楼美厦相对垃圾雾霾;新兴的城市人造风景线相对不断消失的自然风景。这些艺术家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无意嘲讽,而是试图传达一种直面现实的批判艺术精神,分享自己对“吾乡吾土”的思考体悟以及对于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艺术家的责任的反思。在摩洛哥双年展上我们希望能与各国艺术家和学者们交流不同文化与地域的发展之路和经验感受。
双年展的主题“我们现在何处”似乎是一个简单且直接的问题,就如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哲学四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人是什么?”一样简单直接。
四位参展艺术家的“吾乡吾土”在中国,然而他们的观察和反思对于已经非常一体化的“地球村”来讲并不是特例。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这样雷同,各自面对的问题这样相似。
袁顺的装置创作是与摩洛哥的孩子一起展开的,这是13年他从智利开始的“mind land”计划的延续。让从未到过中国的孩子用当地的泥土制作一件想象中的中国自然景观与自己作品一同展出。结合了行为、作品对话及制作过程中不干涉方法的创作开启了对开放和自然的中国乡土的心境之旅。
倪卫华从九十年代就开始用相机追踪中国城市风景的变迁,他的摄影和录像作品似乎也记录着每一时期政策的变迁。站在奢华的楼宇和温馨的广告背景前面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涌进的庞大的打工群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放弃了祖辈的土地,离开家园,希望在城市找到新的生活。然而画面上变化的只是背景和背景上的口号,不变的是这群人的表情和状态,他们离城市如此之近,又如此之遥。这种无奈的不变和不变的无奈,被倪卫华在不断更新的背景前定格。
王南溟是水墨创作出身,他的前卫艺术思想让他不满足于水墨语言本身的推陈出新,而是要伺机打破。<拓印干旱>和<绿藻>是他批评性艺术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代表之作。当年在“雾霾”一词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他就已用装置和行为结合的方式创作了一批警示环境问题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在当时除了部分圈内人士认可外未能引起更多关注。<拓印干旱>乍一看会以为是画家在做笔触创作,然而这不是艺术笔触,而是黄河郑州段的干涸河床。
王久良所展现的是另一类风景——垃圾风景。王久良将成堆的垃圾拍得美不胜收,有远景的大山和近景的小河,还有夕阳下食草的牛群。然而近看人们会发现山是垃圾堆成的山、水是浸泡污物的水、牛群脚下不是绿草而是铺满的垃圾。看王久良一幅幅垃圾风景摄影,观众先是被迷惑,接下来被触动,进而反思。据<自然>杂志报道,全球居民现在每天扔掉三百五十万吨垃圾,由于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到本世纪末将达到每天一千一百万吨。恐怖的数字,王九良摄影作品上的垃圾风景可能很快就是你我居住小区外的景观了。
袁顺的<臆念之景>装置和摄影展现着烟雾缭绕的幻境,很有些中国山水的影子。艺术家先建好装置模型,选择视角和光线,放置烟雾,然后用相机将幻境瞬间定格,随后毁掉装置。真实与虚幻的对比,小装置与大宇宙的反差,具体与抽象的转换,创造与毁灭的连接,让观者在享受着臆念美感的同时有着说不出的恐惧和震撼。这些颇似科幻场景的幻境,可能是已经毁灭的地球,也可能是正被开发的月球、火星,抑或是另一个遭遇人类的星球。
在倪卫华的城市风景、王南溟的自然风景、王久良的垃圾风景之后,袁顺的臆念之景是否就是人类的未来风景。臆念之城是否就是人类未来的吾乡吾土?
讲一个禅宗故事:从前有位公差押解一个犯人去服刑,路途遥远,公差怕忘掉重要的事情,给自己写了个清单,每天早晨出发前必须逐项检查:1.装衣物和盘缠的包裹 2. 公文 3. 犯人 4. 公差自己。一日,两人赶路百里,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公差多喝了几口,大睡不醒。犯人见机可乘,扒下公差的官服穿上,把公差的头发剃光,把自己的刑服给公差套上,然后溜之大吉。第二天公差醒来,照例清查他的四项:包裹,在;公文,在;犯人,他左窥右视,一眼看见镜子里一个穿刑服的光头人,奥,犯人也在;可是“我”呢,“我”在哪儿呢?
这个故事在现代语境下如何理解?包裹是人的财产和物欲;公文是日复一日的工作、责任;这些人们很少忘记。犯人呢?曾几何时,人类被膨胀的消费欲望、过度的城市化进程、疯狂的金融游戏、飞速的经济增长所挟制;被垃圾污水雾霾毒食品钢筋水泥恐惧焦虑所包围。当人类不再控制欲望,而是被欲望所挟制时,人的身份就变成了犯人。
那么,作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我们能认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期望什么?
知识分子艺术家能首先认识人类现在何处,然后应该用他们的作品警示人类,我们已经把自己丢了,我们不仅是欲望的囚犯,也是以增长发展为名义毁坏地球家园的罪人。知识分子艺术家需要承担其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保持批评性、不随波逐流、为弱者代言、追求正义与公正。即便知道艺术的力量不足以改变世界,他们仍可像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言 “如何我知道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今天仍要种一棵小苹果树。”
说到艺术家的责任,需要提一句中国艺术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面临的一个尴尬。许多中国艺术家或身处院校、体制之內,或要靠拿项目养活自己, 意识形态限制以及生存创作条件让他们所要承担的公共正义和真理代言的角色逐渐退色,有人甚至认为这样的角色从未真正形成过。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从未放弃过对这片土地和乡人的真挚关注,生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渊源让他们无法回避。参展的四位中国艺术家受益于艺术创作及其视觉语言的多元解读性,其作品可以较其它文化门类有更多的表达和传播空间。他们作品的“中国问题情境” 并不只局限于中国本土,也是对全球意义上的“吾乡吾土”的反思。
马拉喀什双年展的主题“我们现在何处”是一个非常好的命题,因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间都曾经变为“现在”,未来的任何一个时间也会成为“现在”。海洋上航海的人需要随时定位,是为了计划下一步的航线。人类认识现在何处,是为了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可以期望什么。
现在,20世纪刚过去十多年的21世纪初,是一个从石油主导向大数据主导过度的时代,从模拟向数字化转变的时代,从传统农业向转基因发展的时代。科技创新的动力加上人类永不满足的欲望可能在本世纪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比如我们已有人造假肢,心脏起搏器,可能很快就会发明研制出人造器官、人造皮肤,人造大脑,还可能让人类的平均寿命提高到100岁,150岁,200岁。其实,人类的生命不只是由“出生”来定义的, 也是由“死亡”来定义的,难道我们将要挑战死亡,要长生不老。
所以我们就可以对自然毫无敬畏,疯狂索取?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发展科技,促进经济,提高生产,刺激消费?所以我们必须开发更多的城市,耗费更多的资源,制造更多的垃圾?当地球彻底变成垃圾地球时,人类是否已计划好退路,全体移民到月球上的宜居城市,火星上的度假村?若是这样,前瞻的政府和开发商们是不是应该开始地球外的投资圈地了,未来的建筑展是不是可以征集月球火星开发计划了?
再讲一个小故事:老喇嘛问小喇嘛“你用柴禾烧水,烧到一半,发现柴禾不够了,怎么办?”小喇嘛说“我去拾些柴来。”又问“还有什么办法?”答“我可以去邻居那里借”。再问“还有什么办法?”答“我去市场上买。”再问“还有什么办法?”答“没有其它办法了。”老喇嘛说“为什么不把水倒掉一些?”
还有什么办法吗?为什么不把水倒掉一些?这正是本次参展的四位艺术家用其作品提出的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