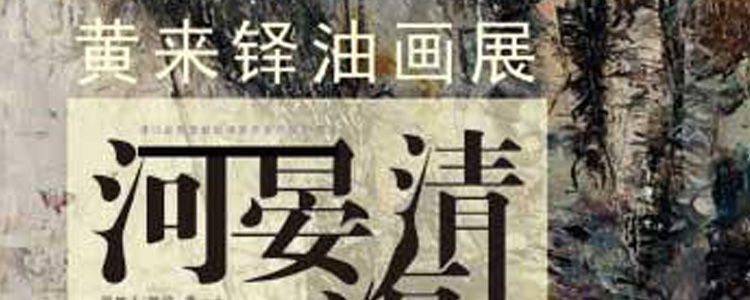
油画家黄来铎先生出生于1935年,和我的父亲同龄。 为他的展览写前言,我其实是不够资格的。看完《河晏海清》的展览作品,我想虽然是两代人,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我们都怀念在高速经济发展下正在消失的家园,那些滋养过一代代中国文人精神世界和气质的家园。
黄来铎先生是上海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江南的美好:水乡,驳船,丁香花,黑色瓦片的屋顶,被南方的水气和雾岚萦绕。在当下这样一个空气PM2.5污染指数不断走高,公众需要带着口罩上街,突发疾病让人惶恐不安的城市中看到黄来铎的作品,除了作品的艺术审美之外,我们本能地会想到更深的层面去。我羡慕黄来铎先生, 他成长的时代,江南还是小桥流水精美抒情的时代,而我担心我们的下一代,也许黄来铎画中境像,下一代只能通过他的作品才能看到了。
近年来,在当代艺术的创作讨论中会听到不少关于风景画是否具有当代价值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创作中的风景画不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自娱,是忘情于山水而回避现实冲突和矛盾。风景画创作在当代艺术创作中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当风景作为具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时,相同的风景触动观察者的是不同的视角。是复制它?是借景抒情?还是对照,反喻,警示?
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其著作《风景进入艺术》中说:“我们被非人造而具有与我们自身不同生命和结构的东西包围着:树、花、草、河、山、云。它们在几世纪以来激发着我们的好奇和敬畏,一直是愉悦的对象。我们在想象中重塑它们来反射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开始将它们视为对所谓‘自然(nature)’这一观念的贡献。风景画标志着我们关于‘自然’这一概念的发展进程。自中世纪以来的自然概念的兴起和发展像是一种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人类精神尝试再次创造一种环境和谐。”
在这段叙述里,自然是主体,而人类不过是寄居于自然中的客体。在当今,重新思考人类和自然的彼此依存关系,是最有价值的思考。
我想说的是,家园不在,精神何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