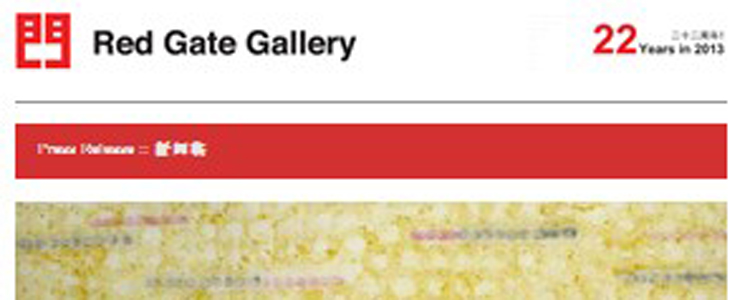
“个体的形迹——孙佰钧、何灿波、吴少英水墨作品三人展”将于8月24日在北京红门画廊举办。
“实验水墨”在中国大陆已有近三十年的创作实践,而“实验水墨”得以相对充分的发展则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便是这一时期以来“实验水墨”创作的代表性艺术家。作为中国最早创立的当代艺术画廊,红门画廊长期关注现代水墨的发展,继去年“清境:新水墨联展”之后,红门画廊再次策划三人水墨作品联展,以期展现水墨在当下旺盛的生命力和多样性。
孙佰钧、何灿波、吴少英是三位风格非常独立且鲜明的水墨艺术家,他们无论对于水墨的理解还是个体创作中的精神指向都不尽相同。水墨该是怎样的一种艺术?我想,它应该是以传统为血脉,以现代为土壤的一种新事物,新的文化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水墨才刚刚开始。三位艺术家不同的个体实践为我们带来了水墨创作的启示,同时也补充了我们对水墨艺术的理解。
孙佰钧的水墨艺术,体现了一位艺术家对生命本体的微观认知,在他布满斑驳细胞的画面中,引导观者从一个切面去理解生命整体。但是,他的艺术面貌并非一开始便是如此,比如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与传统山水的互文创作,在画面里,我们能认出“米氏云山”以及与我们生活相关的田园。虽然,孙佰钧的作品面貌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他似乎一直都在致力于一件事,那就是将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在他对生命的认知中统一起来,统一于山水云气之中,统一于一个切面,一个细胞,从而体察生命之于自然的生息之态。
何灿波是一位独特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抽象符号,如几何和人形,我们可以从他的画面中直接得到丰富的信息。他的画面有西方的形式,又有东方的内容,甚至像是一个圣徒在解读“圣经”,也像一个诗人在用画面思索一首诗,一个思考者在陷入一个哲学命题。精神性是何灿波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他画面中的人形符号像是抽离肉体的灵魂,在茫然无措的时代寻找归途。何灿波的艺术探索体现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精神状况的忧心疑惑。然而,何灿波的作品是非常丰富的,在内在中充满细微的变化,在我看来,何灿波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建立了自身艺术逻辑系统的艺术家。
吴少英的文化背景不在大陆,生于澳门,后又定居台北、北京,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她的作品中没有那么多文化沉重感,换一个角度,她没有大陆人身上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文化包袱。吴少英艺术状态更加个人性,充满游离,游离,仿佛是她的生活状态,也是她的艺术状态,而她的作品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也如这般。因此,吴少英采取的表现方式更加自由多元,比如摄影、影像、戏剧、行为等等,这些都是她表达水墨的手段。我想,在当代的语境下,艺术的表达方式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依然是这些方式的背后,吴少英呈现出一种对水墨怎样的理解。
我想说的是,我们应当避免一种笼统的方式去理解每一个水墨艺术家,尤其是长期以来以水墨为核心,长期实践和探索的艺术家,试图在自己艺术创作的精神指向下建构自身艺术逻辑系统的艺术家。作为致力于此的艺术家,每一个人的努力和实践都值得做个案研究,将之作为一个有效的个体去重新审视。在笼统命名成为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往往因为一个词汇或概念忽略了每一个创作个体的价值,然而,文化创造力的体现恰恰是具体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所以,孙佰钧、何灿波、吴少英此次的展览虽然是一个三人水墨联展,但是我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他们每一个人艺术状态与艺术指向的不同,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通过这次展览,更多观者能够深入到三位艺术家现在和以前的创作之中,将他们每一个个体当成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去理解,而非只是将展览中的几件作品作为长期以来水墨实践的结果来看。
“实验水墨”容易让人将之理解成一个过程的状态,的确,从集体的创作实践而言,水墨的正处于一个生长的状态,这也是我愿意将之看作一个新的文化事物去理解的原因。然而,这个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无数个个体的完成,他们在各自的理解和信念之下实践着自己的水墨艺术,他们既是“实验水墨”的开拓者,也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认识“实验水墨”的内容。最后,在个体经验相对完成的前提下,“实验”一词已变得充分可疑和无效,因为个体的价值始终要释放出来,被要求理解,被要求认知。于是,以三位水墨艺术家的联展为契机,将“个体的形迹”作为本次展览的题目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个体的价值需要在笼统覆盖的环境中被郑重重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