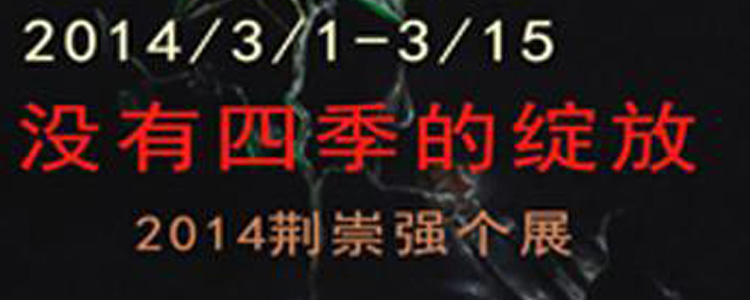
1958年,是一个国人印象深刻的年份:志愿军从朝鲜回国,中国正进入“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开始,也就是这一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一年,降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人:王朔、冯小刚、杨丽萍,还有麦当娜。我这里要说的荆崇强先生,也出生在这一年。
何以要说这样的年份?我和荆先生并不熟识,是偶然的遇到,一个绘画的前辈,言少而诚挚,拿出画册大家传阅一番,内容现代而火热——这个年代出生的人,一定充满故事。
初看荆先生的作品,大多数人会以为他是一个年轻的画家,和他的内敛的态度截然相反,我们看不到他这一同时代作品中风行的山水田园和高级灰,而是满画面的疑虑、思考和魔幻景象。他的作品中充满着穿透、束缚与对立的符号,庭院、火车、宝塔、飞机,他们不停地束缚、不停是穿透、穿透,留给我们的背景永远是深沉的茫茫乾坤。我冒充一次心理分析的医生,这种种的纠结是否是对安全的期待与恐怖的抵抗?是对世道的叹息还是心灵的慰藉?
从艺术史看,这种批判的思维上个世纪初在西方有了充分的展现,但荆先生出生的时代,我朝的艺术正在“为人民服务”,斯大林时代的艺术风貌遍布神州,当”八五新潮”到来的时候,荆先生正是青春热血的年龄,和那一时代中国人集体的解放与批评赤诚相见,而他的画面,也就一直地热血沸腾到今天。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些晚上二十年的青年批判,反而显得“为赋新词”样的虚张声势。今天时代不必坦心置腹,却可以虚情假意地柔肠百结,不必愤世嫉俗,却可以精雕细捻地安然花下。
所以,我更喜欢荆先生的纸本硬笔画,轻巧动人,功底扎实,天马星空的魔幻还在,蕴含的批判火气全消,反而形成一种迥异的趣味,如同没有四季的绽放,好看的很。
写荆先生的画,我倒不急于了解荆先生,就像并不急于了解魔术真像的观众,没有答案,也是一件好玩的事,说对了,大家赐笑,说错了,诸位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