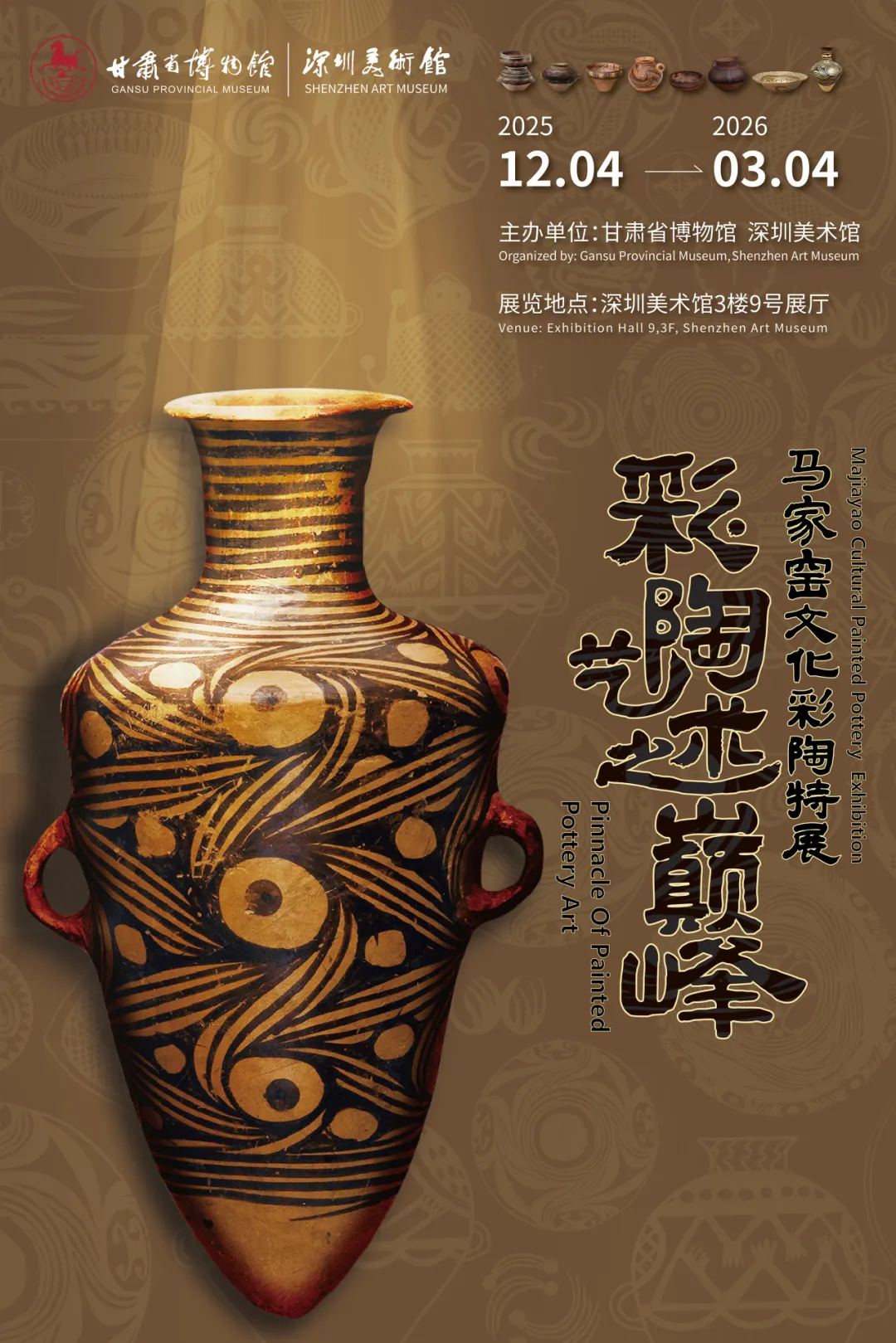我和张成相识相知多年,亲历其创作一路跌宕的变化,从意象风景走到今天光影迷离的幻象。至此,他完成了一段艺术上心历路程,作品完全呈现出了东方式的抽象形态。
张成出生于黑龙江的阿城的山区,这里曾是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营建的金代故都,史称金上京会宁府。历史上的兵戈铁马、龙盘虎距已化作昨日烟云,留下的是亘古不变的北方风景。初春,广袤的黑土地上残雪遍布,冰凌花顶开冰碴子顽强的张显着生存的力量;仲夏,万木扶疏,群山苍郁;深秋,沼泽里不知名的杂花野果相映成趣,柠黄、玫红、淡紫、粉红、浅蓝……汇成了一支缤纷的色彩交响曲;隆冬,山舞银蛇,寒妆素裹,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这就是孕育着张成艺术启蒙的原初营养。现在对故乡的记忆,把张成的艺术引人一个超越了客观实体的意象,在变换复杂的空间构成和具有书法韵味的点线挥洒之间,气韵流动,能量勃发,画家的激情仿佛附和着宇宙洪荒的原始节奏而跌宕起伏。
艺术家朱德群曾这样表达过对中国唐宋时期绘画的敬意,他说,唐宋艺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们“是那时的画家直接与自然接触,是自然孕育出来的”。这样一个朴素的观点,今天仍然贯穿在张成这样的艺术家的实践中。
张成的绘画虽然采用西画的载体,骨子里却在探求中国传统绘画之精神,以忘我的情怀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为我们展现着"象外之象"。显然,就此而言,他成功地嫁接了东西方两种艺术元素,使抽象作品的面貌呈现着东方的诗性。
当然,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张成在早期的绘画中,已经有意淡化景物的形态,注重意象的感悟,但是,那时更像是一种抒情,追求的是“势”与“意”的酣畅表达,犹如中国泼墨山水的淋漓快意。
渐渐的,他开始感到一种困惑,他发现趣味性的东西往往会减弱作品本身的力量,表象的自然之美并不能完全表达思想的意义。这样的一种思索,开始让画家陷入创作上的“瓶颈”。这样的焦灼感,恰恰促使张成开始新的探索,在以往充满湿润的韵律中,去有意寻找一种生涩感。也就是从这个时期,他的作品经历了一次“涅槃”,画面变得单纯,从以往的“传神”变为 “造心境”,意象化为抽象,试图在感性中触摸到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努力抓住“象外之象”。这样的一次嬗变,对于艺术家无疑是幸运的。
我要说,张成是一个天然的直觉型的画家。他几乎没有经历过美院严格的造型基础训练,甚至也没有象其他同龄画家那样受到过印象派画风的深刻影响,但这也许恰恰保持了他的原生直觉。他也不擅于分析自己的作品,想要说的都在画中凸现出来,直抒胸臆。这是朴质的状态,也是一个艺术家应该保持&值得庆幸的本真。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绘画的探索中,自林枫眠始,几代中国艺术家的佼佼者一直在试图将东方传统与西方的现代,尤其抽象表现艺术进行了巧妙的结合,或者说是以个人的方式平衡了这两种因素,从而在绘画语言上取得真正的突破,这个框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间已经构成,并出现大家。如今,在当代艺术的大潮之下,东西方文化更加融合。怎样在抽象艺术的基准中保持各自的土壤的原生性,保持各自文脉的差异性,更凸现出其意义和紧迫性。在这样的一种探索中,我期望象张成这样一批新生的艺术家从敏捷走向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