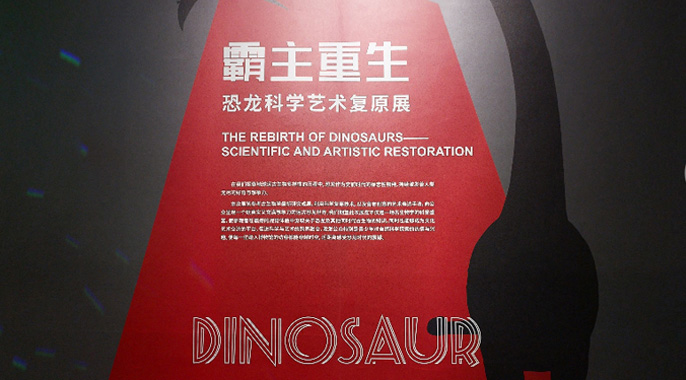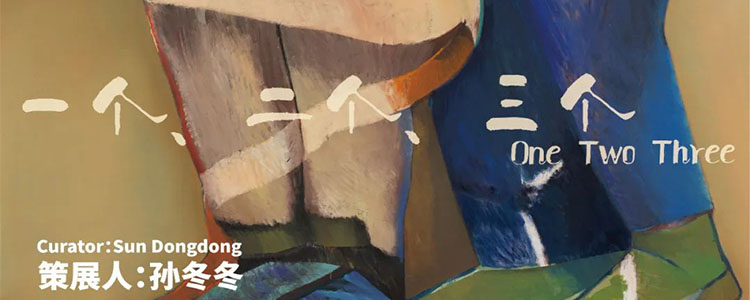
有一个问题,闫占城现在的画作,作为图像“基底”的背景,为什么越来越趋向于纯粹,如同一个中性空间。当然,对于满足观看形象(图像)的人而言,这完全不是一个问题,绘画原本就是一项“制像术”,有了辨识的形象也就够了。但现在的画家,如果也这么想,只能说明这位画家尚未经过“现代”的思辨,空白的画布仍作为一扇向外打开的窗户,画家只需要将看到的现实描绘下来——有趣的是,闫占城自学院毕业后,他就一直试图逃离外在世界对于自己绘画的掌控与支配。
在一开始,所谓的“外在世界”,对于闫占城而言,指向的是一种学院化的组织与再现世界的语言模型,他只需要更改一下语言模型就好。就像他初涉艺坛,在2014-2015年所作的,绘画与再现性无关,而是一场关于质感的游戏。借由风景展开的画面,图与底的空间关系隐没在斑驳的色彩与丰富的肌理之中,以至于形象看上去暧昧地像其间的一个个细节。虽然,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表征,但在那时,外部世界充分给予的物质性提示,正是闫占城为了脱离学院的影响,认知与理解绘画平面性的实践入口。
随之而来的,是对空间秩序的要求:当形象慢慢从背景中生成出来,意味着闫占城的画面也有了清晰的“图底”关系——线条式轮廓形象,搭配形状感的外部世界,通过色彩与笔触的调度,强化画面的结构。从质感到形状,闫占城一直在化约外在世界从自己绘画所传递出的现实感。而与之对应的,我们看到了形象正在逐渐占据了画面的主体。整个过程,一路过来就像电影中的景别,从远景、中景再到近景以及特写,形象逐渐被放大,衬托形象的背景变的越来越静寂,直到在闫占城近两年的画作中,彻底变得沉默。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闫占城面对绘画基底的态度,令人联想到14世纪英国逻辑学家奥卡姆的威廉所提出的思维原则,后世将之命名为“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个原理常见的描述形式:如果你有两个或多个原理,他们都能解释观测到的现实,那么你应该使用简单或可证伪的那个,直到发现更多的证据。了解哲学史的人,从中可以体味到一种“经验主义”的哲学底色,所以,“奥卡姆剃刀原理”更多的运用在科学领域。但如果换到另一个使用语境,例如在社会生活中,剃刀所剔除的干扰,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去与留?
在一开始,所谓的“外在世界”,对于闫占城而言,指向的是一种学院化的组织与再现世界的语言模型,他只需要更改一下语言模型就好。就像他初涉艺坛,在2014-2015年所作的,绘画与再现性无关,而是一场关于质感的游戏。借由风景展开的画面,图与底的空间关系隐没在斑驳的色彩与丰富的肌理之中,以至于形象看上去暧昧地像其间的一个个细节。虽然,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表征,但在那时,外部世界充分给予的物质性提示,正是闫占城为了脱离学院的影响,认知与理解绘画平面性的实践入口。
随之而来的,是对空间秩序的要求:当形象慢慢从背景中生成出来,意味着闫占城的画面也有了清晰的“图底”关系——线条式轮廓形象,搭配形状感的外部世界,通过色彩与笔触的调度,强化画面的结构。从质感到形状,闫占城一直在化约外在世界从自己绘画所传递出的现实感。而与之对应的,我们看到了形象正在逐渐占据了画面的主体。整个过程,一路过来就像电影中的景别,从远景、中景再到近景以及特写,形象逐渐被放大,衬托形象的背景变的越来越静寂,直到在闫占城近两年的画作中,彻底变得沉默。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闫占城面对绘画基底的态度,令人联想到14世纪英国逻辑学家奥卡姆的威廉所提出的思维原则,后世将之命名为“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个原理常见的描述形式:如果你有两个或多个原理,他们都能解释观测到的现实,那么你应该使用简单或可证伪的那个,直到发现更多的证据。了解哲学史的人,从中可以体味到一种“经验主义”的哲学底色,所以,“奥卡姆剃刀原理”更多的运用在科学领域。但如果换到另一个使用语境,例如在社会生活中,剃刀所剔除的干扰,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去与留?
当作为一个问题,放在闫占城的面前时,他的行动其实给了另一个答案——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对于闫占城而言,这是一种“后疫情时代”的生命体证,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使得形象的背景回归到一种母体状态。在此时,我们可以将之诠释为一种生命原初的虚无。但对于语言而言,这恰恰是话语的变体,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表达术。“此处无声胜有声”,上一句是“别有幽愁暗恨生”,与其说出来,适时的沉默才是最诚实的部分。

最新展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