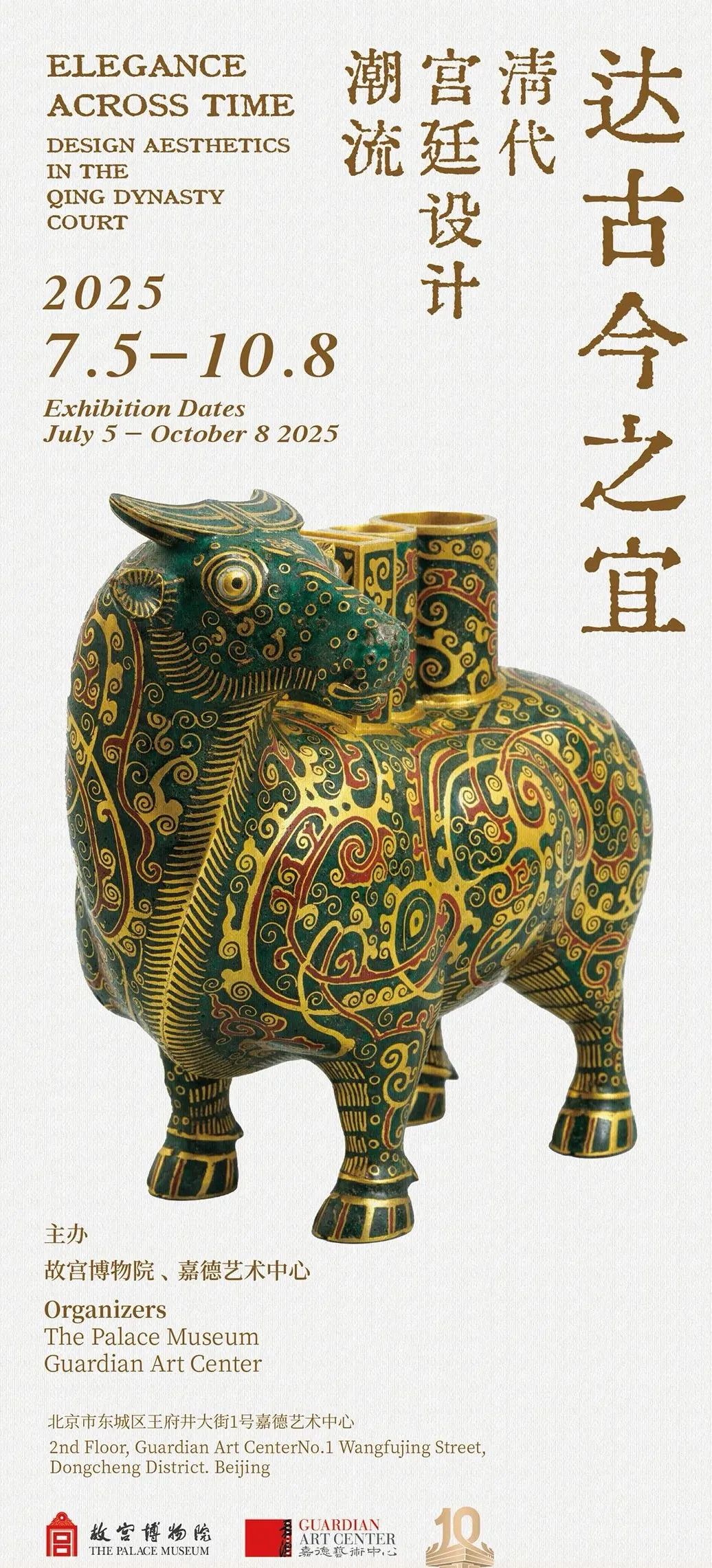我曾做过一场黑白的梦,一片悬崖边的玫瑰园,远处的海岸边晦暗消沉,无尽的雨落在黑色的玫瑰上,埋入一切震荡的缺失。至今我仍然不知道脑海中的那片海洋是否存在尽头,也不知晓这个世界能否被拍摄完结。
一百多年前,人们或许认为摄影的终结是地理的终结;再后来人们认为摄影的终结是事件的终结。但如今看来似乎直至宇宙归于热寂,只要尚有粒子震动,动态的变化便近乎永恒。
阿司匹林的拍摄行为几乎无尽,快门的声响触发另一片空间的虫洞,将堆叠的影像展开,它们或许是造物主未曾见世的图纸,或许是酒神私藏的财宝,或许是无际的原野。
上一篇: 朱新宇 ZHU Xinyu 个展「诸时皆在 NOWS」
下一篇: 代俊鹏:造化游戏

最新展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