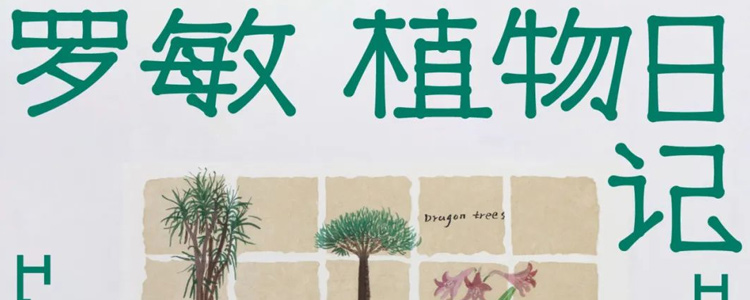
前言
“植物日记”是一个直白而又朴实的标题,它既是展览的内容,又是有关时间与发生的意象,像是罗敏的生活,记述着日常里细微的情动,与植物的亲密关系。
展览分为游日记、春天的故事、植物的倒叙三个部分。以一段私人的旅程开篇,2023年8月,罗敏从纽约登船,随“海洋绿洲号”去往加勒比海岸的巴哈马、海地,之后返回纽约-马德里-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柏林。旅程中的见闻,总是激励着下一次旅程的开始。次年3月,罗敏到达地球的另一端,新西兰的奥克兰和远北地区,再由墨尔本-悉尼,远渡太平洋返回。
5月,罗敏前往东京,之后又从上海坐船到达九州……当然,在这一年里,她也往返于国内的许多城市。直到今年7月,这些没有“负担”的远行,便有了整个365天的绘画日记。某些时候,用绘画去完成一篇日记,成为罗敏的“日课”,闲散旅程里的唯一戒律。然而,幸运的是,它们被描绘得如此轻松、惬意。
日记总有着某种记忆的特质,例如这些日记纸张上的地点:一份某天的北京日报,墨尔本超市里的广告页,长沙酒店里的信签,奥克兰的城市地图,东京回国飞机上的垃圾袋等,这些标识记录了罗敏旅途中的宿站。我们也可以换一种类似电影特写的叙述,这些片段将我们从抽象、漫长的旅程中,拉回到一个具体、亲昵的时刻:某一天,桌子上的一块糕点,一瓶墨水,几张照片,沙发的一角,或是新闻里的重大见闻。这个世界的大事与小事,罗敏以一样的平常心记述。
这便是现代生活的特质:它丰富但又日常,琐碎而又具体,有时一地鸡毛,有时无所发生,但又仿佛发生了一切般的美好。意义总是经“无聊”转译,当罗敏这些无关轻重的“日记”贯穿成线时,便转向了更为永恒和深邃的命题:时间与存在。
在展览的另一部分,我们以时间为线索,陈列了罗敏的“春天的故事”,她描绘下中国80年代的100本出版物的封面。记录成为这些作品的特质,它们亦由今天提问,人们在80年代有什么样的美学与理想?那个被理想化的时代,又抱有什么样的希望?又是什么改变了一代人的认知?
或者说,罗敏需要表现的是一种不可挽回地时间与记忆,因此“如何”表现就变得比表现“什么”更为重要。80年代的书籍封面,在展厅中一字排开,相似的尺寸,春天中蕴含的美好,成为展览的历史背景。365天的绘画日记,以档案的方式封存并呈现。一天只画一张,而在这一张之外,一天里没有被表述的时间与存在,却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
在展厅的另一侧,“植物的倒叙”呈现了罗敏2009年以来和有关植物的绘画作品。我们仿照了植物园的温室结构,人们身处其中,仿佛于某处丛林之中,微光朦胧,绿影绰绰。这些画作来自于罗敏日常生活中与植物关系,有时是画室里几株散落的芦荟,有时源自古代画谱里的花鸟,风寒三友图、葵石峡碟图、写生草虫图。除了对中国传统的借鉴,作品中亦有西方现代科学的交错,布鲁克林植物园、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些动植物以标本的形式分门别类地被描绘。
某些时候,罗敏画中的时间是写实的,它忠实于生活,来自于点滴。但又是写意的,在过去的几年间,我们困于家中、旅馆与房间,有了更多时间去观察那些被遗忘的近处,窗台上的植物,春天的柳絮,院子里的泥土,它们一直都在,也一直有着自己的生长。但只要你关注它、凝视它,它便回馈给你一种超凡的安静与亲昵。
我想,这或许也是罗敏对植物、旧杂志与远行感兴趣的原因。无论你出生在哪里,总是未得其所。机缘把我们随机的抛向一处,我们称之为“故乡”,但它也不过是旅途中的宿站。直到,我们再偶然遇到一个地方,却神秘的觉得这里正是栖身之地,是自己一直寻找的家园。像是毛姆所言:“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在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宁静。”
文 | 崔灿灿
2024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