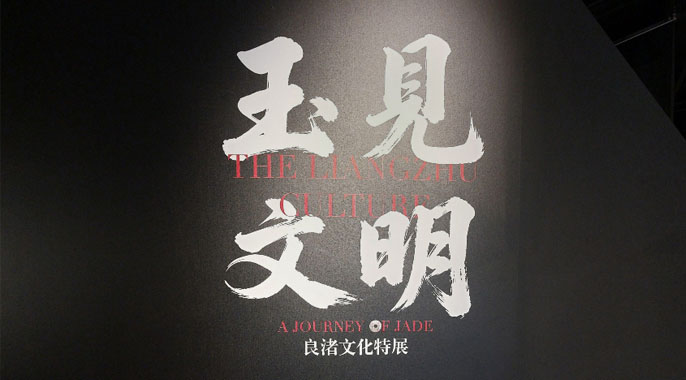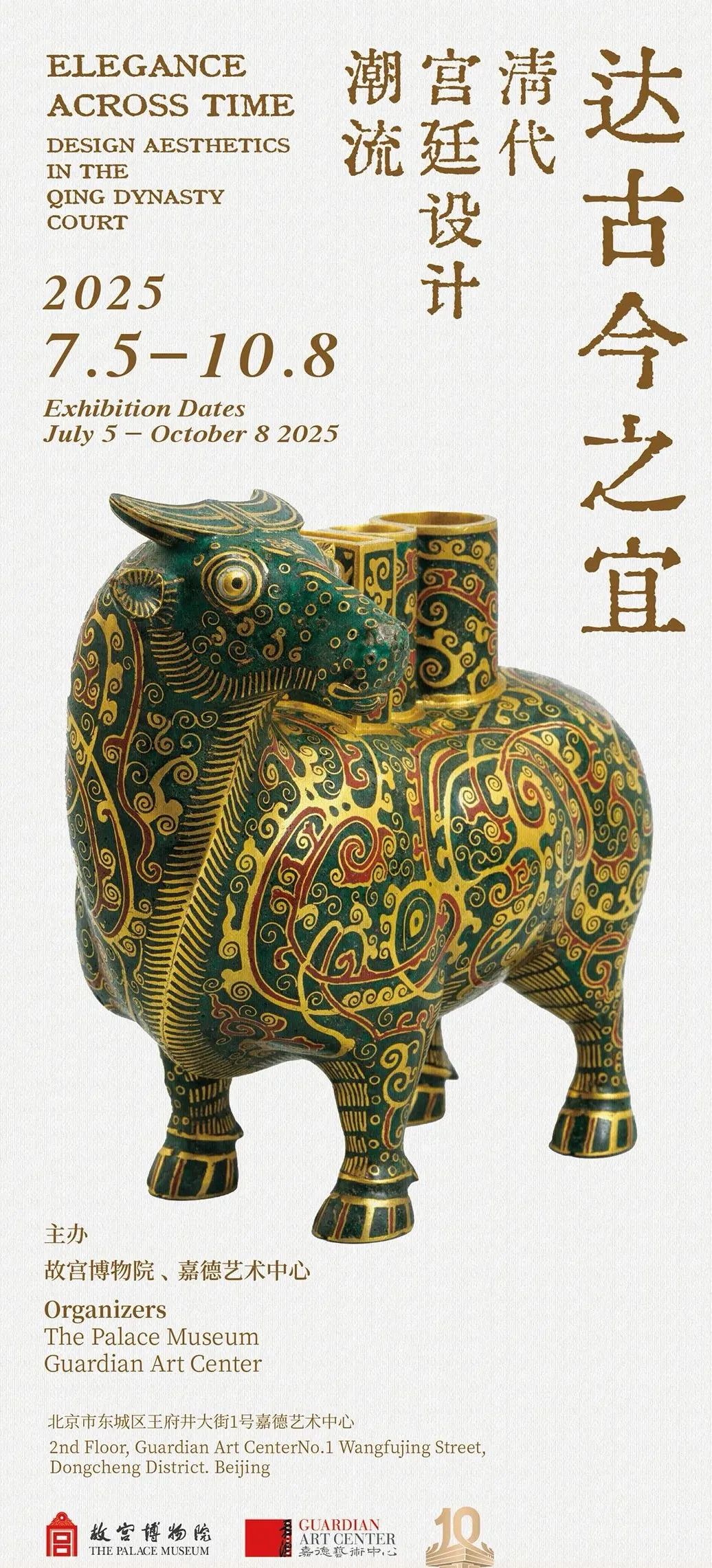竹庵的画
王家葵
我完全不会画画,甚至不全懂画,以前写过《近代印坛点将录》和《近代书林品藻录》,讨论近现代书法篆刻,也曾经动念再编一册《近代画家百一赞》,以与前两书鼎足而三,尽管从旁怂恿的朋友不少,终究还是存有一毫自知之明,没有轻举妄动。
虽然不懂画理,但似乎并不妨碍我以“外行”的立场看看热闹——近代的中国画坛也真够热闹。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外来的美术理念冲击下,不论是否饮过洋墨水,不论主张激进改良,或者温和渐变,或者恪守陈规的艺术家,笔下或多或少都流露出西洋风格、东洋趣味。渐渐的,四僧的地位忽然压倒四王;大写意花卉竟有凌驾山水大科的势头;乃至随笔漫画,也可以堂皇登大雅。
艺术风格千千万万,欣赏品味万万千千,二者契合,便在观览者心中涌现美感,如若相反,则生出厌离。而站在创作者的立场,我手写我心,并不曲阿观览者的好恶,随时俯仰。所以,不管是四任、蒲华、吴昌硕,还是稍晚一些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在他们的时代虽然也是谤誉参半,而盖棺论定,其大师地位终究不可动摇。
晚近的大陆画坛喧嚣依旧,但具体情况却十分不同。以旧笔墨写状新物事,原本无可厚非,可一旦有强权政治渗入,不仅压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更扭曲观览者的美学认知。尤其可怕的是,一旦创作者与欣赏者都自觉自愿地为邪灵讴歌,则整个社会如陷深渊,求出无期。
翻看吴湖帆画作,于两幅作品印象深刻。一是1965年庆祝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用水墨烘染出来的蘑菇云,其创造性并不逊色于“马远水”、“米家山”;另一幅标题为“虚心学习又红又专”的镜心,以一匹红砖压一枝墨竹来切题,庸俗如此,已非言语所能表达。前一作品证明吴湖帆的创作能力并没有因各种运动的折腾而下降,后一作品则是文人精神堕落的标志。至于更多的艺术家,画惯了“二为”主题的作品,连技术也退转了,此数十年间诞生的所谓“重大题材”作品,大半都是吴湖帆“又红又专”之流亚。
1980年代艺术家开始觉醒,竭力挣脱体制枷锁的桎梏,部分国画家也尝试使用夸张的笔墨、强烈的色彩、扭曲的造型来表现荒率的主题,藉此表示对正统“赤色”文化的反叛。我理解这些艺术家内心的无奈,对这样的作品也无反感,但总觉得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对抗,醇和尔雅的古典主义也连带“躺枪”,而这种古典主义,从晚清以来便伤痕累累,再经历此劫,终于荡然无存。因此我更喜欢气息近古的作品,除了个人的性格偏嗜以外,更希望用醇和尔雅来修复这些年毁损的社会关于美的体认,我之推崇竹庵的画作,实缘于此。
科班出身的画家,技术细节的娴熟乃是题中应有之意,而由兹进乎大道,却需要综合积累和机缘凑泊。
认识竹庵已经七年,有幸见证了他的画艺,由青涩而趋成熟的过程。在我朋友中,竹庵最具有古典情节,他不仅对文房雅玩多有见解,也躬自刻砚铭、制匾额,乃至兴构小园,颇令我等只会坐而论道之辈,慨然兴叹。嗜好既高尚,心地便明澈,笔下自然清逸。
未来时代,艺术更加多元,复古绝不是主流,但传统笔墨仍会保留一席之地,假以时日,竹庵必是此流派的顶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