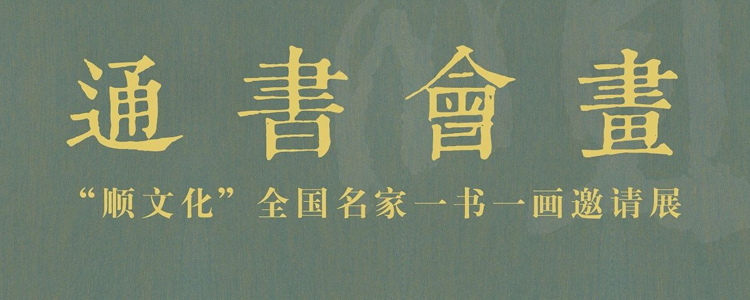
‘以八法合六法’ 刘 墨
‘书画同源’一说,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同,有人否认。
一般而言,主传统者,多持认同态度;主现代者,多持否定态度——盖主传统者,尚依从于文史传统,而主现代者,多主创新与风格。
本可各行其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惟‘书画同源’一说,影响极大,不妨在此稍作分疏。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追根溯源时,曾有‘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以及‘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说,但这是从书画分合的源头上说,并未说到它的美学价值与意义。
在中国绘画中,除了最高的‘气韵生动’的原则之外,就是‘骨法用笔’,它甚至排在‘应物象物’‘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之前——这意味着,‘骨法用笔’从建立绘画批评标准的一开始,就成为仅次于‘气韵生动’的考察对象。试看谢赫《古画品录》中的几则评语: 陆绥,体韵遒举,风彩飘然,一点一拂,动笔皆奇。
毛惠远,画体周瞻,无适弗赅,出入穷奇,纵横逸笔,力遒韵雅,超迈绝伦,其挥霍也极妙。
晋明帝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
(刘绍祖)笔迹历落,往往出群。 从这几则评语中可以看出,一旦绘画成为自觉的艺术创作,画家们就开始将绘画的线条与书法式的用笔力求合一——因为用笔的要点,在于洞悉笔性,掌握和运用毛笔所形成的韵律与节奏。尤其笔的运用,虽在于腕指,而实通于一心,越来越成为艺术家自身人格个性的直接表现。所以绘画能以抽象之笔墨表现极具个性的人格风度及情感,其捷径就是引入书法的技巧及其精神。
对于书法来说,它不必借助于任何具象的东西,而只以点画所形成的疾徐润枯,就可以表现吾人的情感。简言之,笔法体现了生命的节奏:‘……其后汉有蔡邕、魏有锺繇,得其遗法,笔意飞动,点画间一一成形。’
这里所说的‘成形’,非形象之‘形’,乃抽象之‘形’。
以笔法为基础,自然就会在点线的运用中迁入并表现画家的意兴、激情以及其他的精神活动,而如果一种绘画将外在形态和色彩退居其次,自然会向内走,于是中国画在后面的发展中,求返于自我深心的心灵节奏,并在画面上反映出来,赋予笔法以种种象征意味,便成立了。
而笔法的生机,也往往被解释为是书法进入绘画之中所产生的灵性意识的具象化。因为在书法理论中,笔法的运用不是几何式的或机械式的,而是人的内在无限可能性的投影,即它是优雅而精确的灵性表现。随后,美学家们赋予点线以浓郁的审美意味,无论是真正的书法,还是真正的绘画,都成为通晓宇宙人生的秘密和接触万象真意的一种方式。
而绘画也同书法一样,逐渐突破外在形象的束缚,集中映照于人的内在精神,即它摒弃了当初作为描写自然的刻意形似,同时也不迷惑于事物表象的华饰,而是抉取更为内在更为深入的本质,进而捕捉寄寓其间的精神意义,然后通过笔法的运用,给予这一切以尽致的表现。张彦远写道:
或问余以顾、陆、张、吴用笔如何?对曰: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名高宋代,时无等伦。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国朝吴道玄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授笔法于张旭,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张既号‘书颠’,吴宜为‘画圣’,神假天造,英灵不穷。众皆密于盻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守其神,专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吴生之笔,向所谓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也。
张彦远的这段描述,明显地注目于这些人在画中所增加的书法式笔力,这笔力也无不呈现出一种激昂顿挫、风行电驰的情势。换言之,在书法启示下的中国画风,不仅加入了笔力,也显著地增加了运笔的速度,从而使中国绘画的表现力获得了最高度的强化。
如果说,在张彦远那里,还是从根源上引申书法与绘画的联系,那么,在五代南唐后主时期的唐希雅(活动于十世纪),则是从具体形态上来进行书法与绘画的融合。此事见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纪艺下·花鸟门》:‘唐希雅,嘉兴人,妙于画竹,兼工翎毛。始学李后主金错刀书,遂缘兴入于画,故为竹木多颤掣之笔,萧疏气韵,无谢东海矣。徐铉云:翎毛初成而已,精神过之。’后来的《宣和画谱》也以这段议论为根本,却增加了一些新的内涵,一并录之如下:‘(唐希雅)初学南唐伪主李煜金错书,有一笔三过之法,虽若甚瘦,而风神有余。晚年变而为画,故颤掣三过处,书法存焉。喜作荆槚林棘,荒野幽寻之趣,气韵萧疏,非画家之绳墨所能拘也’——这里不仅可以见出书画在用笔形态方面的结合,更是从中看到了绘画书法化的精神。
尤其从元代以后,专门致力于点画结构的训练并在其中寄寓精神表现的书法,在绘画中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赵孟頫的‘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就不是一时兴到之言,而是成了创作的原则性宣言。甚至可以说,它直接导致了‘八法’(即书法)取代‘六法’(即绘画)的结果。
比如,比赵孟頫稍晚一些的柯九思,直接把各体书法的用笔以及它所包蕴的形象内涵与绘画的具体物象的塑造相联接:‘写竹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
固然,中国画家对书法式笔法的引入及应用,明显地弱化了绘画中的结构、色彩等客体形象,但也随之转移了欣赏者的目光——书法式的表达及其相应的美学观念经历了也造就了中国画家尤其是文人画家从‘外师造化’到‘中得心源’的转换。
对文人画家来说,绘画不再仅是人与其环境的一种对话,而且更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它甚至不用求助于外部世界仅用笔法所构成的象征图式,就可以进行表现与呈现了。
杨维桢在为夏文彦所著《图绘宝鉴》(一三六五)的序中指出:
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 这些观点都共同表明,画家应该更明确地将精力集中在对绘画中的书法意味的表现上。
石涛云:
古人以八法合六法,而成画法。故余之用笔钩勒,如行、如楷、如篆、如草、如隶笔法,写成悬之中堂,一观上下气势,不出乎古人之相形取意,无论有法无法,亦随乎机动,则情生矣。
石涛的这段题跋,大概有以下几重意思:一,书法与绘画合在一起,才组成‘画法’;二,绘画创作时的用笔中,结合不同的书体及其用笔组成气势;三,以书法合画法,造型、达意、表情,一以贯之,创造完整的艺术生命——物、我、笔、墨之间的无碍,体现了中国绘画独特的造型意识与表现意识。
另外,石涛还写过这样一首诗:
悟后运神草稿,钩勒篆隶相形;
一代一夫执掌,羚羊挂角门庭。
在石涛看来,想要取得跨时代的成就,就是在书法与绘画之间最完美的深层汇合上。
如今,传统的艺术观念早已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专业与业余等等的交汇中被‘打破’,固有的衡量标准已经‘失效’——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新的艺术形态往往会从这些‘实验’中产生。
《通书会画——‘顺文化’全国名家一书一画邀请展》正是在这样背景之下所做的‘温故知新’的一种尝试吧?
多撒种子多耕耘,必将有所收获。
二O二四年九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