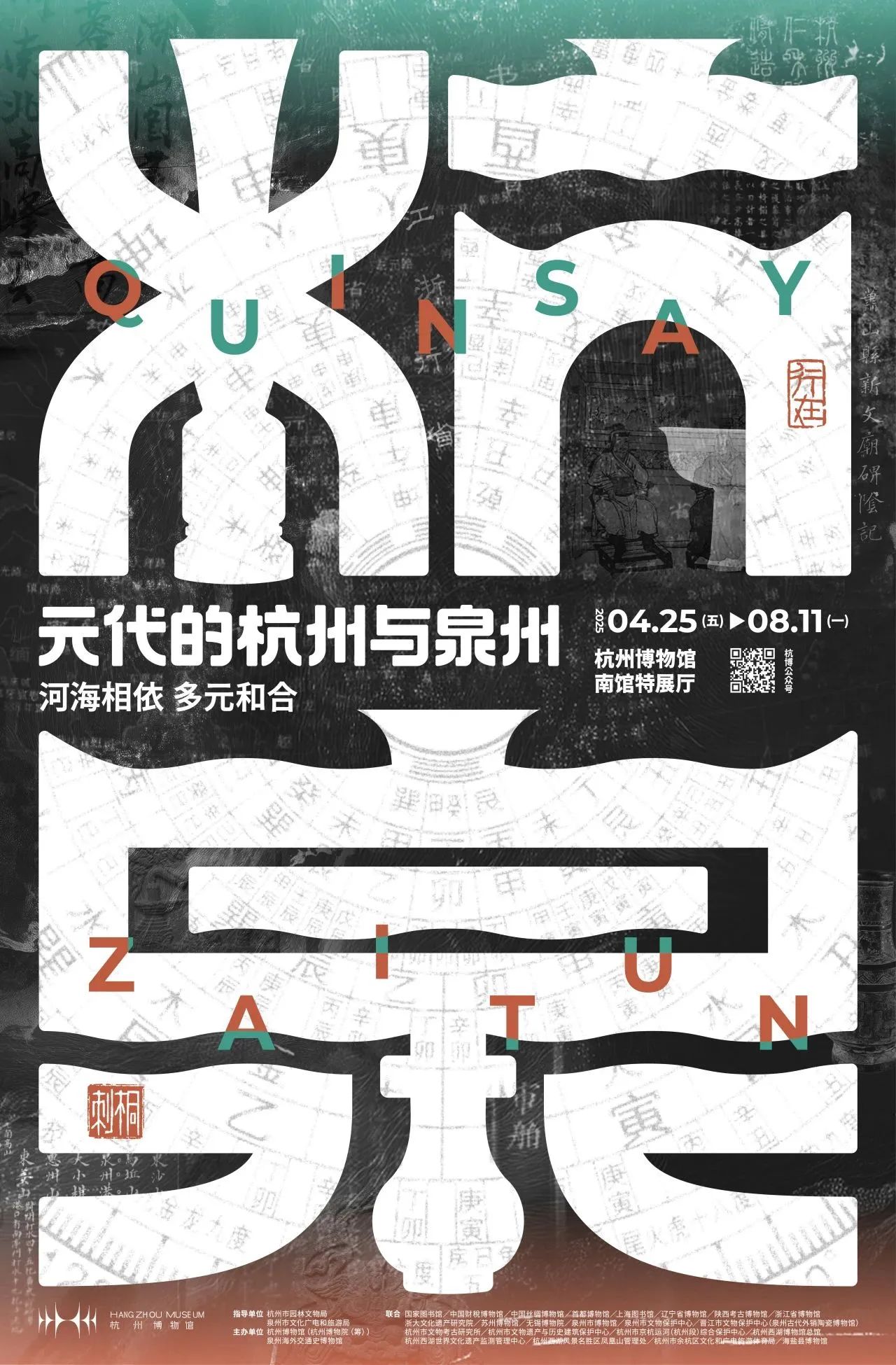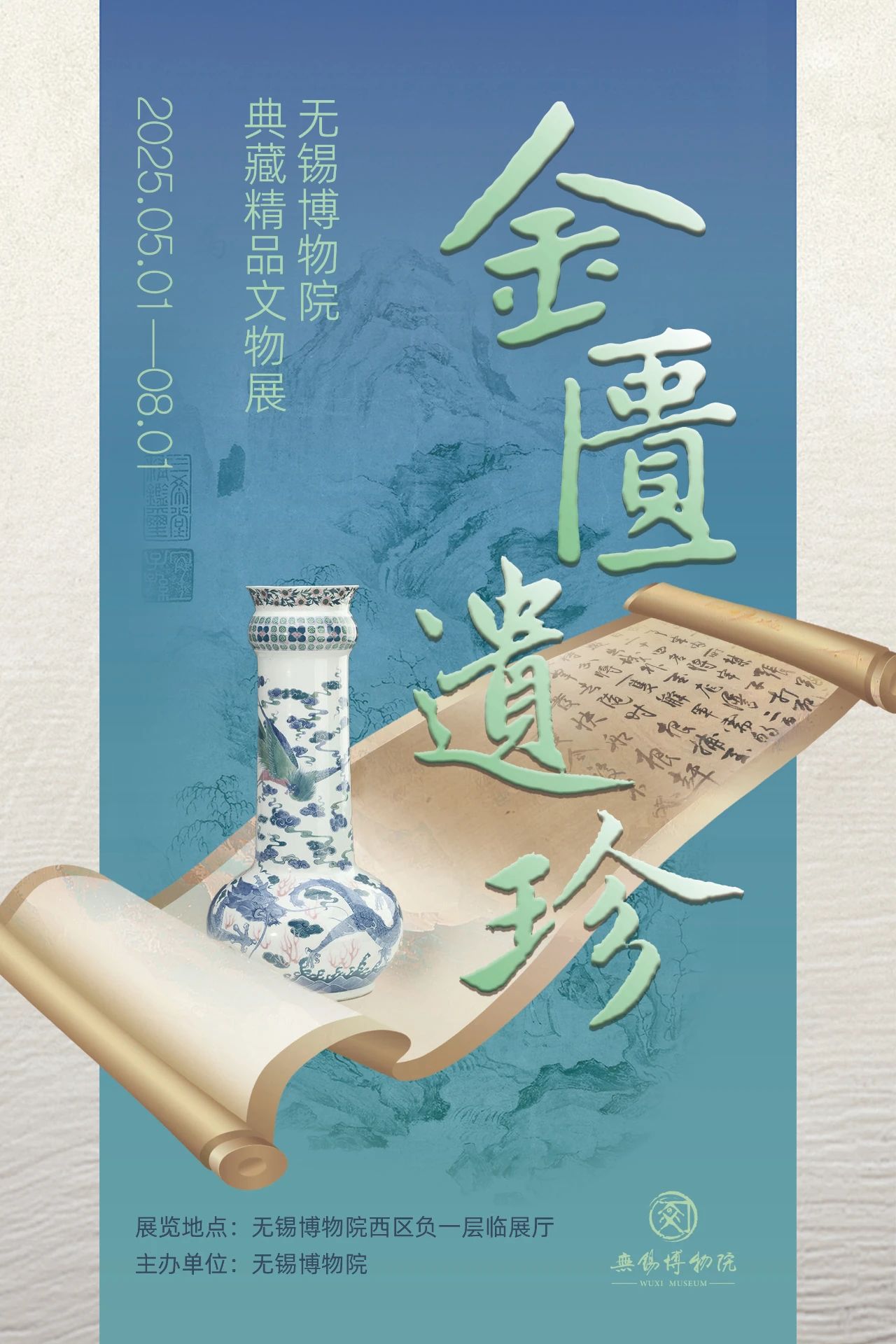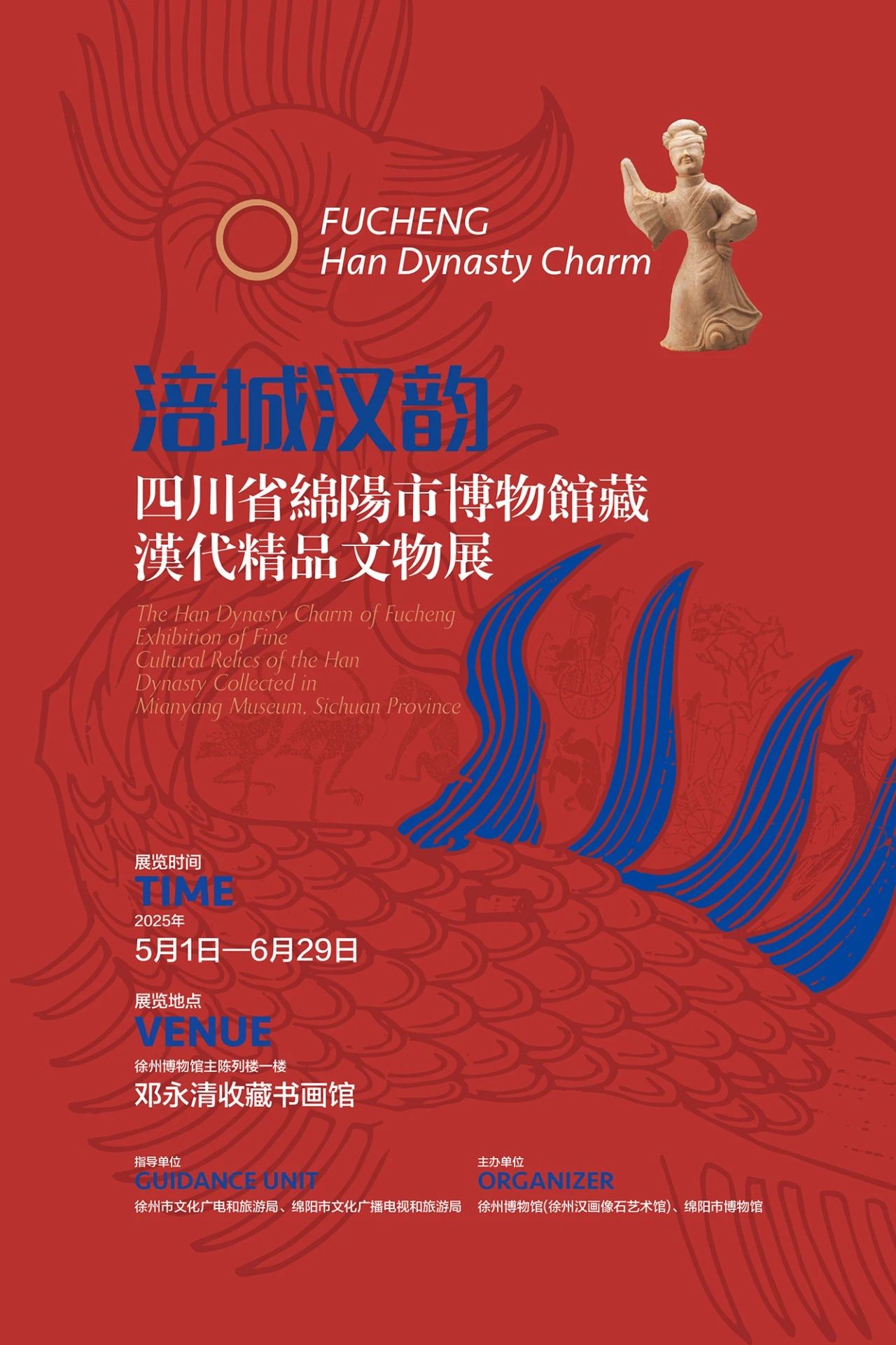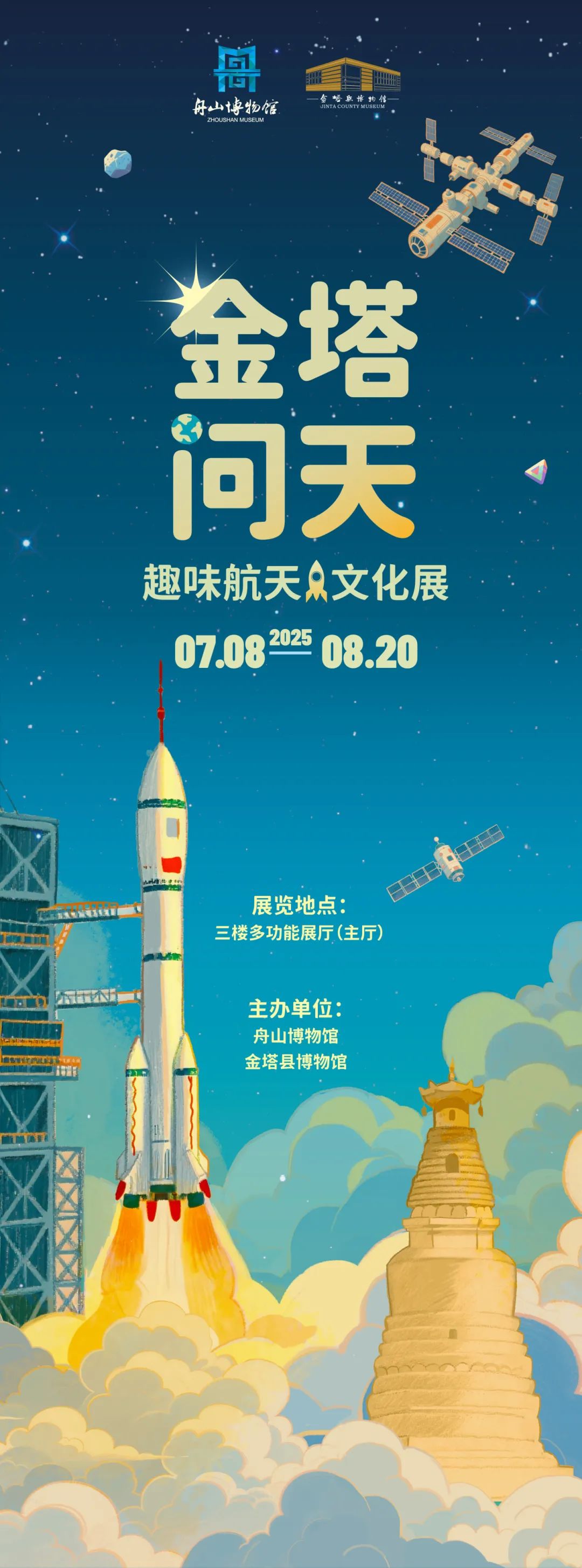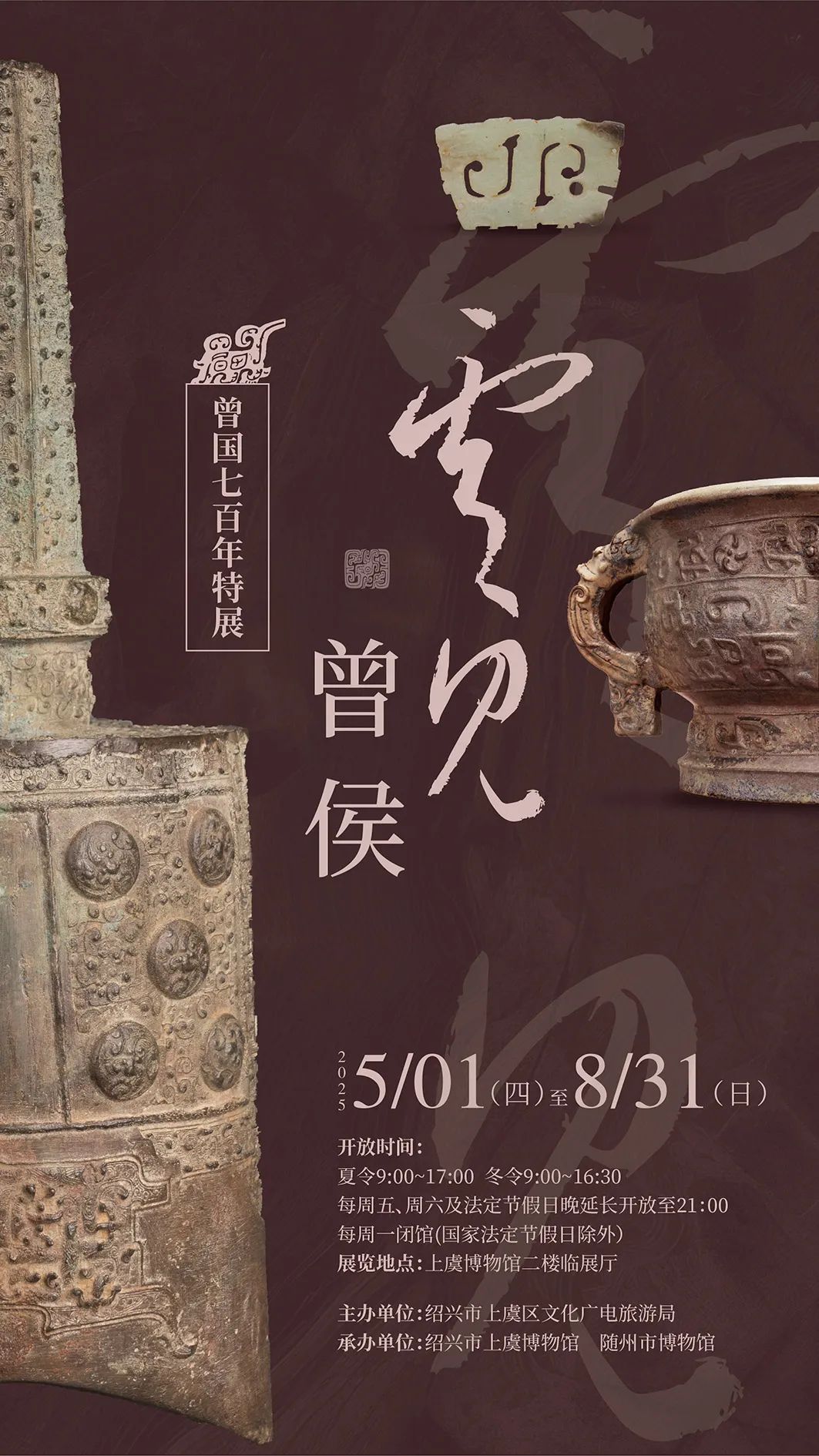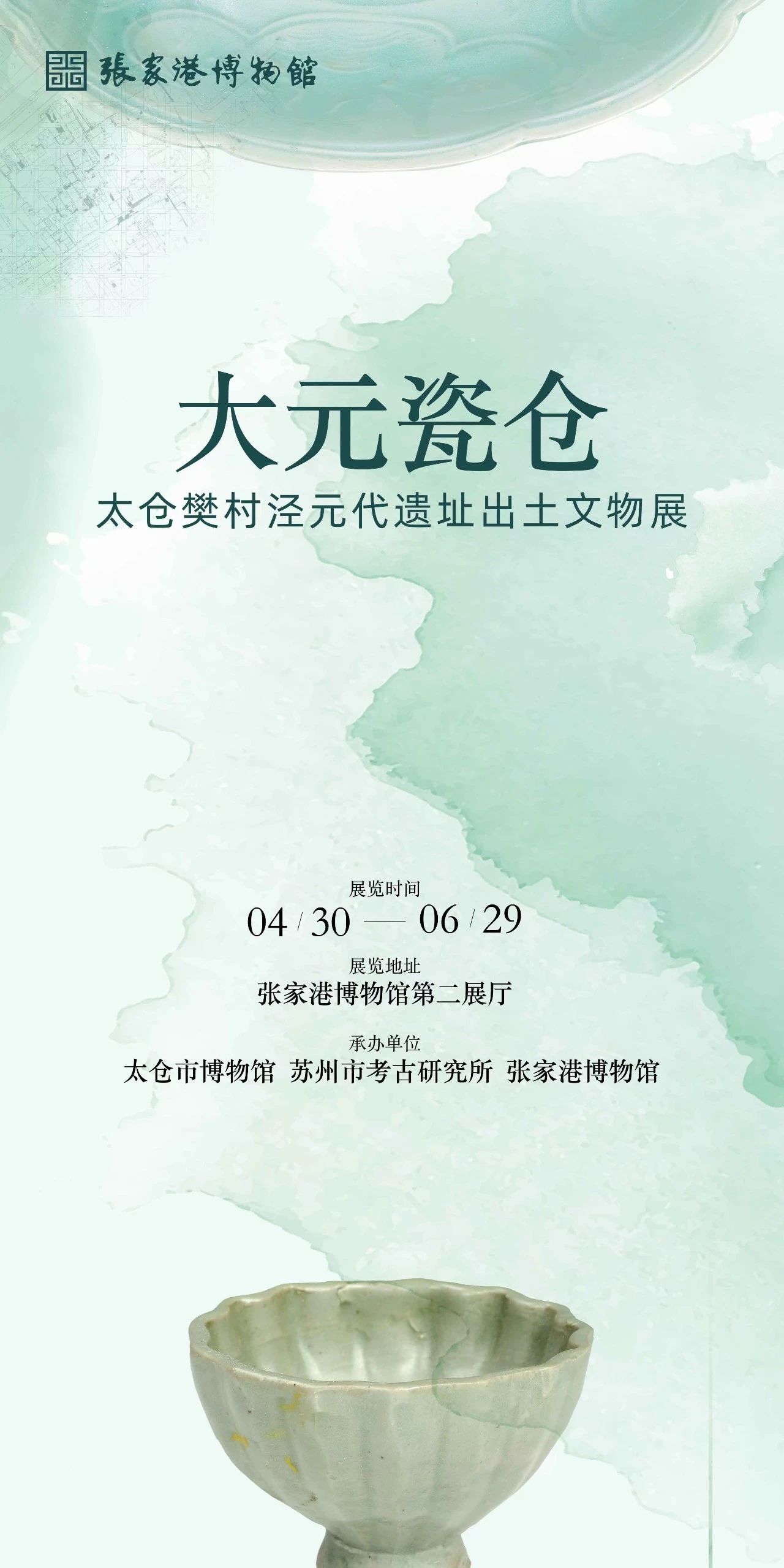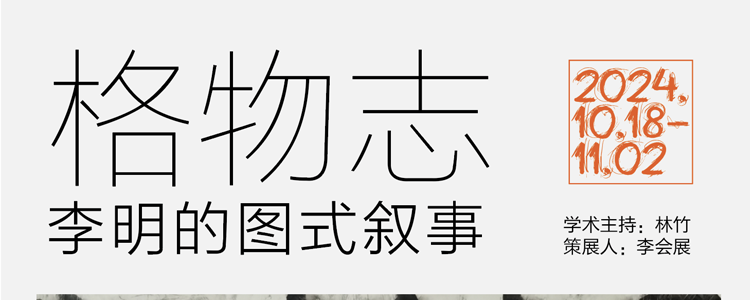
浮游,李明的图像笔记
文|林竹
2023年,一位挚友的意外故去,以及紧接而来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打乱了李明的生活秩序和情绪秩序,人在面对生死时,挫败感和无助会显得特别明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李明选择了闭门居家。这期间,他将家中闲置的一些时尚杂志、账单、礼品、包装袋等物品进行撕扯、剪切、烧制和粘贴,涂鸦上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最终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的这一批饶有意味的作品。
直至临近展览,李明依然一直在说,“这些不是作品,只是我这段时间每一个时间点上,被情绪干扰时随手行动所做出来的,一些没有明确指向的东西。如果有,也只是跟时间和情绪有关”。而李明并不知道,他的这个行动以及所完成的这批作品,其实正应对了马克思的“蜜蜂的劳动”:即使再蹩脚的设计师,他也知道他要设计的建筑最终的结果;而蜜蜂的劳动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预谋,只是凭着直接的重复行动,最终却建造出最为完美的蜂巢。李明的创作也像是蜜蜂的行动,遵循着感性直观的进入路径,在这个行动过程的深入中,经由经验、逻辑理性的分析取舍,最终呈现出一件件彼此独立,又各具完整面目的图式形象,或也暗合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艺术是情感和形式的统一”。
“艺术是生活的余象”(阿多诺语),李明的这些“生活的余象”,具有波普艺术的明显特征。它的破坏、撕毁行为的材料选择均在于现成品的商品包装及时尚杂志,可以理解为他对商业消费的依赖、参与,同时又抗拒消费的行动纠结,和对时尚潮流咨讯过度干扰的反抗。而以一种去现成物实用功能,去价值意义的行动进行组合重构,结合审美经验上的判断进行线条、色彩的结构修正,画面因此又出现了或安静、或激越的文人意兴的视觉现象和气息。这种气息正是李明长期以来所保留的对现实世界的观看习惯。一种屈子式的士人抱负不可伸的压抑和刘伶式“死便埋我”的率真相结合的中国传统文人的面世态度。因此,这也成为我定义李明这批作品为“图式笔记”的缘由。即,这些作品不存在叙事连贯性,它以语焉不详的意识进入创作,以情绪、经验上的自我认同决定画面的是否完成,呈现出基于即时情景的图像言说的碎片化。而集中放置在一起,又进入一定时间跨度中不同瞬间表达的精神意识与价值主张的统一性。进入“变动不居、周游六虚”的浮游的心路历程与表达。
区别于所谓“学界”的综合材料(拼贴)绘画研究,李明可能连半路出家都谈不上,只能说是“意外”的即兴创作。因此,很多人会提出:他是艺术家吗?以此来确认他的作品是否可以认定为艺术。而这种对李明身份的追问,其实刚好也回应了李明的身份,特别是放置于青岛地区的艺术场域。从作为综合材料创作的角度和时间长度看,李明是一个素人。但是从文字写作的创作角度,李明的资深又显而易见。自上世纪80年代青岛先锋艺术的萌芽始,李明就以艺术评论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包括后来的城市人文研究,李明的身影和眼光都未曾离开青岛的艺术圈。艺术之于李明,体现为积极的参与者与冷静的观察者矛盾并置的二重性。这种貌似割裂的二重性,不是相互掣肘的二元对立,而是互为参照的同向并行,也因此让李明在转化创作工具,从使用文字叙事到图式叙事进行创作时,得以顺畅地自由转换。并借由长期养成的审美经验和生命体悟,外化成作品中独属于李明个人的精神气质,一种与现实世界爱恨纠结的弱批判表达。这种表达,由对作品材料、信息的解构和重构,及形式的视觉美感来完成呈现。它是李明的态度,也是映射这个时代的现实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