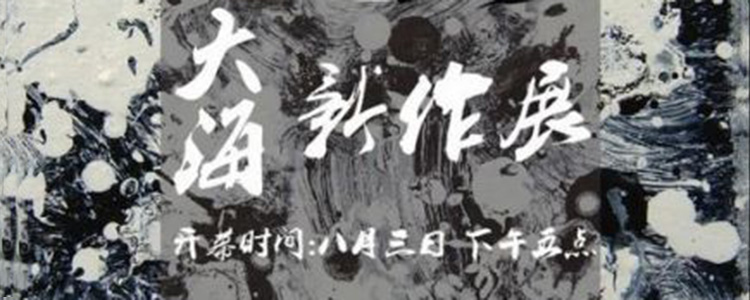
“世界存在着,仅仅复制世界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德国表现主义流派的口号。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表现性是绘画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架上绘画这一“舶来品”流入中国后,即在追求西方绘画形式与中国表现精神的“契合”,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种探索曾一度中断。今天许多人又回归到表现性的尝试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更是深谙只有以本土文化为体,油画形式为用,才能正抒写“中国油画”这一道理,开始了将中国传统艺术、经典文化融入西方艺术载体中的实践。我想,陈东杰便可算作一个。
陈东杰的新作《须弥山》系列,通过情景假定和错觉思维,使形象在绘画空间里的表现趋于“幻象”特质,并且形成自己独有的,符号化的创作展现。他用随意的笔触,在经过处理的底子上划圈、舞动、皴擦、旋转。描绘出极富个性的景象。我之所以用“景象”一词,是因为我不知该用洋画的“风景”还是国画的“山水”来界定《须弥山》系列的题材。第一眼观看作品,似乎嗅到了凡高般的梦幻、野性、奔放。细品之下,却又有中国大写意山水那乾坤斗转的神秘,虚无、涌动。那一个个富有动感的圈和线条,仿佛宇宙的黑洞,视线被牢牢吸引,难以自拔。而借助材料和笔触所创造的独特肌理,让这种奇妙的视觉体验显得愈发强烈。材料、笔触、肌理等等这些元素,在陈东杰的作品中不仅仅是技法,更是作品的构成,体现着画面的表现性。那时而浑厚时而透薄,时而刚硬时而柔和,时而粗糙,时而光滑,时而凝固时而流动的笔触肌理,赋予了作品张力,使画面生动而又充满感染力。
应该说,这些表现性元素是陈东杰内心的自然流露。既是流露,便不乏偶然的灵感。这偶然的出现,在陈东杰恰到好处的经营位置与把握下,非但不觉杂乱,反而在与心灵的碰撞下,产生了原始的悸动。虽有偶然,却并不能将作品等同于偶得,因为它们都是作者“师法自然”后“中得心源”的结果。
陈东杰用他的画笔和颜料描绘了主观的幻象,把握了世界的意义。在他特有绘画语言的探索中,传承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血脉联系的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