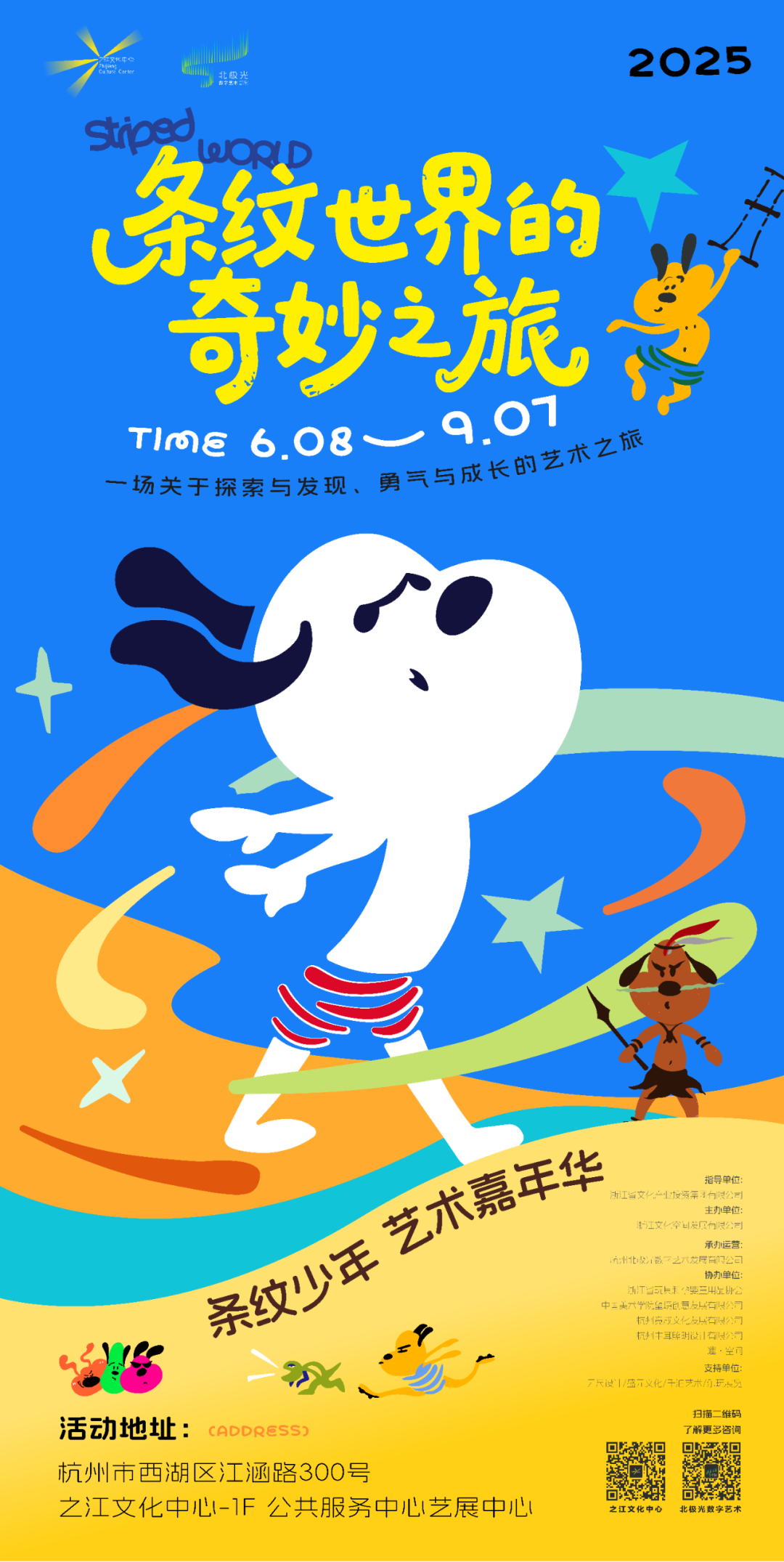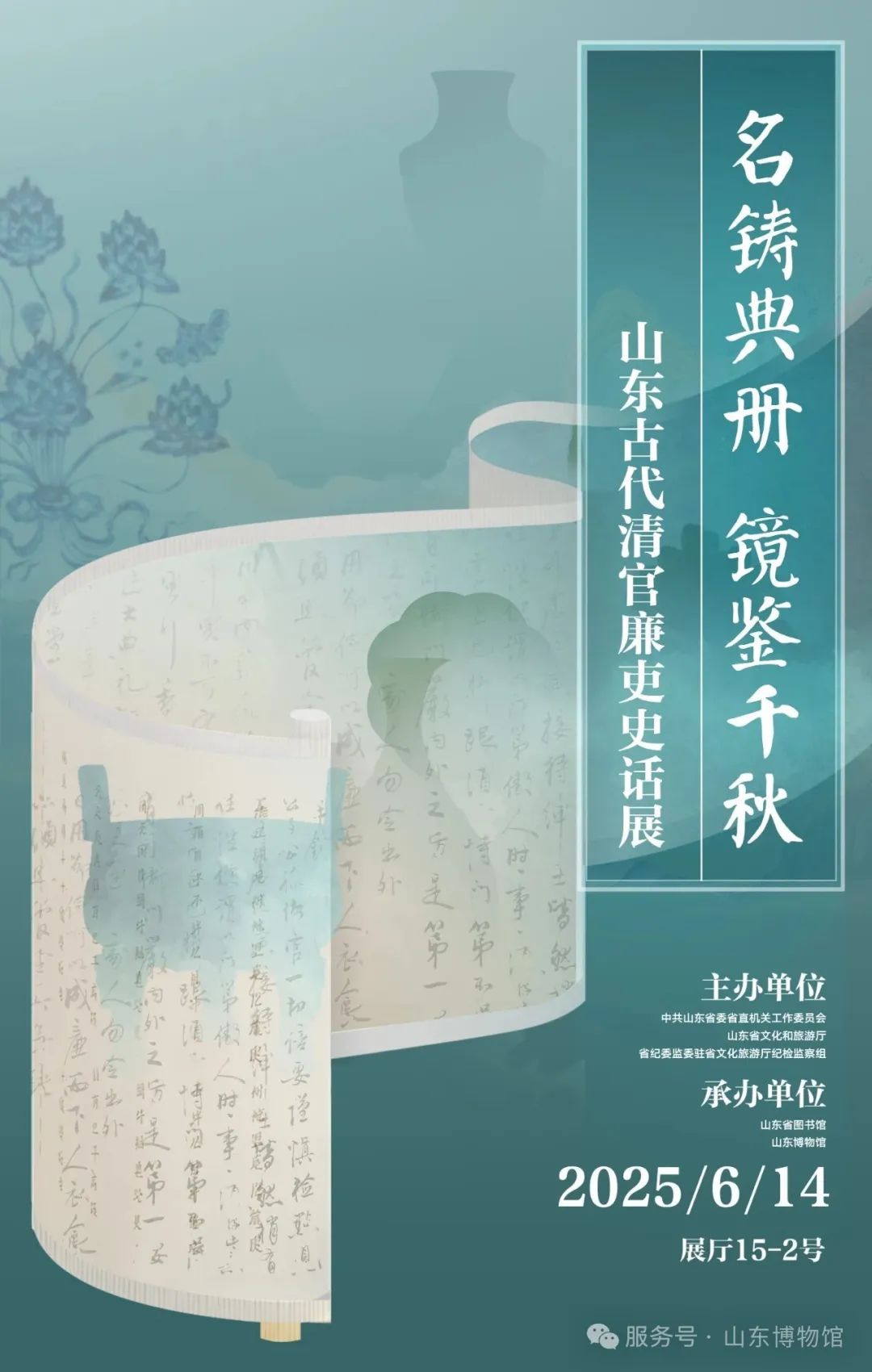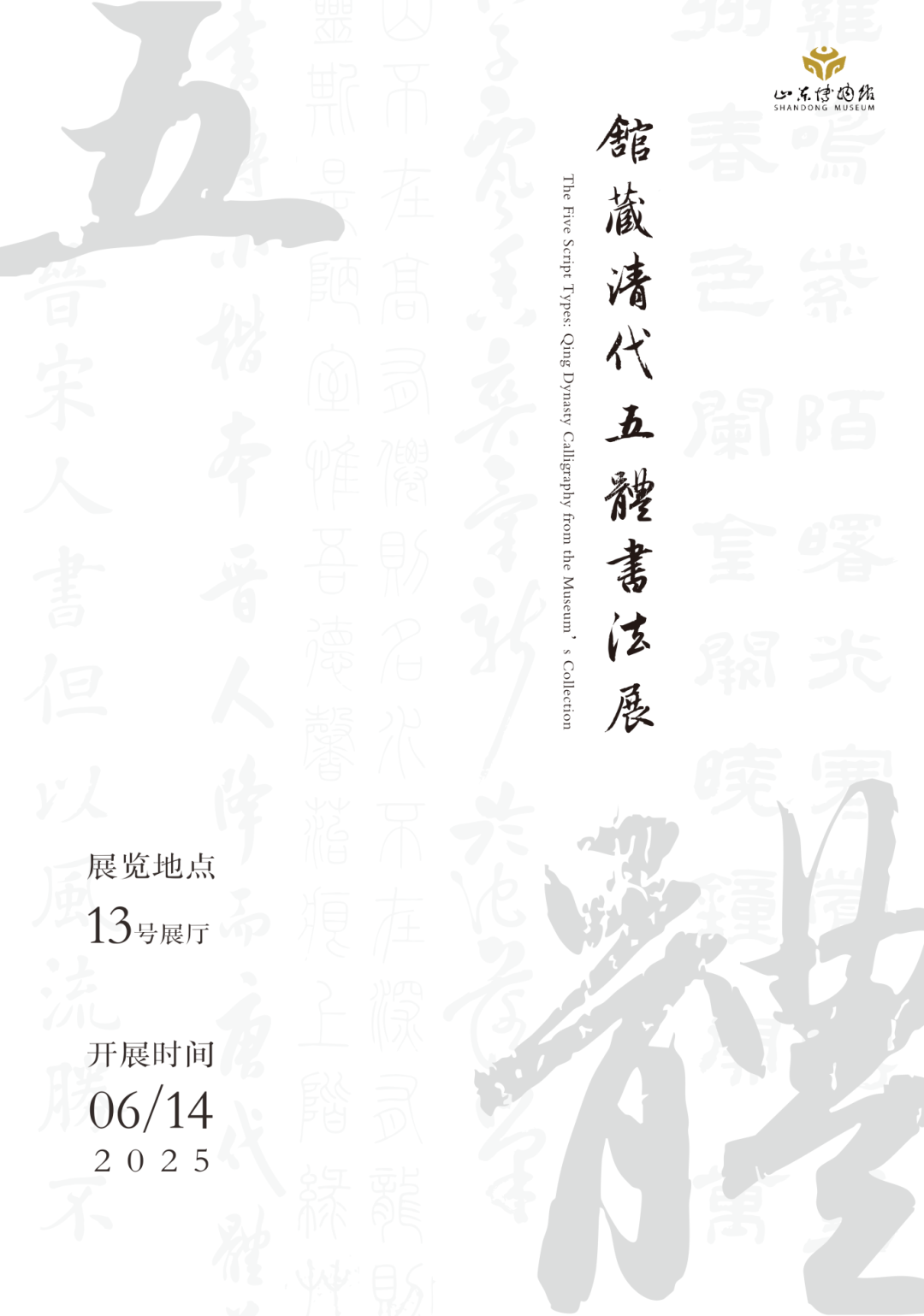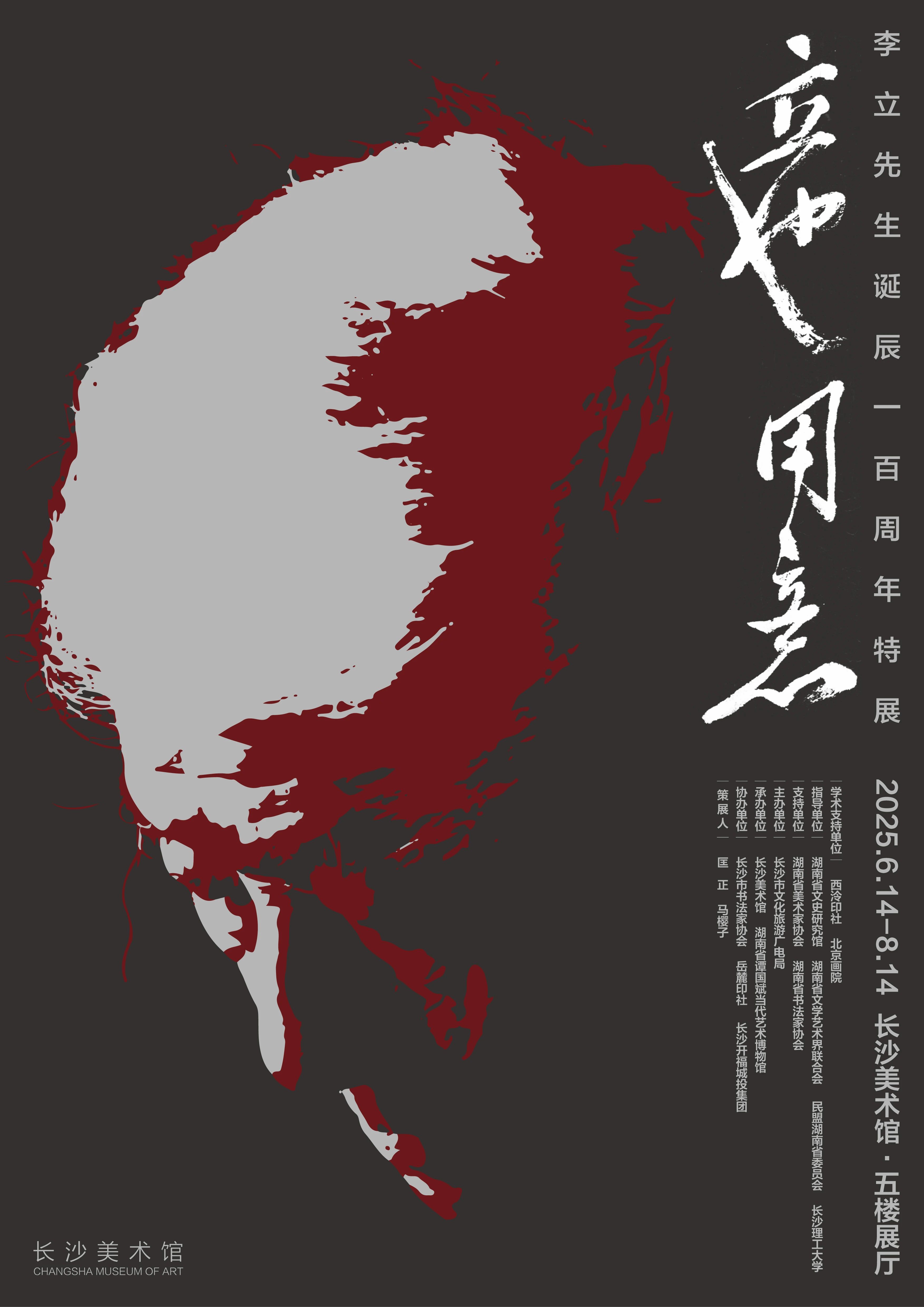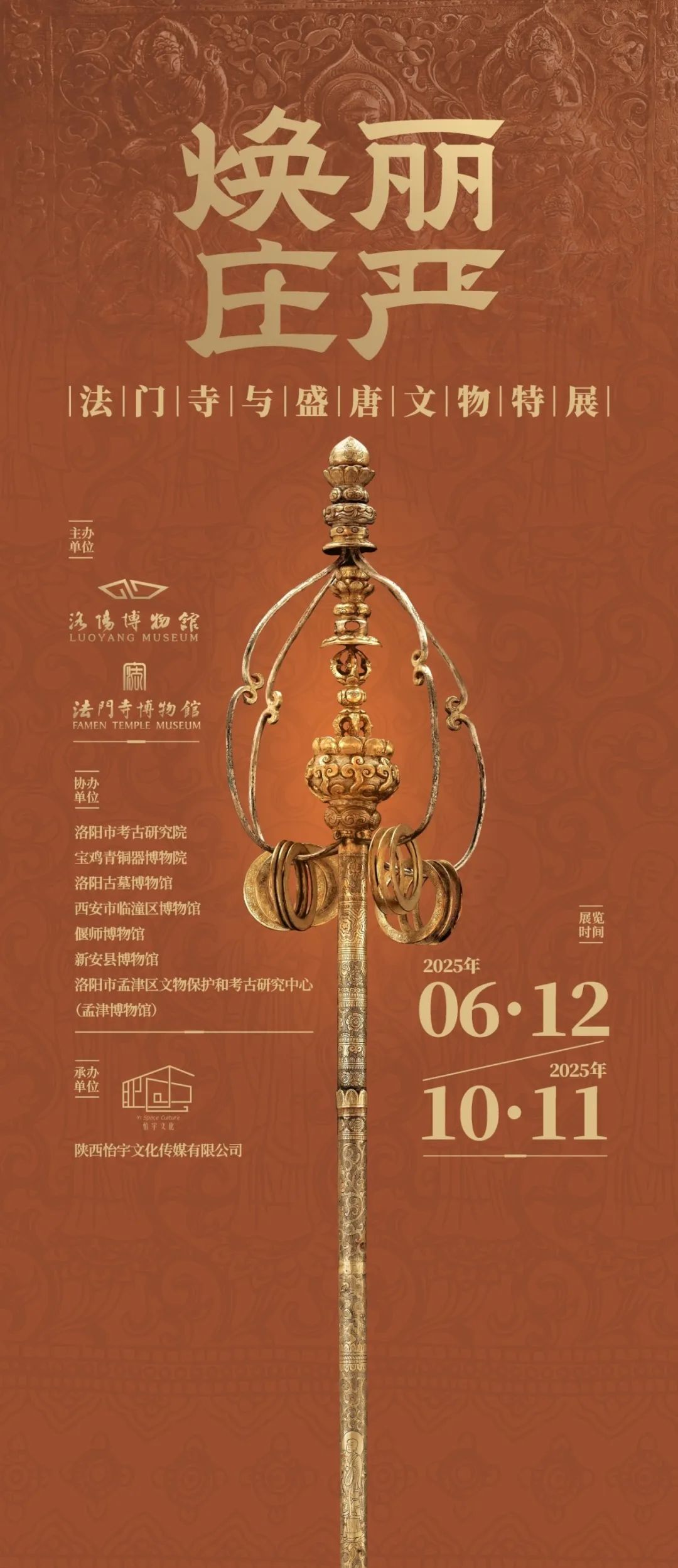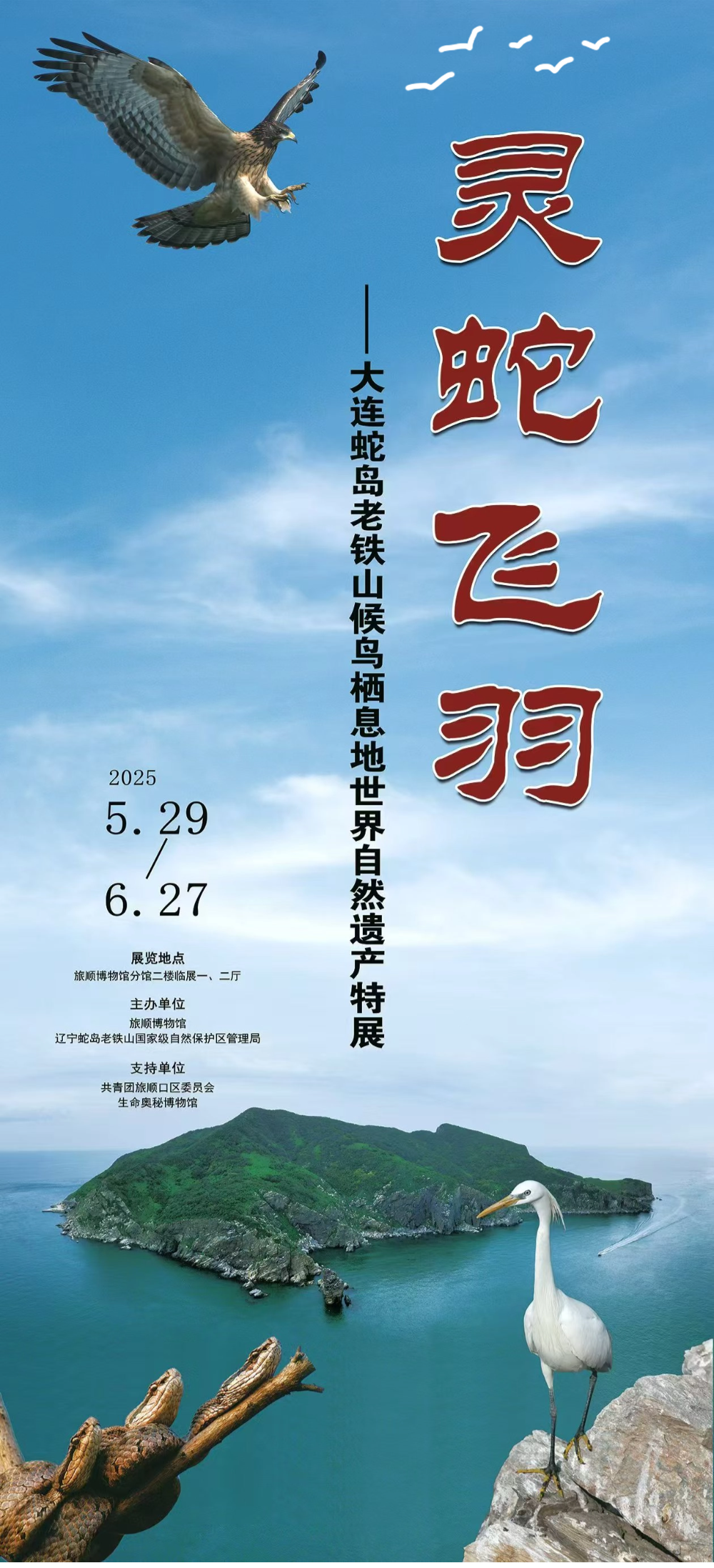濮水梳野:王永成的绘画边界与多重结构
文/侯昌恒
王永成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绘画语言的探索与拓展,他的这种不知疲倦的探索和拓展是来源于他的内心、他的激情,他的变不是为变而变,他的变是自然而然,是对人生的坚守,也是对世俗的对抗。王永成从水墨到丙烯,从具象到表现,他的表达方式一直处于不断的切换之中,收放自如。王永成虽然是中国画专业出身,但他认为媒介没有传统与当下之分,他并不想将作品局限于水墨领域,水墨也不是他纠结的概念。他一直在试图突破宣纸、绢本等传统媒材的承载边界,水墨、丙烯、水彩、水粉和色粉,凡是可用水性调和的材料他都乐意使用并陶醉其中,他通过反复的色彩叠加、反复的线条勾勒,建构他之于诗性表现的多重结构。
自2015年的纸本水墨《白月光系列》开始,王永成的画面呈现出短暂时期的宁静致远与神秘气息,他似乎在通过对中国传统的重新思考来建构他的“桃花源”;2016年的《儿时物语系列》又恢复了王永成发自内心的表现性,他用色粉、丙烯、彩铅在水彩纸上恣意挥洒,表达他对家乡曾经熟悉的记忆风景诸如矿区、厂房、山林、小河和破庙等进行不断的描绘与回忆,这是他对童年生活在记忆深处的映射;2018年的纸本水墨作品《迷踪系列》、《寻踪系列》和《野火》等皆以饱满的抒情性情感与强烈的表现性线条,使得作品表达极为纯粹而成熟,笔墨在画面上呼之欲出;2021年以来王永成在创作布面丙烯材料作品《漂流世界系列》、《树石山野系列》以及《梳野系列》等的画面中,他将枯木与怪石设置在特定的光影之中,用明快、稳定而魔幻般的色调呈现出一片荒诞而极具诱惑力的视觉世界。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说:“人生处在荒诞、荒谬之中,但人生值得一过。不管这个世界多么荒诞离奇,你都要选择活下去,但绝不苟活,而是活过荒诞。”加缪认为荒谬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直面荒谬,通过认识和接受这种荒谬,找到一种全新的生命意义。加缪强调反抗的重要性,在他的小说《鼠疫》中,加缪通过描述在对瘟疫的抗争中,展现出了人类在绝望中的尊严。王永成自2021年以来的布面丙烯作品《漂流世界系列》、《树石山野系列》中的枯木与怪石正是基于他之于对生命中荒诞的追问与感悟。从2023年个展《樗之大焉》到2024年个展《濮水梳野》,王永成思考将传统意象与现代表现在其作品中进行生成的价值与意义,他将“树”作为人类与自我存在的象征,以树的坚韧与承载,追问人类与自我生命的不确定性亦或可能性。
王永成属于哲思型的那种艺术家,他在创作的同时,也在不间断地阅读古典与现代的经典著作。王永成不仅对苏轼(1037—1101)的《木石图》中的枯木与怪石之于生命的价值进行思考,还对徐渭(1521—1593)《杂花图卷》中笔墨流露出的情绪进行转换,他更关注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的是他回归到绘画最本能最原始的状态,他追问赵无极(Zao wou-ki,1921—2013)在抽象背后表达的东方精神。近十年来,无论在创作材料、主题还是观念上,王永成一路拓展,最后他将目光定格于“濮水之滨”。在老庄思想的边界,他以“野”为描绘对象,以“野”为表达方式。在山野的空间中,王永成找到了他自由表达的自留地;在山野的气息里,王永成承接到了他精神舒缓的能量所。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在其著作《存在与虚无》中,通过对虚无与存在相互塑造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人类可以通过不断超越自身、面对虚无,实现存在意义的塑造与重构,即存在与虚无是可以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从而共同构成一幅人类存在的体验场域。萨特认为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宿命,人必须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一系列选择,正是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可以赋予外物以意义,但作为主体的人必须对自己的所有选择承担全部责任。这与《庄子·秋水》中庄子(约前369—约前286)“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的认知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王永成追求自由与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态度高度契合。
本次以《濮水梳野》为主题的展览,王永成以“漂流世界系列”、“梳野系列”、“树木山野系列”、“竹石图册系列”、“隐匿的诗系列”等系列作品梳理了近年来他在材料、主题和观念上的探索与拓展,同时他也建构了一个“存在与虚无”的多重结构性场域。在梦幻般的色调(外物)与极具力量感的树干(主体)盘旋中,具象、表现与写意在交织与互动中阐释了王永成对生命哲学的书写:自由与自我、存在与虚无、荒诞与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