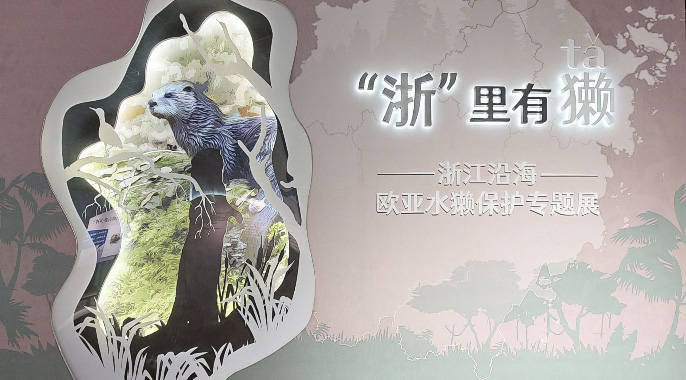策展人语:
后神话与后自然
——王旭的绘画艺术
艺术家王旭,以南阳本土文化为原点,广泛学习国际当代艺术创作成果,纵横捭阖,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他具有开阔的视野,饱满的热情,纯粹的创作状态,艺术眼光犀利而高远。在艺术创作上,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绘画语言和审美经验。是当代真正对艺术有思考、有观点并对艺术抱有理想的艺术家。
当代艺术经历现代、后现代以后,艺术由跨文化变成超文化,颠覆和解构了传统价值,更具包容性,在表达上也有更多的可能,艺术的观念性成为表达的核心。而视觉新秩序的建立使各种表达得以实现。以自身为现场,自我塑形、自我感受、自我体验,把意识形象化、视觉化、意象化,自我成为文化景观,以此抵御消费主义及其暴力等对艺术的规训和倾轧。
后工业时代以来,技术科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也改变着我们的思维和认知。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文明和民主的社会形态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也是人类发展的最优方向。与之相反,在意识形态落后的社会中,启蒙理想在迅速褪色,权力在高科技赋能下更强化对人的控制,最终将覆盖所有个体及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然成为反噬的利剑,加剧了人类生存的困境。
王旭的作品,深度思考社会问题对于人的塑造和干扰。把个人叙事转化为人类集体的叙事,个体经验转化为集体经验,个体处境转化为群体处境。这不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当代人类的共同话题,是对现代政治、消费、人权等的深度介入,是对社会危机、人类生存危机的关注和拯救。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击水独山下》,来源于王旭一幅作品的名称。独山又称玉山,是南阳地理、历史、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和丰富的神话传说。关于南阳独山的神话传说至今在民间流传,构成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根基和朴素积极的价值取向。
最初的创世传说,是人类关于原初的哲学思考,是把人类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建立自己的社会秩序。是一种人格神在原始自然主义的确立。神话叙事的语言结构是去自然的或者说是与自然对立的。随着技术科学的发展,人重新被定义,被解构。借助艺术重建思维,回到自然叙事的语言结构之中。
王旭的老家遮山,是南阳历史坐标中的九架孤山之一,也正是南阳神话系统中的重要地域。意味着生命之源的故乡,是王旭生活的原点,也是王旭精神的出发点,他的艺术创作也必然会与此地的人文风物发生联系。南阳地域性的、标志性的景观,有意无意出现在王旭的画面上。外部的生存境遇与内部的精神景观互文和对照,人文历史和神话传说深沉的融合,山的孤独、水的自由、故乡神话的磅礴浪漫,都在画面中若隐若现。故乡的神话是关于大地的修辞、是历史文化的符号,更是绵延于历史长河中的内在精神。王旭作品中地域性符号的运用,正是当下生活和精神的自然投射,或者说他在画布上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一种独立的精神世界,一种后神话的语言系统。
王旭作品所呈现的气度和精神光芒,是直面当下的思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灾难时代,疫情让每一个人深陷其中。王旭以个体的生存困境为出发点,面对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脱离了单纯的民族性、地缘性和文化性,思考并展现了当代人的无奈和无助。作品饱含热情,充满力量。似乎是一种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的表达,但本质上是一种隐喻和象征。是一个人的孤独和沉思,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和状态。
当代艺术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审美艺术,而是一种重新解读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它是艺术家观察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因此它不是一种结果,而是过程,它建立在对既有认知的颠覆和反叛之上。身处以信息化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环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是指向国际环境、消费环境、意识形态环境等多重意义。
当一种绚丽的色彩、意象化的物像,无不彰显着消费社会的特征,人的生存究竟是在什么语境之内的?是自然的,是知识的,还是逻辑的?不同语境下的群体和文化,只有回归自身,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才是当代艺术的本质所在。当代艺术追求一致性表达,在不同的境遇中,创造出更合适、更准确的表达方式。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生存问题,是社会问题,艺术就是对这一类世界性宏大叙事的质疑和思考。
王旭的作品,远离客观性。画面中的人物、山石、树木、鸟兽、水果等,以符号化的视觉元素切入到表达系统。它们只是形象化的存在物,并不具备现实的质感和自然状态,彻底回到物性上。它们活动的空间,随着心境在改变、生成。
王旭作品画面的主体形象通常是一个人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纯自然意义上的,脱离族群、身份性别特征的人。这个类似裸猿的形象和树木、鸟兽、河流等自然物纠缠拥抱,在画面中肆意蔓延、生长,丑陋、疲软。像一个失去光芒的,疲惫的,被捶打的生命。它在挣扎,有时目光呆滞,表情涣散,对盛放身体的空间毫无反应。有时又拉长了躯体,似乎在捕捉转瞬即逝的时间。凝固的动作,超出了正常的活动局限,随着身体在自然延伸。这是一个卡夫卡式的生物躯体,也有着达利般的漫漶和粘稠。自然物都是他意识的幻化之物,或者就是他身体的分解之物。他让物体自我呈现。在无力的世界里,物因为与人的相互依存而显现,物更纯粹、更本质。这是物的自我显现,自我照亮。它以内在的光对抗自然,对抗世界。
王旭作品的色彩明快,亮丽,如同跳跃的阳光。他用纯色把来自于世界的困顿、阴郁和不快,依附于生命中最常见的事物,铺满整个画面。饱满,炫目,如同流动闪耀的光芒。《一个人的日月星辰》,如同一个灿烂辉煌的梦境,像极了小时候的某种场景——一种梦幻,一种想象,一种对未来世界的期待。但成年以后再去观望,浪漫变得沉重虚无,犹如美丽的幻像。世界在这一刻发生转移。
艺术是人的行为,是人关于视觉经验的表达,更是自我关于世界内在感知的表达。因此艺术的核心必然是关于人和这个世界的思考。这样说似乎接近哲学的定义,但谁又能说艺术不是人类生存的视觉表达呢。随着工业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深入,人类进入到更高级的生存状态,作为自然的艺术和自然的人逐步被技术所替代,进入人造世界的时期。无论是从德勒兹笔下的培根的“形象”,或者贾科梅蒂式的孤独,或是巴特尔的符号学的归纳谈起,我认为王旭的创作,或者说他内心的外溢,意识的幻化,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符号形象。因此他的作品便有了艺术学和哲学的深度和结构。
当代艺术家都有着创世的精神,都是自我的上帝。他们通过视觉语言,重建一种基于现代社会的认知结构和秩序,以此揭示世界存在的真理性。王旭的作品以当代的创世精神,呈现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生存秩序和期待。从自我生存状态的现实到精神层面,变大自由度和敞开性,摆脱具象的束缚,做到了自由的表达。兼具后神话的附魅和后自然的祛魅。因此,整体来说,王旭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在技术时代,重新回应生命和自然的关联与纠结,在浩渺虚空无意义的宇宙之中,他自我塑造、自我成就,从而拥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