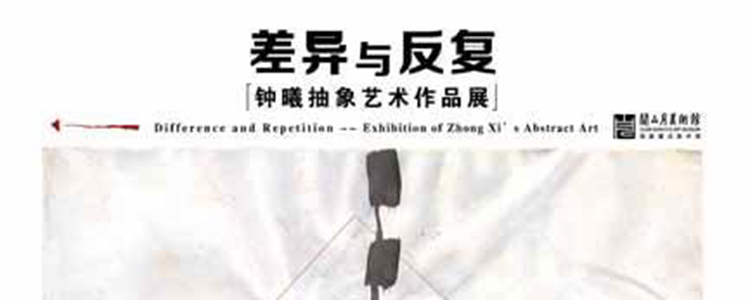
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德里达运用解构的思想分析集中阐明了延异这一他自造的概念的内涵,它标志着一种各自差异的运动—迂回、间隔、代表、分裂、失衡、距离—的纯粹统一。所谓“延异”,即延缓的踪迹,它与代表着稳定的语言--思想对应关系的逻格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德里达认为,语言无法准确指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只能指涉与之相关的概念,不断由它与其他意义的差异而得到标志,从而使意义得到延缓。因此,意义永远是相互关联的,却不是可以自我完成的。
在我看来,钟曦的绘画更多的指向一种哲学思考,以他精心的艺术构建将抽象艺术引向了哲学的推演,他早就敏锐地看到抽象艺术的形而上的批判背后,存在着对于外在形式符号依赖性的指责与抽象艺术转向更本质的寄望。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的抽象艺术家有着根本的差异。事实上,他从未放弃对于抽象绘画的某种本质的东西的思考,他认为如果抽象艺术缺少了一种直觉的基础,我们就会失去抽象的某种内质,就会滑向被遗弃的危险,那么,抽象的一切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而反反复复的差异性追逐与他要解构的话语,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的形象阐述,语言的模糊性与未定向的明晰性实验,为其抽象世界的建构打开了一扇差异与反复之门。
具体来看,在钟曦的绘画中延异作为一种观念,包含着直觉性和间距化的双重意味,不仅将有关符号的任意性和差别化的意义上从根本上取消了直觉性的质疑,并通过差别异化的时间性痕迹的嬉戏,使得抽象性的指涉被“历史性”地构成为差异的编织物,表达了对意义构成的感性追求。他不断地去打破既有的规定性,不受任何限制,试图超越抽象语言的传统痕迹,并在超越中针对书写的封闭性结构,反复进行线与形的有限性游戏,一方面希翼彻底打破传统抽象语言的形式结构和意义结构,另一方面希望在差异的构成关系中扩大创作的自由维度——解构传统符号结构受传统形而上学束缚的本质特征和形式表现,寻找破坏和超越传统符号结构而达到实现符号无限差异化的途径;以类比化的符号形象结构,建构解读式的 “类符号”书写与言说。这些表面上各异的抽象图形在精神上却一致突出了差异化、异质性、多样性,突出了对同一性的形而上学思维的超越和拆解,在本质上与传统的抽象思维习惯相对抗。
一切感性显现物都包含了其内在的本质内容,这种内在的本质规定性一旦被思想意识到,这就是精神。钟曦认为,感性的显现只有通过差异化的反复才能在类符号的游戏中找到当下的根本性开启。因为,要想让抽象超越为一种实存,就必须让人意识到反复就是差异,差异就是反复,于是寻求抽象意义的行为就和寻求世界的内在结构的活动一样,和一种生存体验相关,与我们眼睛可见的或不可见的相关。也就是说,可感的现象是不实在的,而通过我们思想所把握到的东西才是稳定的、普遍的——可感知的世界才是本质的世界。
钟曦的抽象绘画,明显地向我们展示了对诗与思的话语存在——话语的多重隐喻与书写的反反复复,让感性生命活动自由地流淌,任性而为,这或许是最终所追求的生命境界。语言传达的瞬时性以一种物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在体验的知觉和内在体验的记忆中让符号的意义永不固定,在时间的延宕和空间的分延中形成丰富多彩的语言游戏。这种语言游戏并不只限于符号的领域,也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差异化的转换形成不同向度的流动或静止——线与线的每个交织与构造、反复标记的边缘与节点都无限延伸,在自我的延宕与分延中不断自我生成。空白与间隔、覆盖与保留、边缘与踪迹等等都可以是双重的表示与书写。事实上,这样的绘画作品如按照传统的解读模式去解读是难以做到的,但借用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来解释就可以,这种非确定性的书写模式即多样性的相互交叉的模式。在反复和差异之中,是和多种语言游戏相关联的一种自我生成式的书写,凝固在书写中的各种可能性,构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文化生命体。以书写的特定行为而产生的无限可能的差异性,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延异,表达了某种欲望的张力——由内而外、重复替代、对调转换,形式被预设又被拆解,结构被固定又被解构,非确定性的知觉似乎总是被纳入到某种历史的意义之中,寻求意义的自我呈现又独立于语言之外。如果我们通过试图从某种传统的角度去思考其作品中对符号的意指是难以理解的。
钟曦所要寻求的抽象本质是一种想象中的流动,即在语言空间的变化中摆脱结构主义的限制,延异和撒播混沌不清、偶然又必然、同一又差异的世界感观,呈现彼此的差别与自身的存在。他的抽象书写是一种创发和变异的书写,迥异于传统和当代抽象创作的各种进路 ,即有一种散漫无序的感觉,却又是一种思想困难的书写。他的书写的方式是在幻象的变异中从“物—象”,到“形—象”、再到“语—象”、直至“幻—象”的延异。“幻—象”是可见之中的不可见,交错重叠在万象之中。用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的“显隐”理论来看,即幻象具有显现的维度和隐性的维度的两重性,幻像与幻象的交错和重叠不能理解为表象化的对峙。在笔者看来,钟曦的幻像世界总是在消解和转化,只有通过幻像的变异踪迹体味幻像。钟曦不断以“反复的迹线”进入幻象书写的追寻。经过书写的变异,转化为变异的书写——变异的书写是不被书写的书写——随时涂抹、逆转着书写的对象,但同时又尽可能地紧贴着所呈现的历史和文化、踪迹和结构的限性,以及对自我立场的消解。书写的这种游离状态也表现为从一个“幻像”到另一个“幻像”的链接,如同人生的反复书写,回应中止的命运,构成自我的境界的生命共通体。这是一种真实的状态,也是一种主观的感觉,这种主观的感觉因反世俗的内心执着而显得宝贵——一次次反复的涂抹,不仅消解了经典的意义;甚至消解了涂抹的彻底性,只剩下涂抹本身——消除了个体生命书写中的变异,或者说,变异的书写是形成生命个体书写——不可能书写的书写,并以此质疑变异中的异质性。正如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引》一书中所说“只有在不懈地自我延异中才能成为当下”。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钟曦的抽象世界已然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域,并提供了一个可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视界与平台。
展览具体分布:
历路:语言的转向。钟曦从《失落的羽毛》到《远方》再到《夏季的风》《远古与未来:落差系列》,从《净地》到最近的一系列作品,语言不断发生转变,追求越来越纯粹化的个性语言,在反复和差异化的多种语言游戏中,以一种自我生成式的书写方式,书写各种可能性的抽象表达,构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文化生命体。
延异:一种哲学的思考。德里达的延异这一概念,标志着一种各自差异的运动—迂回、间隔、代表、分裂、失衡、距离—的纯粹统一。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钟曦的抽象艺术更多的指向这一种哲学思考,其艺术的形而上的批判背后,存在着对于外在形式符号依赖性的指责与抽象艺术转向更本质的寄望。
书写:差异与反复。钟曦的抽象绘画,明显地向我们展示了对诗与思的话语存在——话语的多重隐喻与书写的反反复复,让感性生命活动自由地流淌。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差异化的转换形成不同向度的流动或静止——线与线的每个交织与构造、反复标记的边缘与节点都无限延伸,在自我的延宕与分延中不断自我生成。空白与间隔、覆盖与保留、边缘与踪迹等等都可以是双重的表示与书写。
本质:变异的书写。钟曦所要寻求的抽象本质是一种想象中的流动,即在语言空间的变化中摆脱结构主义的限制,延异和撒播混沌不清、偶然又必然、同一又差异的世界感观,呈现彼此的差别与自身的存在。经过书写的变异,转化为变异的书写——变异的书写是不被书写的书写——随时涂抹、逆转着书写的对象,他的书写的方式是在幻象的变异中从“物—象”,到“形—象”、再到“语—象”、直至“幻—象”的延异。一次次反复的涂抹,不仅消解了经典的意义;甚至消解了涂抹的彻底性,只剩下涂抹本身——消除了个体生命书写中的变异,或者说,变异的书写是形成生命个体书写——不可能书写的书写,并以此质疑变异中的异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