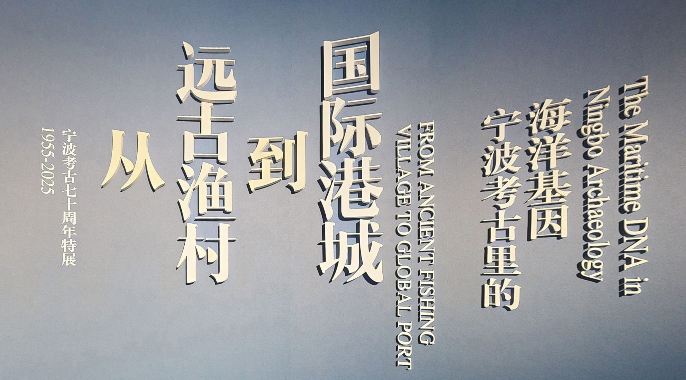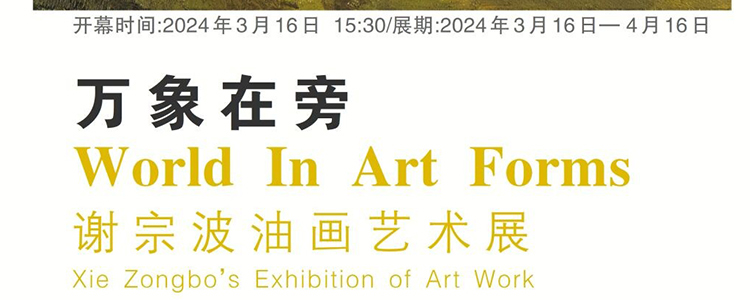
万象在侧,直抒我心
——我看大波的画
在大波的画里可以看到一种喷薄而出的生命力量。
熟悉大波的人都知道,他一肚子的豪气,却不甚擅于言语,往往兴致到了,就用粗厚的大手一遍遍地拍着你的背,嘴里除了一连串的“哈哈哈”外,说不出别的什么。他把一腔热情诉诸了绘画,他的绘画一定是远胜于他的语言的。大波是个热爱生命的人,但不是以悉心呵护、岁月静好的方式,而是呼吸相闻的贴身肉搏,用血与汗与之绞缠在一起。生命里有许多不如意,甚至是痛苦与灾难,但并不妨碍我们去热爱生命——如大波的画里展示的那样。
大波热爱古代文化,他工作室里堆满了淘来的、捡来的、土里刨来的远古物件,自珍自赏,乐在其中。这两年,他又一头扎进了书法和篆刻的世界,甚至买了台切割石头的台锯放在工作室。我知道他不是喜新厌旧的猎奇,也不是人到中年的附会风雅,而是要在书法和篆刻这类具有书写痕迹、情绪表达、动作凝结的方式中,找到与他绘画冥冥中连接贯通的地方,换个视角重新审视绘画。前段时间,他高兴地通过电话告诉我:他从古玉的砣痕里找到了与自己应当如何用笔和发力的答案。
大波不是那种深思熟虑的创作者,他的方式是即兴的,但又崇尚手工与心力的能量。因而,虽然有些画简单得几乎潦草,但更多是刀劈斧斫与反复堆积的痕迹。
在油画的体系里,从平面到立体、从概念到鲜活、从填描到涂绘……无一不是经验的积累与技术的“进步”。作为还原对象和审美创造的智力活动,我们面前有太多的标准与法则,这是大多数人接触绘画门径的必经之路。哪个学画者不曾为自己笔下突然冒出了圆融老练的色块而沾沾自喜呢?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进步”,是以损失某些天性或本能的代价实现的。庆幸的是大波并未自以为英明且冷静地去控制“心猿意马”,以“完型”的审美预期去打造自己,而是断然地放弃所谓“纯熟的技术”和“完美的形式”,哪怕自己的画有粗糙与草率的风险。身在学院,大波理应是“标准”的执行者与代言人,但他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认为“学院”是一种精神,而非被竖立起来隔离专业者与素人的围墙。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他的学生和他一样左突右闯,画出了不少让人意外的好作品。
人的个性“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大波将有限的时间与精力献给了内心的发掘,在创作的轨迹中以自我为参照,诉诸个人化的绘画形式和个体化意义的追求。绘画之于他反而具有了别样的意义:一块安全的“飞地”,可以栖居心灵的净土。大波将内心感受与现实经验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我的世界”。对于一个执着而坚定的画者来说,“找到自己”无疑是最幸福的事情,与别人无关。
画展的名称叫“万象在旁”,大波笔下有人物、有鸡狗、各种物事……似乎漫不经心地选择绘画的对象,于他而言,并无专注某种题材的心理压力与固定表现手法的限制,表面的世间万象,不过是他为了指向自己内心而设下的一串伏笔,碎裂的镜子般折射出万千个“自我”。一缕回忆、气味,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或者干脆一阵莫名其妙的心灵震颤,都可以是促成他绘画的起因。
我总觉得,人的一生就像拼图,又像一个不断找回记忆的失忆者。远远的前面“仿佛若有光”,所谓宿命,不过就是把眼下这块拼图拼向了“有光”的那个方向。大波就是在“顾左右而言他”中寻找记忆,他说不出什么,可又无时无刻不在印证着自己的艺术宿命。
文/赵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