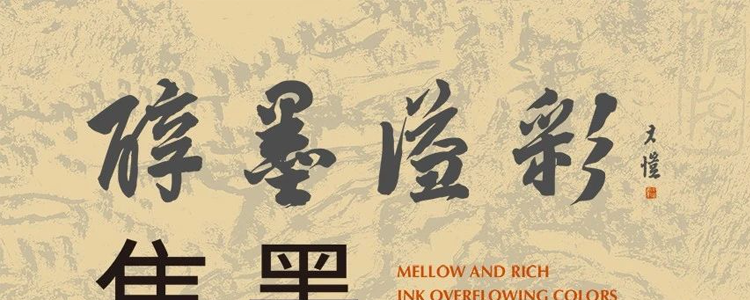
前 言
自原始岩画、彩陶至战汉漆画、帛画,黑色以其色相的沉著稳定而被画工首选为勾勒物象轮廓与图案符徽的颜色。在以白色或浅灰、浅褐为底色的材质之上,唯有黑色可以“一画开天”,于混沌太虚中判分天地阴阳,构建事物清晰的框架,让人的认知具有格式塔的知觉完型。直至西域“凹凸法”传入中土,华夏绘画始知在衣纹线条两侧以淡黑画出衣褶的暗影,并自此而悟“墨分五色”,以黑度之深浅浓淡描绘视觉经验中的阴阳向背远近。大概从五代北宋开始,画家们就非常自觉地弱化丹青而主要以墨色的浓淡变化来表现大自然的景象,郭熙的《林泉高致》提到当时的画师口诀“用焦墨,用宿墨,用埃墨,不一而足,不一而得。”可见对墨法的研究和运用已达到深致而细腻的程度,焦墨,作为各种墨法之一,堂皇登场,成为画师炫技的手段。但纵观画史,似乎也找不到有谁真正纯以焦墨完成一幅作品,直到明末清初的垢道人程邃,纯焦墨山水画在他笔下才得以小品的样式出现。1996年我陪同张仃先生专程赴歙县博物馆拜读程邃焦墨山水册页,发现多为淡墨渴笔之作,与同时期新安画派诸子崇尚简淡的渴笔画风一致,其源头可上溯元代倪瓒。虽然如此,程邃纯用枯笔渴笔作画而摒弃水墨与颜色渲染的决绝画风,因其坚守明遗民操守的孤高品格而赢得士林广泛尊敬,其一味枯槁的焦墨语言亦赢得“干裂秋风,润含春泽”的美誉,可以说是独步一时。但程邃之后三百年,焦墨竟成绝响,及至其同乡黄宾虹在困居北平十年中予以发掘方为世人所知。黄宾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型画家,他游历所至必阅方志,且总是随身携带一册一砚,以焦墨勾勒山川风物。张仃先生1954年在荣宝斋购藏一册十七页的宾翁焦墨山水,是宾翁北上北平时沿途所见齐鲁燕赵景观的记录,画在巴掌大小的紙上,以桐木为封,装为一册,赠与其女弟子谈月色。正是这本黄宾虹在册尾跋语中明确表明向程邃致敬的焦墨山水册页,开启了那个特殊岁月中张仃的“灵犀”,像一位精神导师将时隔三百多年的三位重要的山水画家导引到焦墨这一极致的艺术语言。所以,从其出生与传承,焦墨就是孤勇的象征。
当然,在资讯发达文化多元的今天,在张仃、崔振宽几位先行者艰辛开拓之后,焦墨山水也获得了一大批爱好者和追寻者,张仃先生当年自嘲的“寂寞之道”,如今也不乏知音。更年轻的画家走上这条“道”,各有灵苗各自探,出现可喜的局面,竟致有国博立项的焦墨山水画科研项目及结项成果汇报,由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导,与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院、荣宝斋画院、李可染画院共同主办“醇墨溢彩---焦墨山水画展”,真是令人高兴。圣人云:“德不孤必有邻”。焦墨山水,是有高级审美品位和深邃艺术品格的艺术,是有高深语言难度和孤㢠超逸境界的艺术,是有源远流长传统和曲高和寡存在的艺术。诸位焦墨画家同道,一定要学习苏东坡贬谪惠州时的自信,哪怕是到天涯海角,他也要给自己的庐屋匾书“德不孤斋”和“有邻馆”。焦墨不可能成为横无际涯的大河,但一定是一条淙淙流淌的山溪,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和沿岸风光。
王鲁湘
2023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