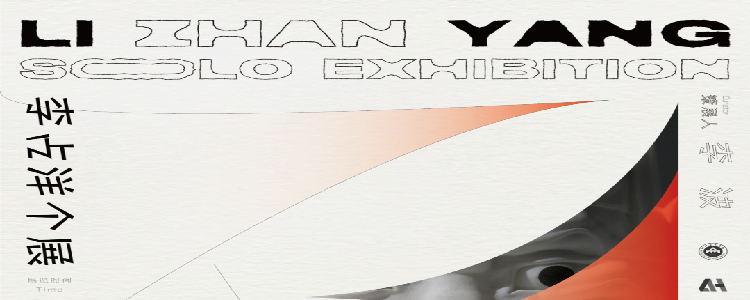
雕塑家的真实——观李占洋近期作品
尹丹
过往,李占洋老师喜欢在网上分享自己所听所闻的一些小故事,给大家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其文字直截了当而令人忍俊不禁,其叙事太过直白甚至得罪了不少人。这些都太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个嬉笑怒骂的北方“老粗”,其实他才是一个真正的“粗中带细”的人。本次展览筹备过程中,他对于细节的在意,对于创作的专注,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自己的雕塑,确实是用心。或许他就是这样的矛盾体,这些都是他的真实。
曾经,李占洋的雕塑以其戏谑、挑衅意味而为人熟知:有《丽都》一类,以活色生香的芸芸众生像,体现出中国 90 年代以来边缘群体的活力与躁动;有《武松杀嫂》一类,因其情色意味和荷尔蒙气息而在公众层面引起很大争议。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一位特别真实的艺术家,这真实不仅在其言谈,在其行为,在其“文如其人”的作品,更在其对于伪善的回避和对于真实人性的直击。占洋老师的作品诙谐、幽默,直接而刺激,有烟火气,这也很容易让人将他与其生活过的东北、重庆的文化特性相联系。我绝非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但你不得不承认,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环境的真实也是真实。
批评家高名潞曾将他的作品称之为“草根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与命名之间永远充满着悖论,艺术家一方面希望有精准的话语对其创作进行定义,又不希望被命名所束缚。我想他或曾欣然接受,又曾被这样的命名所役,甚至想挣脱它。真正的艺术家是善变的,因为他具备敏锐的感受力来把握自己的“当下”。今天的李占洋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想换一个面貌,他想换一种思路,他想换一些风格。这个展览是很好的回答,是近几年其创作新面貌的集中呈现。
它们同样诙谐,却似乎回避了前些年的挑衅意味。作为一个雕塑家,李占洋在本次展览中所拿出来的作品,体现出一位雕塑家的“固守”,即对于雕塑造型语言的一贯关注。实际上,去年在讨论展览主题时,他曾设想对其早年的雕塑造型语言及相关思考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如今,他成了一个炼金师,民间的图像,学院的造型,传统的装饰纹样被他扔进熔炉。从题材上讲,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小”题材,却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结合部转向了乡土社会。诸如咕咕吃米的群鸡,温情脉脉的抚马人,憨态可掬的农家小狗,被困藩篱的硕鼠,秀色可餐的出笼包子,荷叶包裹的蟾蜍……相比前些将泥塑作为其主要创作手段,近两年对于石雕和木雕的倾心颇为明显。至少有几种造型语言在近期的雕塑中得以明显的呈现:一是将稚拙、诙谐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较之前作品中“矮圆肥”的芸芸众生和全景式视角,这批作品拓展了反常化的方式来制造幽默。例如《抚马》这件浮雕作品,有意夸大了马与人的头部比例,拼命将硕大的马身压缩到“画幅”之内,由此产生出一种浓郁的稚拙感。又如他雕凿的狗与老鼠,皆刻意强化了其浑圆形象,蠢萌模样尽显无遗。另外一件《吃米(小)》作品中,二十几只鸡非常守规矩地围着居中的米堆,形成一个圆圈,撅着屁股旁若无人地大口进食。这种太过规则整一的造型反倒呈现出极强的形式感和莫名的荒诞感。二是对于木、石、陶瓷等材质本身特性的尝试。例如他刻意在这批作品中保持了石雕表面的光滑和细腻感,却有意地在木雕中强化其粗糙感和凹凸感。在《牡丹》和《抚马》两件作品中,类似于木版画的推刀手法在物象的表皮被强化,密密麻麻的短线成为这两件作品最显眼的肌理效果。又如《硕鼠硕鼠》这件木雕作品中,束缚其逃离的“围墙”保留了木料原有的凹凸和镂洞,稍微加工,趣味无穷。展厅门口的《吃米(大)》中,每只鸡都被赋予不同色彩的羽毛,似乎是出于他景德镇之行后对于不同釉色效果的兴趣。三是不少作品中浓郁的中国传统装饰趣味。作为一位常常被冠以“当代艺术家”的雕塑家而言,他近期的这一尝试让很多人始料未及。在引人关注的一件汉白玉自我肖像《闹海》中,李占洋的头像似乎正从水面上浮出,偷偷摸摸地张望着。水波的表达,完全是对中国传统水纹图像加以转译的结果。《小狗》这件作品中,他还煞费苦心地为其制作了一个颇为尊贵的底座,在表面雕凿出繁复的牡丹纹饰,富贵气十足,与憨态可掬的“狗模狗样”形成了极强的反差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