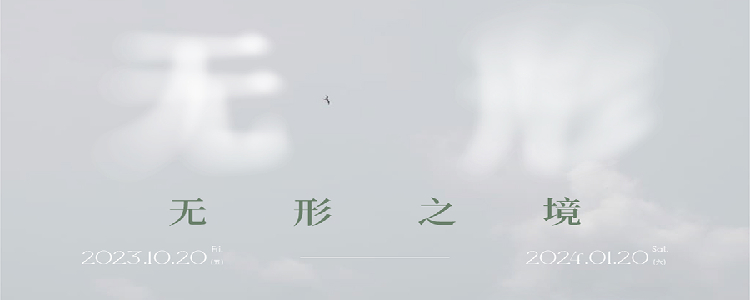
“我们将桥梁拆掉,甚至将土地毁坏,登船离开陆地!啊,小船呀!要小心!此刻你身处大海之中,虽然它并不老是白浪滔滔,有时也会荡漾着金黄色的波光,静谧地有如柔和的梦幻一般;但是当潮水汹涌而至时,你便会感受到大海的浩瀚无涯;同时,没有比“无限”更为可怕的了。噢,那自觉十分自由的可怜小鸟,现在开始要奋力挣脱这牢笼了!”
——尼采
《快乐的科学》§124 无限的范畴
在普遍认知中,“社会”与“自然”常被描述为对立的力量,其中前者将暴力施加于后者,而后者则需要人类的保护。
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两者则为相辅相成关系,体现在儒家的礼,道家的自然,也体现在宋明理学重新提出的道德宇宙论,其所宣扬的“道器合一”贯穿着古代社会进程中,直至近现代与国际接轨后产生了让步与脱轨,“自然”转变成为被剥削客体。单一作用所导致的不平衡危机在上个世纪末凸显出来,当代人文学科中提出人类与非人类的平等理念逐渐成为主流,然回归古代理念在现代的语境下明显显得不合时宜,意味着传统的认知需基于对当前文化和科技的理解以及消化,不仅是单一认知论的范式转移,同时需要在更高层次之上对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审视并寻找新的实践方法。
作为社会文化的生产物,艺术不仅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载体,更结合着个人体验与当下社会环境中的思想。本次展览《Invisible Land 无形之境》呈现在当代艺术板块中对于上述关系的观察:我们不可否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与其产生效益的必然性,同时相对应的自然也在其中进行自我消化与适应。而在一切思考的客观前提是,自然不可被征服——它无形而庞大,掌握着一切事物存在的规律并在其内部发生的调整都不断被融合吸收,形成新的规律并产生的结果是不可逆的。
此次展览在艺术的范畴内对于“无形之境”从内至外进行体现的同时,更是着眼于“海洋”这单一生态体:凯林布里克、冯至炫分别以互动装置与立体造型来呈现对“社会”与“海洋”关系的辩证性思考;范西的影像与装置也在“海岛”的语境下进行个人经验的传达;同时,范尼吉奎尔与石至莹通过装置和绘画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郭海强、赵仁辉则从更为客观的视角通过绘画与影像对于自然观察的显形。
随着“人类纪”(人类纪意味着人类活动已经是地球的主导力量)的来临,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单一的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决定的时刻”——我们该如何决定自身族群的走向?我们希望一个怎样的未来?
文 / 谭佳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