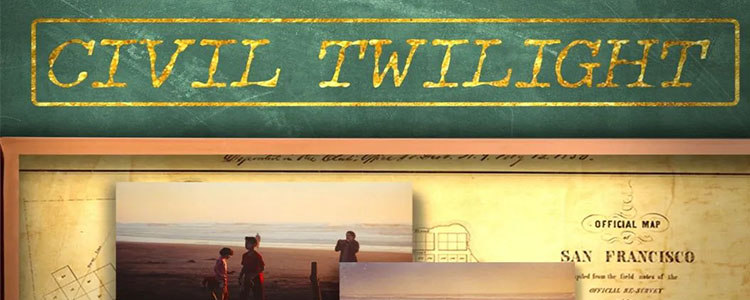
摄影媒介的本质便在于人或物的脆弱性、可变性、必死性,在于冻结时间流里的这一刻并见证其流逝。摄影图像代替了被拍摄者在场的替代,恰恰证明了其本身的不在场。
牟翰林的图像是对于受害者弥留时刻的再现,与死亡的主题直接相关,与摄影本身展现“不在场”和瞬间性的性质不谋而合。人物剪影的使用暗示不完整性。系列分为三种人群——身份图像变成了一种索引。
作品的手法模糊了虚构和现实的界限——根据真实案件,创造虚拟的“真实”摄影图像。
可信度极高的画面(描述)、摄影媒介的“记录性”vs虚构场景根据真实事件虚构场景的手法使人联想到电影。
汉斯·贝尔廷在《图像人类学》中提到,辛迪·舍曼的摄影系列《Untitled Film Stills》通过一系列刻板化的女性荧幕形象让观众混淆其作品的媒介,误以为摄影作品是五六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静帧。作为一个虚构叙事,《Civil twilight》的可信度是极高的,除了对于人物在自然状态下的抓拍,还有环境空镜和对于他们“遗物”的写照——营造氛围(描述)同时,这些图像由不同的摄影媒介拍摄——数码相机、拍立得、胶片,信息收集渠道的多样性,仿佛各式各样的新闻照片让人误以为这组摄影作品是新闻照片,或者一部记录性短片的静帧。摄影系列原本呈现于报纸印刷的摄影集,报纸这一媒介体现出短暂的时效性,同样也是对于新闻照片的戏仿。
所有的这些特点使得创造性摄影与新闻摄影、这些图像和真实性产生暧昧的关系。在与真实性的舞蹈中,图像变得更为破碎、转瞬即逝。但(对于最后一张图的探讨结尾)将消逝的光点;而当我们找寻、渴求,它又变成具象的记忆:幼年参加选美比赛时穿的裙子,父亲车行柴油的气味,还有自家餐馆日复一日亮起的霓虹招牌。于是归属感变成了一种敏锐的感知,它联结起内心和世界,召唤着每一个在归乡途中的人。
在本次展览中,唐子儒以外来者的角度向观众们展现一纸异乡客的内心图卷,一份实验性的在地调查,一次浪漫而脆弱的切身冒险。
牟翰林的图像是对于受害者弥留时刻的再现,与死亡的主题直接相关,与摄影本身展现“不在场”和瞬间性的性质不谋而合。人物剪影的使用暗示不完整性。系列分为三种人群——身份图像变成了一种索引。
作品的手法模糊了虚构和现实的界限——根据真实案件,创造虚拟的“真实”摄影图像。
可信度极高的画面(描述)、摄影媒介的“记录性”vs虚构场景根据真实事件虚构场景的手法使人联想到电影。
汉斯·贝尔廷在《图像人类学》中提到,辛迪·舍曼的摄影系列《Untitled Film Stills》通过一系列刻板化的女性荧幕形象让观众混淆其作品的媒介,误以为摄影作品是五六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静帧。作为一个虚构叙事,《Civil twilight》的可信度是极高的,除了对于人物在自然状态下的抓拍,还有环境空镜和对于他们“遗物”的写照——营造氛围(描述)同时,这些图像由不同的摄影媒介拍摄——数码相机、拍立得、胶片,信息收集渠道的多样性,仿佛各式各样的新闻照片让人误以为这组摄影作品是新闻照片,或者一部记录性短片的静帧。摄影系列原本呈现于报纸印刷的摄影集,报纸这一媒介体现出短暂的时效性,同样也是对于新闻照片的戏仿。
所有的这些特点使得创造性摄影与新闻摄影、这些图像和真实性产生暧昧的关系。在与真实性的舞蹈中,图像变得更为破碎、转瞬即逝。但(对于最后一张图的探讨结尾)将消逝的光点;而当我们找寻、渴求,它又变成具象的记忆:幼年参加选美比赛时穿的裙子,父亲车行柴油的气味,还有自家餐馆日复一日亮起的霓虹招牌。于是归属感变成了一种敏锐的感知,它联结起内心和世界,召唤着每一个在归乡途中的人。
在本次展览中,唐子儒以外来者的角度向观众们展现一纸异乡客的内心图卷,一份实验性的在地调查,一次浪漫而脆弱的切身冒险。
上一篇: 严瑜哲个展:跃出幻境
下一篇: 张青个展:XSC1-40

最新展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