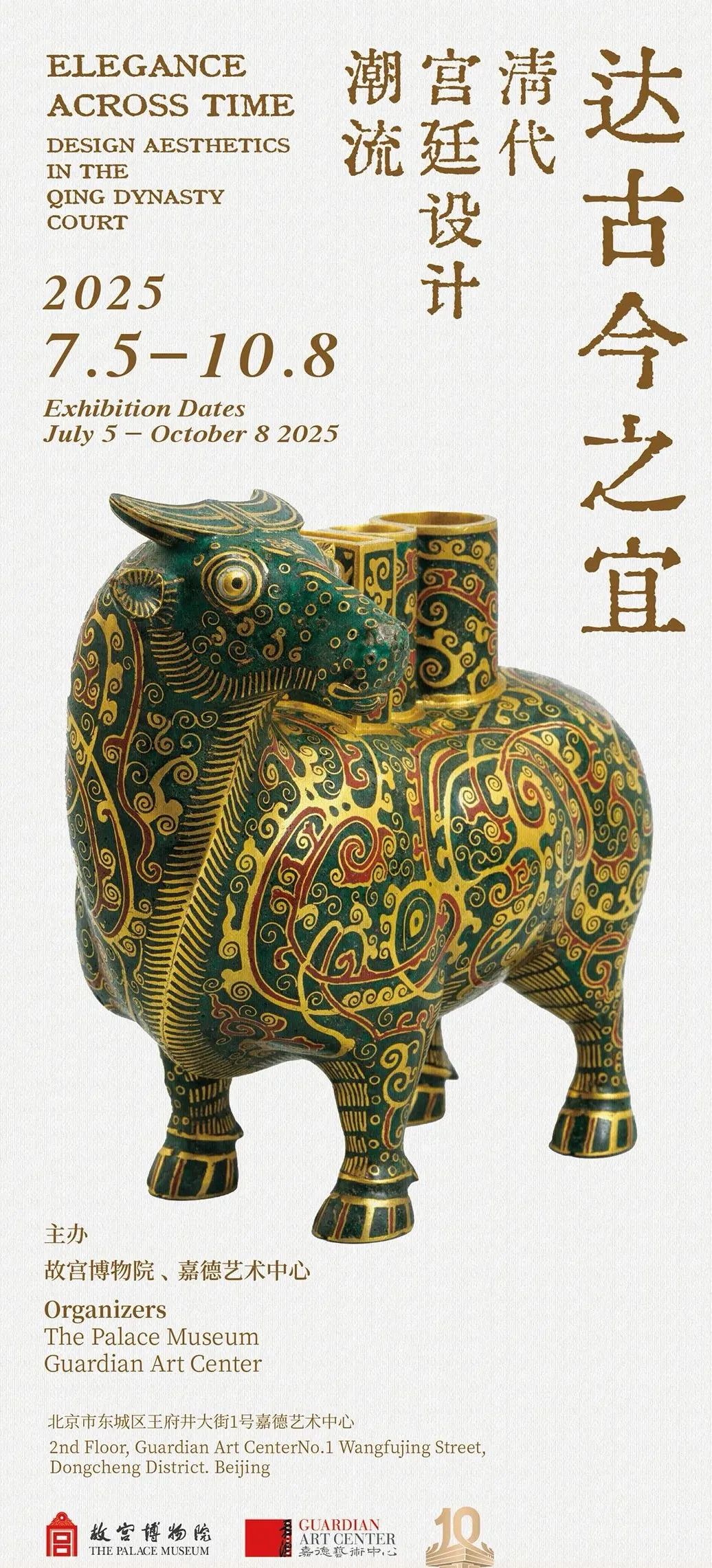2011年(上一个兔年)网络上的"虐兔门""周老虎"事件都进入了我的画中,后来兔子和老虎作为一个形象符号经常在我的画面中出现。在《兔子兔子》系列中我画了现实社会里的虐兔门、炫富门、兔子舞、接吻大赛、米兔(MeTo)事件等,又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月兔、兔儿爷,西方美术史中丟勒的兔子、波依斯与兔子对话等,各种现实与历史的图像以兔子为线索纵横交织在我近百幅的系列作品中,2013年参加过“海峡两岸当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和台湾美术馆展出过。后来我又做了兔女郎、基因兔等雕塑,在我近几年的多次个展中都有出现。我用兔子符号揭示的是当代消费文化中娱乐至死的社会问题,是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与反思流行文化和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
《周老虎》画的是2008年陕西农民周某龙的华南虎事件。周某龙用图片合成假照片说他发现了野生华南虎,并冒领了政府两万元奖金,成为一时的社会热点新闻。后来作假的老虎图片被扒出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他还能够信誓旦旦地指鹿为马,被判诈骗罪两年半出狱后还理直气壮决不认错。这件事让我感到荒谬背后还有点黑色幽默,并思考关于谎言与真实、道德与诚信、诡辩与逻辑的关系,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这些年层出不穷的荒唐事件似乎并不偶然,“周老虎”在我看来已成为一个哲学或社会学的问题。
草食动物兔子和肉食动物老虎在丛林社会中是食物链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虎兔是否可以和平共处?2011年我还画了一幅《虎兔寓言》,作品里的兔子成为驯兽师,和一只像马戏团里的白老虎对峙着。我善良地认为在文明社会里面也许兔子跟老虎可以用智慧和规则进行一些合作与对话,但充满火光的背景中一切又显得很不确定与危机四伏。《虎兔寓言》在十二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还有些预见性,在幽默调侃后面似乎还有些哲学意味的荒诞感。
疫情三年间我画了《庚子惊蛰》《壬寅虎啸》和《墙》系列作品。这些都是我在画布上的思考痕迹,说不清究竟是物质世界的幻像呈现还是精神世界的心灵映照?疫情之前我的《朋友圈》和《墙》系列都是对网络时代图像的绘画性转换,《朋友圈》系列以肖像形式表现当代人的精神相貌,但疫情后我已无心再画现实中的人,也许人在困境中容易成为哲学家,我成不了哲学家,但画了一些哲学家肖像。疫情三年人人都有围困墙中的体验,《墙》系列以碎片化的图像和事件构成了一组时代的记忆之墙。墙在我看来己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墙的建立与拆毁是一个世界话题又是一个历史话题,对墙的凝视就是对自身处境的关注,对墙的超越也是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溯。我用墙的寓意来反思国际关系之墙,信仰冲突之墙,文化观念之墙,以及人与人之间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心墙。
回想起来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伴随着青春和理想主义的激情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过叔本华、尼采、萨特、西蒙波娃、弗洛伊德等哲学心理学著作,这个烙印可能伴随一生。罗素说,在神学与科学之间就是哲学,而艺术又游离于这三者之间。在我的认知里,哲学是尚智求真的追问与反思,是超越俗世的思想与精神,是蒙昧黑夜里的一束光。我的艺术并不图解哲学,但类似哲学的思辨意识又经常是我创作的内在逻辑和思维导图,我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与创作方法论。
很荣幸地受到荣剑先生的邀请,把自己画的哲学家肖像和在这十二年之间画的虎兔系列做一次专题的梳理与展示,并有机会和真正的哲学家们进行交流,聆听各位专家学者们的高见,为自己以后的艺术创作打开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