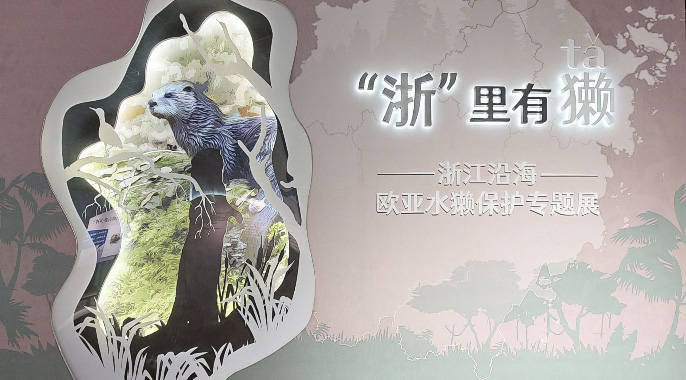由彼及此
文/林一梦
中文字的构造,决定了中国人的模件化思维,即由相对有限的标准化零部件组合构建出变化无穷的单元。很多中外学者都赞成,模件化思维不仅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各个领域,远至青铜器的铸造,丝绸和瓷器的生产,中国建筑的斗拱,近有活字印刷,民间版画。在我们熟知的传统书画领域,更是出现了诸如《芥子园画传》这样将中国绘画中的所有元素一一拆解和组装的教科书。
我们时常会问:在模件化几近极致的中国绘画领域,年轻的艺术家们还有创新的空间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首先,我们的模件化体系,自最初就为个人创新保留了空间。在青铜器、砖雕和印刷等需要用到模具的艺术类型中,生产者可以依据器物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对模具进行选择和调整。如此,最终成型的器物上的纹饰,在总体符合文化和审美规范的同时,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细节。在手绘瓷器和版画等更依赖手工技巧的类型中,更容易观察到生产者在排布符合规范的设计元素的同时,为了实现画面的美观而加入的个人巧思。
其次,尽管艺术品(我们且把原本作为礼器和日用品的物件按现代的惯例统称为艺术品)的模件化和标准化一直是中国特色,但是我们的艺术审美千百年来始终以极具个人风格的创新为最高抱负。书法上,“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的米芾,“神鬼惊,龙蛇走”的怀素,绘画上,洒脱不拘泥于形式的牧溪,打破了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的题材界限的徐渭,都被尊崇备至。
我们可以想象,要在如此底蕴深厚的领域中实现被世人认可的创新,是有多么难。古人常说,须得“淹雅博物”,即宽宏、儒雅、渊博,在通晓文化和艺术史的前提下,才能有机会形成自身艺术创作的独特个性。
这次参与展览的三位年轻艺术家,无不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在艺术院校接受长达十几年艺术教育,熟知东西方历代的艺术积淀,并在经年累月的绘画实践中逐步探索出自己的艺术风格。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静物为描绘对象,但又发展出各自迥异的描绘视角,令观众得以一窥当下年轻人面对这个世界时的情绪和态度。
符茗希偏好描绘带有年代感的南方城市建筑,然而与其他很多带有复古未来主义意味的城市题材作品不同的是,艺术家在建筑物与观众之间,添加了一层似有若无的玻璃,玻璃上的灯影使得作品形成了前中后三重景观,从而让观众产生了从室内向外窥视的观感。年轻的艺术家笔下的图景,正是她当下的一个迷惑状态的表达,玻璃内外的世界,哪一个是真实的?艺术家试图用一个平等的视角从一侧望向另一侧,然而最终的感受却是自己被困在了两个世界之间,难以超越那个父辈们造就的世界。
同为女性艺术家,许嘉维也喜爱描绘带有复古感的物件,比如古董水晶杯,因其在转手的过程中被不同的人拥有而带有一种故事性。许嘉维在画面中将质感坚硬的水晶物件排列得整整齐齐,中国水墨特有的单色绘画进一步强化了画面的冷峻和理性,但正因为此,观众在秩序带来的舒适感中隐隐产生想要打破这套秩序的欲望。
相对于两位女艺术家,王家豪的静物带有比较明显的生活气息,因此也就更带有叙事性。汽车尾箱中的无人机,意味着一次周末的出游?面对面的两支牙刷,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场景感。当一件于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物件,被单独呈现,甚至占据整个画面的时候,这些物件给予我们一种不现实感,也就是陌生感。高纯度的色彩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现实感,让我们开始细细打量这些原本再熟悉不过的物件。
三位艺术家的作品画面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识别出某些传统绘画模件化的“规训”,体现出经得住挑剔眼光的绘画功底,这是长时间浸润在传统绘画训练体系中带上的深刻烙印。与此同时,艺术家们的作品又都呈现出具有辨识度的个人特色,他们在持续的创作中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绘画语言。
更重要的是,三位艺术家用理性克制的方式,表达了90后一代人感性的一面,在舒适生活中成长起来的90后,如何超越父辈的成就,是始终困惑着同时诱惑着这代人的一个课题。正是作品中传递出来的有代表性的情绪,赋予了这些作品以确凿无疑的当代性。
米芾在《画史》总序就开宗明义,认为书画作品可以比建功立业更加历久不衰:“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薛稷,初唐书画家)之笔静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们,在传承了彼时绘画精髓的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不间断地探索,表达自己此时身处当下的社会态度,记录下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人们的忧与思,乐与悲,令世人得以由彼及此感知那些自己未有机会触碰的人生,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
上一篇: 自我:新纪实摄影
下一篇: 是日天气:壬寅年艺术计划

最新展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