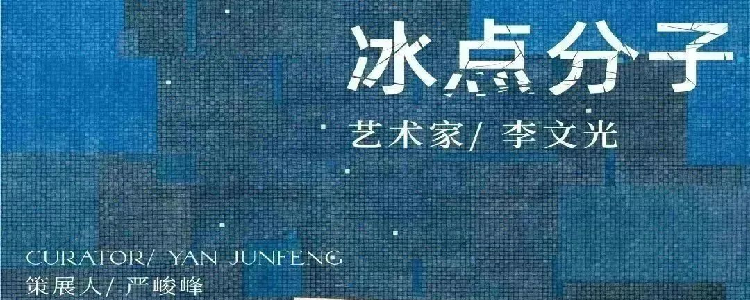
高温、干旱、洪涝、寒潮......这些极端气候已经持续性影响人类的日常生活,环境问题似乎又一次更加牢固地回归到公众的意识中,与资本、国家和权利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引发地缘政治上的争端和冲突。回归本质,体现的就是对这颗星球不稳定未来的忧忡。自然而然地,艺术家们会把自身的艺术实践当作反思的容器,尤其在特殊时期,生存受到威胁时所采取的行动也将变成希望的灯塔。
在李文光近期的创作中,对自然危机以及个体境遇的思考一点点显形,他将景观、身体和时间进行混合来分析现实,用冰山的主题证实气候变化的真实存在,以及污染的水体、砍伐的森林、枯萎的盆栽......这些主题演变成后期作品韧性发力的蛹。
本次展览的名称,灵感源自于物理学的概念:冰点,水由液态冻结成固态的临界值,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无定形式的向质量、稳定的、由形式定义的规训,也是将人类生存空间困囿在最小活动范围的隐喻;分子,在物质发生变动瞬间之前无限小的阈值,是独立存在的最小单元,也是相互依存成整体的其中之一。冰点分子,正是这种辩证,如果分子间作用力更加团结,它会影响其物质层级间的性质。
在此,他提供了俯瞰的视角——对既定的秩序进行长久的审视,扁化为一道道分岔的小径,将作品引向为“能量的全景图①”,在构成之初便把画布分割成为等比大小的网格,就像梳子一样筛选过组建排列,并力图让线性的时间重叠共存。这种仪式感使观众立刻被推到作品的表面和笔线的细节,同时又被拉回一个多维度纵横交错的空间,使作品的地下世界浮出水面。
迄今为止,许多人都视架上绘画为艺术表现的次要媒介。然而,新兴一代的艺术家正在努力突破表现的极限,并尝试大量不同的技术来创造新颖和激进的绘画形式;有的艺术家则坚守传统的工具和技术,试图重塑当代绘画的意义和精神的界限。李文光使用中性水彩笔作为绘画的媒材,对绘画的基本语言——线条和形状,进行解散、重组、堆集等处理方式来记录现实的碎片化特质,形成作品中视觉词汇的基座。他坐在桌子前,编织和计算出一系列高度严谨、精密、节奏感的抽象,给视线以躺在平面上的错觉。每件作品都源自艺术家遵循的一套流程主导的规则,即相同且无休止重复的书写,让线条本身在隐喻的深邃海洋中游荡、内敛、积蓄,在高度严格的监管框架内野蛮的成长和再生,进入乔治·库布勒②所说的“人类创造力是不断重复的尝试”的规则中。
同时,他利用笔管中固有的红、蓝、绿色,通过颜色叠加的深浮和浅没来实现画布的地下世界。这些用以滚动的笔芯前端装置而来的痕迹,产生出自我的意识,自行载入历史的铺陈,连接到原始质料的过去、艺术家的过去以及集体的过去:曾经工业制造的进程、碳化钨球珠的力量,一种怀旧的叙事。这样的流动同样暗示出重新获得与身体存在感知的联系方法——劳作,并在当下手指滑动数字屏幕上的信息瀑布流而产生质朴的呼应。其次,他用矿物色熟褐在画面的局部染出时间残留的催化物,用树脂密封表层后形成石英般坚硬的质感,“静态的普遍平衡③”。就像洼地浓雾笼罩在某种阴沉的优雅、隐秘又清晰、谨慎而华丽的深渊。
李文光的元叙事云,是从早期的“护身符”精神图示建立起来,以“荷鲁斯之眼”,古代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他的眼睛意谓着无所不见,洞晓万物,借此他在寻求稳固、神秘、近乎完美的物质,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以太④”,抽象里最纯粹形式的体现。继而在几何绘画往具象化的尝试——滴水兽开始,存在画面中心的凝视犹如“作品在看我”。
这种主客错位的观看体验直到“科幻笔记”系列转变为冷静的研究,以及开始寻求逻辑认知上一种互文性的表达,并将公众的理解置于美学和科学共同作用的标本之上。他在两个月的驻地期间,起初制作一张五米以上的塑料膜水槽,随后将调制的颜料与水多次混合,最终将油渍产生的涂层效果拓印在纸本上,既像是“疾病类病菌在身体中扩散的过程,又形似工业污水中黏浊的金属颗粒⑤。”纸本晾干,托裱在树脂胶制作的黑板上,并附上连串的、虚构的数学公式来实现陌生化效果,这些附注给这些肌理的说明也是通向理性真实的假象,未在认知范畴建立起的浮标。
年初静默在家的时候,李文光对阳台上即将枯萎被丢弃的植物发起视觉的冥想,个体的境遇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敛缩为被铁丝缠绕、剪制、歪曲出的怪相畸形的“盆栽”。他的关注视角开始伸向日常,伸向内心和情感,逐渐向大众靠拢,就像一个个毛线团滚向公众的面前。观看也被编织成网格的幽灵,被它们扔进了“有意义”的隔间。
在李文光近期的创作中,对自然危机以及个体境遇的思考一点点显形,他将景观、身体和时间进行混合来分析现实,用冰山的主题证实气候变化的真实存在,以及污染的水体、砍伐的森林、枯萎的盆栽......这些主题演变成后期作品韧性发力的蛹。
本次展览的名称,灵感源自于物理学的概念:冰点,水由液态冻结成固态的临界值,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无定形式的向质量、稳定的、由形式定义的规训,也是将人类生存空间困囿在最小活动范围的隐喻;分子,在物质发生变动瞬间之前无限小的阈值,是独立存在的最小单元,也是相互依存成整体的其中之一。冰点分子,正是这种辩证,如果分子间作用力更加团结,它会影响其物质层级间的性质。
在此,他提供了俯瞰的视角——对既定的秩序进行长久的审视,扁化为一道道分岔的小径,将作品引向为“能量的全景图①”,在构成之初便把画布分割成为等比大小的网格,就像梳子一样筛选过组建排列,并力图让线性的时间重叠共存。这种仪式感使观众立刻被推到作品的表面和笔线的细节,同时又被拉回一个多维度纵横交错的空间,使作品的地下世界浮出水面。
迄今为止,许多人都视架上绘画为艺术表现的次要媒介。然而,新兴一代的艺术家正在努力突破表现的极限,并尝试大量不同的技术来创造新颖和激进的绘画形式;有的艺术家则坚守传统的工具和技术,试图重塑当代绘画的意义和精神的界限。李文光使用中性水彩笔作为绘画的媒材,对绘画的基本语言——线条和形状,进行解散、重组、堆集等处理方式来记录现实的碎片化特质,形成作品中视觉词汇的基座。他坐在桌子前,编织和计算出一系列高度严谨、精密、节奏感的抽象,给视线以躺在平面上的错觉。每件作品都源自艺术家遵循的一套流程主导的规则,即相同且无休止重复的书写,让线条本身在隐喻的深邃海洋中游荡、内敛、积蓄,在高度严格的监管框架内野蛮的成长和再生,进入乔治·库布勒②所说的“人类创造力是不断重复的尝试”的规则中。
同时,他利用笔管中固有的红、蓝、绿色,通过颜色叠加的深浮和浅没来实现画布的地下世界。这些用以滚动的笔芯前端装置而来的痕迹,产生出自我的意识,自行载入历史的铺陈,连接到原始质料的过去、艺术家的过去以及集体的过去:曾经工业制造的进程、碳化钨球珠的力量,一种怀旧的叙事。这样的流动同样暗示出重新获得与身体存在感知的联系方法——劳作,并在当下手指滑动数字屏幕上的信息瀑布流而产生质朴的呼应。其次,他用矿物色熟褐在画面的局部染出时间残留的催化物,用树脂密封表层后形成石英般坚硬的质感,“静态的普遍平衡③”。就像洼地浓雾笼罩在某种阴沉的优雅、隐秘又清晰、谨慎而华丽的深渊。
李文光的元叙事云,是从早期的“护身符”精神图示建立起来,以“荷鲁斯之眼”,古代埃及神话中法老的守护神,他的眼睛意谓着无所不见,洞晓万物,借此他在寻求稳固、神秘、近乎完美的物质,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以太④”,抽象里最纯粹形式的体现。继而在几何绘画往具象化的尝试——滴水兽开始,存在画面中心的凝视犹如“作品在看我”。
这种主客错位的观看体验直到“科幻笔记”系列转变为冷静的研究,以及开始寻求逻辑认知上一种互文性的表达,并将公众的理解置于美学和科学共同作用的标本之上。他在两个月的驻地期间,起初制作一张五米以上的塑料膜水槽,随后将调制的颜料与水多次混合,最终将油渍产生的涂层效果拓印在纸本上,既像是“疾病类病菌在身体中扩散的过程,又形似工业污水中黏浊的金属颗粒⑤。”纸本晾干,托裱在树脂胶制作的黑板上,并附上连串的、虚构的数学公式来实现陌生化效果,这些附注给这些肌理的说明也是通向理性真实的假象,未在认知范畴建立起的浮标。
年初静默在家的时候,李文光对阳台上即将枯萎被丢弃的植物发起视觉的冥想,个体的境遇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敛缩为被铁丝缠绕、剪制、歪曲出的怪相畸形的“盆栽”。他的关注视角开始伸向日常,伸向内心和情感,逐渐向大众靠拢,就像一个个毛线团滚向公众的面前。观看也被编织成网格的幽灵,被它们扔进了“有意义”的隔间。
(严峻峰)
上一篇: It's Okay 快乐就好!
下一篇: 胡庆雁个展:2023

最新展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