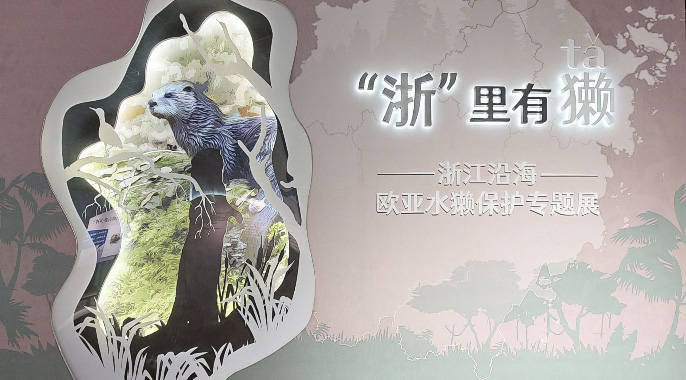白川艺术空间,如白水流过之地。水流不可胜数,此展为其滥觞。此间的序章,陆斌的回首一望,时间指向1997年。本次展览的主题,是陆斌的“97式花器”。
二十五年过去了,“逝者如斯夫”。水流无形,日升月恒,那于岁月中不老、于今日仍称现代艺术者,是陆斌先生的陶。这些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定型的陶艺作品,要到今天才能被认识。
回到1996年,我在艺术鉴赏课上看到了雍正粉彩蝠桃盘,如遇甘霖。指引我逃避现实功利的路径,从此多了一个陶瓷。同时,陆斌在深圳,一边做着那些主题宏大、表达深沉的当代陶艺作品,一边也把内心的温存留给了泥片和花,97式花器因此诞生。我们当下继续讨论它们,因为经过了时间的锤炼和拣选。
陆斌在南艺求学的时候,本无意去制作器皿,而是想从事雕塑——传统中国士人“君子不器”的观念、上世纪八零年代浓郁的文艺复兴式的氛围,以及他对历史和现实的个人思考,都驱使他去讨论更为宏大的话题。
这二十年来,陆斌创作了不少令人惊叹的当代陶艺作品,从早期的化石系列到近年的信仰之塔和残损之书(大悲咒系列),都是纯粹只为精神留存的陶瓷,是他个人对时代和自身思考的瓷化,它们往往是残缺或破碎的。
反观这一组97式花器则有着近乎完美的形式,甚至有他很独特的对“实用”的定义和设计。我如此去理解其中的张力:那些破碎的形式要么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反映,要么是他个人对现实的坚硬还击,拒绝被使用,拒绝被工具化。而花器中的“完美”,则是他忍耐着、坚持着去作从从容容的表达,这两者都是陆斌。
是的,二十年后,当陆斌从一堆堆的碎片中起身,重新看到自己当年的那一组“完美”的、有工业审美趣味的、漠漠含光的器皿,一定也起夫子之叹。他重新拿起泥拍,使用当年在南艺学到的最初的陶艺技能,像锻造铁器一样,拍出一条条泥片,围出一个个身筒,又去演绎它们,壮大它的家族,去重新塑造它们,让它们更加简练有力,愈加内敛丰富,这时候的陆斌已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他自己说是“退步”,而我看到的是他内心温柔的部分,前进了。
因为花器是器皿,器皿即是空间,在能容纳花的空间里,最大的是天地,至大无形,苞育万物。若不是效仿了那造天地之心,陆斌如何做出此等尽善尽美的花器。
尽善尽美得就像当年我看到的那只雍正粉彩蝠桃盘,良工美才,温润新鲜。蝙蝠在成熟的桃林中飞行,它们以娴熟的超声波领航术来避免撞破一枚成熟的水蜜桃——哪怕只是一枚。当桃子成熟,蝇蚋纷飞,蝙蝠就来收割它们,也把桃子留给吃桃子的。有一年的春夏之交,在一晚的蝙蝠飞行之后的上午,我在姑妈家的桃园就吃了十三只桃子。那只盘子让我意识到,古人把蝙蝠和成熟的蜜桃绘于盘中,有良好的寓意,多福多寿且美。
可是陆斌的陶器上,既没有桃子也没有蝙蝠,它们也不是白如玉的瓷,它们是生锈的铁器、丝绒面的革制品、花斑的岩石,从青铜黑铁时代穿越而来的盘或钲,其间闻得出冷月照在岩壁的气味,也有海洋的气息,是园丁或船厂的工人用了许久的工具,岁月和汗水早把它们摩拭得恰好,陆斌想在其中插上看不见的花,盛上我们吃不着的果子。好的花器和食器,真是不需要真去使用的。它们放置在空间里,单纯地存在着,就足够好了。
从1997年到现在,陆斌作品二十多年的作品呈现了“完美——破碎——完美”的超越之路,像极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三段论。是知天命的妥协和放下,还是青春的回潮和凝结,所得唯独在他的心里。至于旁观的我们,哪怕没有陶瓷的专门知识,也能感受到力量和美。很荣幸在白川艺术空间,举办此次陆斌先生陶艺作品展,初试啼声,已然煌煌。
二十五年过去了,“逝者如斯夫”。水流无形,日升月恒,那于岁月中不老、于今日仍称现代艺术者,是陆斌先生的陶。这些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定型的陶艺作品,要到今天才能被认识。
回到1996年,我在艺术鉴赏课上看到了雍正粉彩蝠桃盘,如遇甘霖。指引我逃避现实功利的路径,从此多了一个陶瓷。同时,陆斌在深圳,一边做着那些主题宏大、表达深沉的当代陶艺作品,一边也把内心的温存留给了泥片和花,97式花器因此诞生。我们当下继续讨论它们,因为经过了时间的锤炼和拣选。
陆斌在南艺求学的时候,本无意去制作器皿,而是想从事雕塑——传统中国士人“君子不器”的观念、上世纪八零年代浓郁的文艺复兴式的氛围,以及他对历史和现实的个人思考,都驱使他去讨论更为宏大的话题。
这二十年来,陆斌创作了不少令人惊叹的当代陶艺作品,从早期的化石系列到近年的信仰之塔和残损之书(大悲咒系列),都是纯粹只为精神留存的陶瓷,是他个人对时代和自身思考的瓷化,它们往往是残缺或破碎的。
反观这一组97式花器则有着近乎完美的形式,甚至有他很独特的对“实用”的定义和设计。我如此去理解其中的张力:那些破碎的形式要么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反映,要么是他个人对现实的坚硬还击,拒绝被使用,拒绝被工具化。而花器中的“完美”,则是他忍耐着、坚持着去作从从容容的表达,这两者都是陆斌。
是的,二十年后,当陆斌从一堆堆的碎片中起身,重新看到自己当年的那一组“完美”的、有工业审美趣味的、漠漠含光的器皿,一定也起夫子之叹。他重新拿起泥拍,使用当年在南艺学到的最初的陶艺技能,像锻造铁器一样,拍出一条条泥片,围出一个个身筒,又去演绎它们,壮大它的家族,去重新塑造它们,让它们更加简练有力,愈加内敛丰富,这时候的陆斌已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他自己说是“退步”,而我看到的是他内心温柔的部分,前进了。
因为花器是器皿,器皿即是空间,在能容纳花的空间里,最大的是天地,至大无形,苞育万物。若不是效仿了那造天地之心,陆斌如何做出此等尽善尽美的花器。
尽善尽美得就像当年我看到的那只雍正粉彩蝠桃盘,良工美才,温润新鲜。蝙蝠在成熟的桃林中飞行,它们以娴熟的超声波领航术来避免撞破一枚成熟的水蜜桃——哪怕只是一枚。当桃子成熟,蝇蚋纷飞,蝙蝠就来收割它们,也把桃子留给吃桃子的。有一年的春夏之交,在一晚的蝙蝠飞行之后的上午,我在姑妈家的桃园就吃了十三只桃子。那只盘子让我意识到,古人把蝙蝠和成熟的蜜桃绘于盘中,有良好的寓意,多福多寿且美。
可是陆斌的陶器上,既没有桃子也没有蝙蝠,它们也不是白如玉的瓷,它们是生锈的铁器、丝绒面的革制品、花斑的岩石,从青铜黑铁时代穿越而来的盘或钲,其间闻得出冷月照在岩壁的气味,也有海洋的气息,是园丁或船厂的工人用了许久的工具,岁月和汗水早把它们摩拭得恰好,陆斌想在其中插上看不见的花,盛上我们吃不着的果子。好的花器和食器,真是不需要真去使用的。它们放置在空间里,单纯地存在着,就足够好了。
从1997年到现在,陆斌作品二十多年的作品呈现了“完美——破碎——完美”的超越之路,像极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三段论。是知天命的妥协和放下,还是青春的回潮和凝结,所得唯独在他的心里。至于旁观的我们,哪怕没有陶瓷的专门知识,也能感受到力量和美。很荣幸在白川艺术空间,举办此次陆斌先生陶艺作品展,初试啼声,已然煌煌。
——顾力
2022年2月14日
上一篇: 无形阐释
下一篇: 萨波尔齐斯·博佐:巴拉顿湖

最新展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