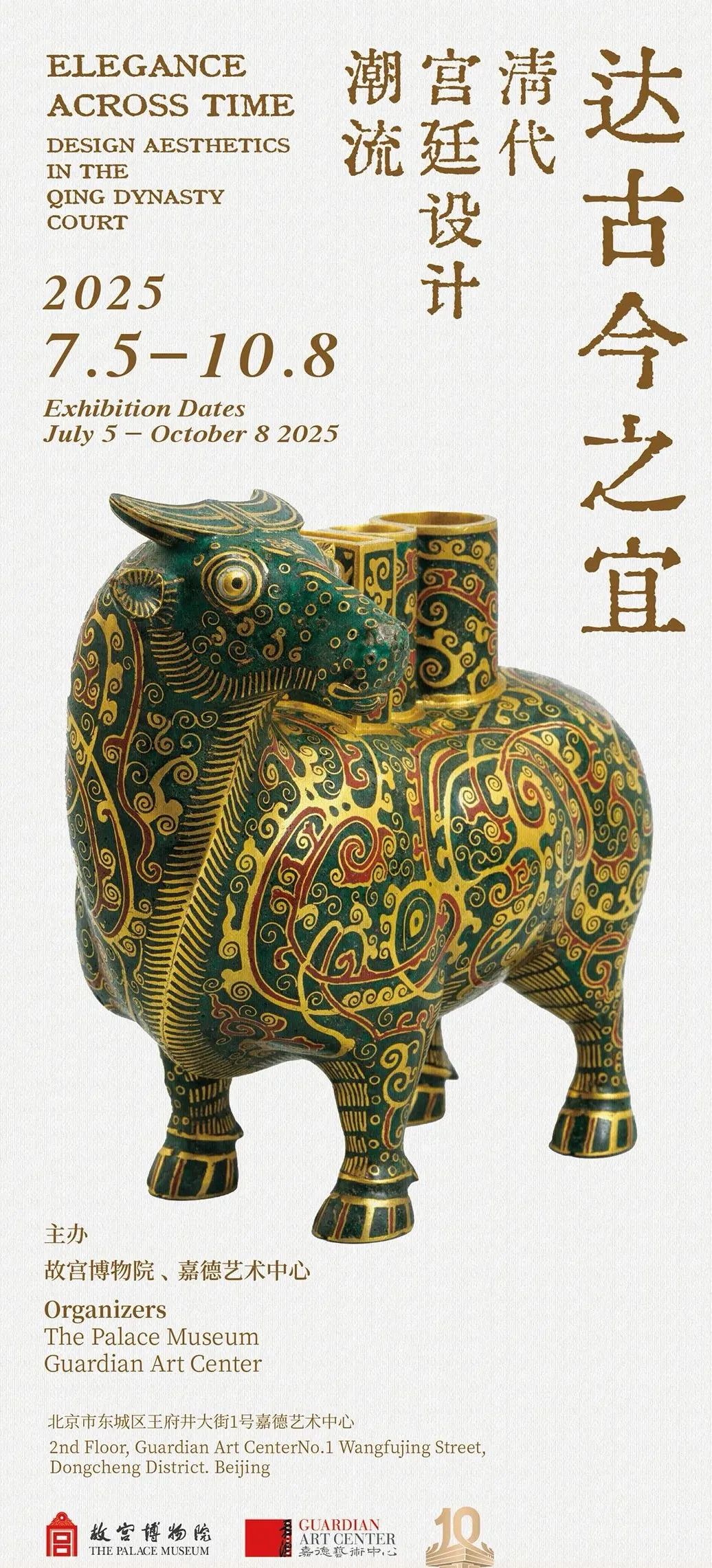总有一些时候,我们会问自己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好像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现在的我,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个我吗?”这是一种自我身份的缺失。在张可可Kchaoz的《The lost myth figures》(迷失的众神)中,正借助于画中人物,向观众抛出这一问题,犹如英国作家尼尔·盖曼(Neilman)笔下的《美国众神》。只不过在《美国众神》中,是旧世界(古典时期)的众神与代表着互联网、媒体等现代生活和科技的化身的新世界众神之间两大势力的对抗(为身份的逐渐逝去而反抗),而在张可可Kchaoz这里,则是直接的身份的彻底迷失,它似乎象征着现代人正处于的一种精神危机。
在张可可Kchaoz早期创作系列中,有一个不断重复的小男孩角色,艺术家将其取名为ogé,它将 ego(自我)反过来,成为一个“颠倒”的“自我”。这种对自我身份的思索,来源于艺术家在追寻童年时期接受的文化,是如何塑造成后来的自我意识,而这些文化符号又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成为产业链的集体式行为进入人们的生活。它至少从一个侧面开始去寻索关于自我身份(自我)的来源是什么?而这个“自我”在某种哲学前提下,被默认为是一种由语言(图式)所塑造成的某种“知识型”,或是“认知型”。这是一种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关于逻辑哲学的维特根斯坦对语言逻辑单元及程式化的“图式”概念,并揉杂了心理学及福柯关于“知识型”等多种同时代哲学元素的集合。在这里,它作为一种时代的哲学特征,试图去理解到底什么是“自我”,并最终可能演变成一种精神分析式的技术手段。于是,在这一顿分析之后,“自我”似乎消失了。
这正是由当代哲学所引发的问题所在。正如张可可Kchaoz的《Figure in the bedroom》中所示:“在昨天,你说明天”,而“今天”却恰恰消失在中间。“自我”的主体性消失,取之而来的是“自我”是由哪些碎片来源组成?这一问题追溯到社会层面,便一定是与社会生产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在这张《Figure in the bedroom》作品中所示,女孩的房间是由一大堆现代商业产品占据和包围,它们统统形成了消费工业思想碎片的组成部分。而这些来源于超大型的社会化流水线大生产的系统里面,“效率”一词,几乎包装成等同于“流行文化”,或许,我们可以说,波普艺术,或如今称为的潮流艺术,正是在这一架庞大且看不到尽头的生产消费的机器上的真正的“效率”推动器。
而张可可Kchaoz所要探寻的,正是流行文化所带来的,或塑造而成的当代新兴人类的系统之事实,至少作为对艺术家本人而言,张可可Kchaoz之所以在一个流行文化中,成为一个流行文化的波普艺术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流行文化是如何塑造这个世界的?以及在流行文化背后,还有什么?2015年,艺术家曾经创造了一家虚拟公司“GlobalHobby”,采用游乐场的概念,探讨消费空间与交换空间之间的关系,借以当代艺术市场的运作机制,包括图像专政(dictature de l'image)、符号抽离及挪用(l'appropriation)、集资(crowd funding)等概念,将艺术家与不同艺术助手分工,使之将艺术创造与商品生产模糊化,直指将艺术创作、交流、收藏等关键要素进行解构,甚至质疑大众消费心理的价值动机和来源。
于是,我们看到,在“Myth around the corner”的系列里,所有人物的眼睛,都被遮挡或甚至不出现在画面之内,故意去除“绘画中的凝视”,进一步加强了主体迷失的氛围。在这里,张可可Kchaoz在黑色方块的匿名符号的基础上,融合了艺术家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的割痕符号和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波点符号在空间交错而生成,正如在“Common Sense”系列中所使用的一样,并使其成为人物眼部的遮挡物。
该符号的出现,显然融合了最具美式波普的波点符号,与象征着决然打破绘画空间的割破画布的丰塔纳刀痕,变成了张可可Kchaoz对波普艺术的即反叛又融合的态度张力,正如丰塔纳的反绘画行为成为了绘画本身,当代艺术中的反艺术也成为了当代艺术本身时,任何的反叛似乎都成了一种玩笑,它似乎是一种戏虐,或是一种游戏,在这里,它又似乎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主题的新变体:关于“艺术”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它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缺失”?实际上,它等同于美国小说家卡佛所提出的经典疑问: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到底在谈论什么?
在张可可Kchaoz波普创作的历程中,这是艺术家一直在追问的线索和问题。而在“Myth around the corner”系列中,艺术家似乎又走向了青春回忆的时期。这显示了艺术家对时代问题的悬置,并期望回归到一种更为原初的艺术冲动与热情。在这里,张可可Kchaoz回忆起父亲曾在他暑期中,于图书馆借了一大堆艺术家画册。那些在空调房里躺在床上翻看这些充满着西方艺术的画册时光,对张可可Kchaoz来说,就是最美好的记忆。艺术家重新找到了这些来自于西方艺术史的绘画符号,并借之于古希腊神话,用类似于电影镜头的一种画面的整体调度构图的技术“Mise-en-scene”,将所有原本已有原出处的图像,经过反复筛选并通过数字技术重新拼凑成艺术家期望的新图像。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基于情感记忆交织的波普艺术。这是一种私人化的,饱含着艺术家的热情与复杂。在这里,我们又好似看到了一种重新诠释古典及当代艺术史的符号的波普转换。正如张可可Kchaoz所融合的多种手法,从日本、美国漫画,到Kaws、罗伊·利希滕斯坦、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村上隆,他将鲁本斯(Rubens)的经典油画《帕里斯的决断》(Judgement of Paris)中的三位古希腊女神转换成为了《Moder Paris》;将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神似照片的绘画作品《贝蒂》(Betty)转换成多件作品里的人物侧背形象;将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的多重转换过的作品《红船上的人物》(figures in red boat)进行再次转换,成为《Figures in salon》。
可见,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元素和图像,都有一个真正的原出处,艺术家似乎在消解了原初印象的同时,依然在搭建某种关联。它展现了一种新颖的绘画图像拼贴法,甚至连技法都来源于不同的波普技巧。它形成了一种流行文化式的忒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张可可Kchaoz将不同时代的流行符号,甚至连记忆中成长期所浸润的流行文化,都统统纳入这艘不断被拆解和更替的流行之海上的大船。这也正如在“那些花儿”的系列中,所展现出来的,对安迪·沃霍尔的花卉系列的再思考与再创作,正如张可可Kchaoz所说,在法语中,“la fille”(女孩) , “la fleur”(花) 都是阴性词,艺术家通过将花儿进一步细节化,拉近镜头,以营造出以消费广告语言中对准女孩的视觉感。
很显然,消费主义是流行文化在经济学上的结果呈现。它通过一代一代消费更替的文化覆盖,消解了本体存在的原始意义,正如忒修斯之船那样,也正是张可可Kchaoz一直不断在思索的问题。但艺术家似乎还想更进一步,要寻找流行之所以能成为流行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更基底层的美学原理。在这里,至少从女孩与花在消费主义中的表现就能看出端倪,因为经济学在自由主义中,视市场为自然律的运动法则和机制,至少,波普艺术的诞生,其本身就来源于商业美术,它作为一种视觉宣传,被带入进流行文化之中。
波普(pop)最早来源于18世纪的“棒棒糖”(lollypop)的简化口语,后用“soda pop”来表示可乐类汽水的开瓶声。很显然,波普首先就与感官愉悦产生了联系,它通过味觉、视觉和听觉等多方面来打开大众的感官享受,正如棒棒糖亦暗示了更为丰富的感官欲念,它所产生出的轻松愉快和享乐与渴求的肉体通道,统统成为了波普的一种感官转化下的美学表达。实际上,张可可Kchaoz本人就享受于颜色的纯粹性以及它所引起的欲望,这种纯粹性正是一种单纯欲望的视觉放大。他建立了一个色彩库,将同一画作的不同配色加以各种组合,从而挑选出最适合的色彩组合。
将图像、色彩、叙事、象征、构图、心理学等元素,通过调度技巧,把波普所带来的愉悦发挥到极致,这正是艺术家张可可Kchaoz正在做的。这是回到了波普艺术在原初本质上所进行的美学语言探究,但他所使用的丰塔纳的切痕符号,仍对当代艺术市场背后的系统组织化保持警惕。这是一种基于波普艺术在社会学上的观察,一种工业化、商业化和组织分工化的当代艺术系统正在形成,它暗示了一种非波普艺术的艺术系统正在走向波普化。
或许,一切正如安迪·沃霍尔曾经所预言的,流行艺术将成为未来的唯一艺术。而21世纪的张可可Kchaoz,或许正在这个加速消费的时代中,见证这一预言的形成。而这所带来的问题,也正如一开始我们所说,人类心灵迷失的时代,也将加速到来,精神危机下的“自我”在存在意义上的消融。或许这个时代的哲学特征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应该重新回到“位格”这一观点来找回我们的失去的本体论上的价值意义。
在张可可Kchaoz早期创作系列中,有一个不断重复的小男孩角色,艺术家将其取名为ogé,它将 ego(自我)反过来,成为一个“颠倒”的“自我”。这种对自我身份的思索,来源于艺术家在追寻童年时期接受的文化,是如何塑造成后来的自我意识,而这些文化符号又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成为产业链的集体式行为进入人们的生活。它至少从一个侧面开始去寻索关于自我身份(自我)的来源是什么?而这个“自我”在某种哲学前提下,被默认为是一种由语言(图式)所塑造成的某种“知识型”,或是“认知型”。这是一种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关于逻辑哲学的维特根斯坦对语言逻辑单元及程式化的“图式”概念,并揉杂了心理学及福柯关于“知识型”等多种同时代哲学元素的集合。在这里,它作为一种时代的哲学特征,试图去理解到底什么是“自我”,并最终可能演变成一种精神分析式的技术手段。于是,在这一顿分析之后,“自我”似乎消失了。
这正是由当代哲学所引发的问题所在。正如张可可Kchaoz的《Figure in the bedroom》中所示:“在昨天,你说明天”,而“今天”却恰恰消失在中间。“自我”的主体性消失,取之而来的是“自我”是由哪些碎片来源组成?这一问题追溯到社会层面,便一定是与社会生产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在这张《Figure in the bedroom》作品中所示,女孩的房间是由一大堆现代商业产品占据和包围,它们统统形成了消费工业思想碎片的组成部分。而这些来源于超大型的社会化流水线大生产的系统里面,“效率”一词,几乎包装成等同于“流行文化”,或许,我们可以说,波普艺术,或如今称为的潮流艺术,正是在这一架庞大且看不到尽头的生产消费的机器上的真正的“效率”推动器。
而张可可Kchaoz所要探寻的,正是流行文化所带来的,或塑造而成的当代新兴人类的系统之事实,至少作为对艺术家本人而言,张可可Kchaoz之所以在一个流行文化中,成为一个流行文化的波普艺术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流行文化是如何塑造这个世界的?以及在流行文化背后,还有什么?2015年,艺术家曾经创造了一家虚拟公司“GlobalHobby”,采用游乐场的概念,探讨消费空间与交换空间之间的关系,借以当代艺术市场的运作机制,包括图像专政(dictature de l'image)、符号抽离及挪用(l'appropriation)、集资(crowd funding)等概念,将艺术家与不同艺术助手分工,使之将艺术创造与商品生产模糊化,直指将艺术创作、交流、收藏等关键要素进行解构,甚至质疑大众消费心理的价值动机和来源。
于是,我们看到,在“Myth around the corner”的系列里,所有人物的眼睛,都被遮挡或甚至不出现在画面之内,故意去除“绘画中的凝视”,进一步加强了主体迷失的氛围。在这里,张可可Kchaoz在黑色方块的匿名符号的基础上,融合了艺术家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的割痕符号和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波点符号在空间交错而生成,正如在“Common Sense”系列中所使用的一样,并使其成为人物眼部的遮挡物。
该符号的出现,显然融合了最具美式波普的波点符号,与象征着决然打破绘画空间的割破画布的丰塔纳刀痕,变成了张可可Kchaoz对波普艺术的即反叛又融合的态度张力,正如丰塔纳的反绘画行为成为了绘画本身,当代艺术中的反艺术也成为了当代艺术本身时,任何的反叛似乎都成了一种玩笑,它似乎是一种戏虐,或是一种游戏,在这里,它又似乎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主题的新变体:关于“艺术”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它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缺失”?实际上,它等同于美国小说家卡佛所提出的经典疑问: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到底在谈论什么?
在张可可Kchaoz波普创作的历程中,这是艺术家一直在追问的线索和问题。而在“Myth around the corner”系列中,艺术家似乎又走向了青春回忆的时期。这显示了艺术家对时代问题的悬置,并期望回归到一种更为原初的艺术冲动与热情。在这里,张可可Kchaoz回忆起父亲曾在他暑期中,于图书馆借了一大堆艺术家画册。那些在空调房里躺在床上翻看这些充满着西方艺术的画册时光,对张可可Kchaoz来说,就是最美好的记忆。艺术家重新找到了这些来自于西方艺术史的绘画符号,并借之于古希腊神话,用类似于电影镜头的一种画面的整体调度构图的技术“Mise-en-scene”,将所有原本已有原出处的图像,经过反复筛选并通过数字技术重新拼凑成艺术家期望的新图像。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基于情感记忆交织的波普艺术。这是一种私人化的,饱含着艺术家的热情与复杂。在这里,我们又好似看到了一种重新诠释古典及当代艺术史的符号的波普转换。正如张可可Kchaoz所融合的多种手法,从日本、美国漫画,到Kaws、罗伊·利希滕斯坦、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村上隆,他将鲁本斯(Rubens)的经典油画《帕里斯的决断》(Judgement of Paris)中的三位古希腊女神转换成为了《Moder Paris》;将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神似照片的绘画作品《贝蒂》(Betty)转换成多件作品里的人物侧背形象;将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的多重转换过的作品《红船上的人物》(figures in red boat)进行再次转换,成为《Figures in salon》。
可见,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元素和图像,都有一个真正的原出处,艺术家似乎在消解了原初印象的同时,依然在搭建某种关联。它展现了一种新颖的绘画图像拼贴法,甚至连技法都来源于不同的波普技巧。它形成了一种流行文化式的忒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张可可Kchaoz将不同时代的流行符号,甚至连记忆中成长期所浸润的流行文化,都统统纳入这艘不断被拆解和更替的流行之海上的大船。这也正如在“那些花儿”的系列中,所展现出来的,对安迪·沃霍尔的花卉系列的再思考与再创作,正如张可可Kchaoz所说,在法语中,“la fille”(女孩) , “la fleur”(花) 都是阴性词,艺术家通过将花儿进一步细节化,拉近镜头,以营造出以消费广告语言中对准女孩的视觉感。
很显然,消费主义是流行文化在经济学上的结果呈现。它通过一代一代消费更替的文化覆盖,消解了本体存在的原始意义,正如忒修斯之船那样,也正是张可可Kchaoz一直不断在思索的问题。但艺术家似乎还想更进一步,要寻找流行之所以能成为流行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更基底层的美学原理。在这里,至少从女孩与花在消费主义中的表现就能看出端倪,因为经济学在自由主义中,视市场为自然律的运动法则和机制,至少,波普艺术的诞生,其本身就来源于商业美术,它作为一种视觉宣传,被带入进流行文化之中。
波普(pop)最早来源于18世纪的“棒棒糖”(lollypop)的简化口语,后用“soda pop”来表示可乐类汽水的开瓶声。很显然,波普首先就与感官愉悦产生了联系,它通过味觉、视觉和听觉等多方面来打开大众的感官享受,正如棒棒糖亦暗示了更为丰富的感官欲念,它所产生出的轻松愉快和享乐与渴求的肉体通道,统统成为了波普的一种感官转化下的美学表达。实际上,张可可Kchaoz本人就享受于颜色的纯粹性以及它所引起的欲望,这种纯粹性正是一种单纯欲望的视觉放大。他建立了一个色彩库,将同一画作的不同配色加以各种组合,从而挑选出最适合的色彩组合。
将图像、色彩、叙事、象征、构图、心理学等元素,通过调度技巧,把波普所带来的愉悦发挥到极致,这正是艺术家张可可Kchaoz正在做的。这是回到了波普艺术在原初本质上所进行的美学语言探究,但他所使用的丰塔纳的切痕符号,仍对当代艺术市场背后的系统组织化保持警惕。这是一种基于波普艺术在社会学上的观察,一种工业化、商业化和组织分工化的当代艺术系统正在形成,它暗示了一种非波普艺术的艺术系统正在走向波普化。
或许,一切正如安迪·沃霍尔曾经所预言的,流行艺术将成为未来的唯一艺术。而21世纪的张可可Kchaoz,或许正在这个加速消费的时代中,见证这一预言的形成。而这所带来的问题,也正如一开始我们所说,人类心灵迷失的时代,也将加速到来,精神危机下的“自我”在存在意义上的消融。或许这个时代的哲学特征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应该重新回到“位格”这一观点来找回我们的失去的本体论上的价值意义。
文/黑匣子

最新展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