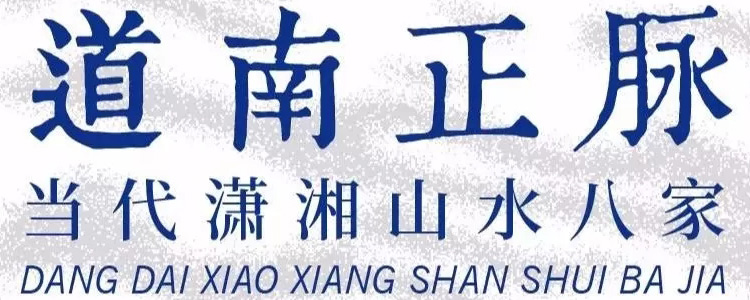
前言
“潇湘”
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 中山经》,书中言湘水" 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沣沅之风,交潇湘之渊"。及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湘水》,则说“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潇者,水清深也”。实际上,自中唐以后," 潇湘" 不仅意指湘水,而且被诗人们衍化为具有美学意象的地域名称。此后,潇湘一词广为流传,并被不断赋予新内容,如用作词牌《潇湘神》、戏曲《潇湘夜雨》、琴曲《潇湘水云》等,曹雪芹还在《红楼梦》的大观园里设置了一个“潇湘馆”。尤其是自宋代宋迪所创《潇湘八景》开始,更使得郦道元关于“潇湘”这一概念从地理学范畴延伸到了审美范畴。
从中国美术史的角度来说,由于受到明代董其昌等“松江派”的推崇,五代南唐董源的《潇湘图》更是受到文人画家格外重视,成为一种理想价值的图像。莫是龙将中国山水画,比作禅宗分为南北二宗,董其昌则突出了南宗的地位,使之提高到了文人画的高度。他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正因为如此,《潇湘图》无疑就是中国文人山水的原典,《潇湘图》中的“潇湘”,便历史地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的审美意象。
事实上,中国绘画史上关于 “潇湘” 的美学建构主要体现在“潇湘八景”的表现上。据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潇湘八景”原是宋代宋迪创作的八幅山水画的题目,宋迪选取湖南零陵湘水、潇水合流处的景色,绘制“潇湘八景”,分别名为:山市晴岚、渔村落照、平沙落雁、远浦帆归、烟寺晚钟、洞庭秋月、潇湘夜雨、江天暮雪。据传苏轼、米芾、文同、慧洪等还有潇湘八景图绘的题画诗,由于众多文人的参与便使得“潇湘”诗画母题不断衍化。其中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抒发遭贬谪的悲愤和怀古幽情。潇湘的自然山水承载了娥皇、女英为上古舜帝二妃的神话传说,以及投汨罗江以殉国的屈原的历史故事,熔铸了《楚辞》诗歌浪漫而悲怆的情怀,成为以后中国失意文人兴发思古和悲愤之情的意象。如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苏轼《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中有:“知君有幽意,细细为寻看。”强调了“士不遇”的忧愁。二是抒发羁旅行役的离愁。“潇湘”诗画中南方广阔水域里漂荡着的船只,湿冷的夜晚雨滴,也引起舟中过客离愁和望归的情思。如李白《秋夕书怀》:“北风吹海雁,南渡落寒声。感此潇湘客,凄其流浪情。”三是描写地域化的诗意胜境。宋迪开启的潇湘八景诗画,以诗文、图绘、音乐、舞台等艺术形式,“为好事者多传之”,从而推动潇湘胜境的传播,如元代的散曲、都市梨园杂剧中嵌入八景名目的表演唱词。
“潇湘”在南宋随中国东渡日本的僧人牧溪、玉涧等传入日本,形成幽玄禅余的游戏意味。如思堪《平沙落雁》突出落雁母题,解构了中国潇湘山水画的图式,表达超越尘世纠葛、回归自然的心志,且形成室町时期潇湘图绘的“多景同图”的山水特点,以及多个景点糅合于一首诗中的游戏。五山诗人横川景三的潇湘八景题诗:“景似潇湘四未成,以诗补画意分明,江山日落雪为雨,只有钟声无市声。以江天暮雪”“潇湘夜雨”二景融合为“江山落日雪为雨”一句诗中的暮夜、雨雪意象;以最后一句解构了“烟寺晚钟”“山市晴岚”,将四景融合于一首诗中,并赋予只有钟声的烟寺的新意。16 世纪日本潇湘八景诗画融于生活,出现大型屏风和隔间的“祆绘”。如狩野松荣为京都大德寺的聚光院作《潇湘八景图》大画面居室中的屏风山水,作为禅思观想的手段,表达追求平静、超越尘俗的幽玄。玉涧的潇湘诗画在日本清拙正澄、雪舟、云溪永怡等人那里得到回响,如清拙正澄《潇湘八景诗》为日本五山禅宗文学典范,其《潇湘夜雨》“玉龙漉润楚云寒,衡水沆波漏未残。若具摩醯顶门眼,暗中一点不相瞒”,运用佛教词语“摩醯顶门眼”,寓意洞彻一切的大智慧,方能秉持正念,富有禅意。
从“潇湘”到“潇湘八景”,随着文人的寄情感怀和诗画畅意,已经凝结为中国文化的独特审美意象,甚至影响到日本及朝鲜、越南,并且历史地成为了汉字文化圈共享的文化母题。当然,这其中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内涵,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根脉之中。
孔子说“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其实对于儒家而言,更多的是“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儒家喜欢“比德于山”。故而主张天人合一的董仲舒在其《山川颂》中也发挥孔子思想, 认为山之所以值得赞美, 就是因为山之高峻、宽厚以及滋养万物的这些自然特点“似乎仁人志士” ,“是以君子取譬”。至于“智者”何以“乐水” , 更多的是在道家方面得到阐扬。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从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角度来看,山水乃至山水画,便成为文人最为推崇的审美艺术形态。宗炳撰《画山水序》, 就说“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应会感神”而“神超理得”。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文人而言,“山水”与“江山”之别只在于一念之差,只是入世与出世的命运安排与态度选择而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何“潇湘”乃至“潇湘八景”能够成为文人诗画歌咏的隽永主题,就是因为潇湘具有一种远离权力中心而且又具有完整权力叙事的外在自然形态与形式。从山到水,从江到湖,从“潇湘”到“八景”,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文人情怀与人生理想的叙事结构,歌咏“潇湘”便是拥抱整个世界。或许“潇湘”与“八景”正好暗合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具体演绎形式,而且形成了一个在空间结构与时间流变相互统一的景观意象与浑然一体的自然图像,它既现实存在又别有诗意,它是文人内心世界与外在空间的完美结合,既是净土又生机活泼,甚至还有几分神秘与神圣。故而有杜甫歌咏洞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乾坤”之喻,有范仲淹的“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怀。很显然,“潇湘”是最能够契合文人士大夫“出”与“入”的心灵机枢。因此,“潇湘八景”其实就是中国文人对于乌有之乡的想象性文化建构,但却历史性地植入到中国文化的主流文脉之中。
从以上文脉追溯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潇湘”之于湖湘文化而言,更多的只是历代文人士大夫诗意化与理想化的一种文化想象与建构。湖湘文化真正崛起,乃至从边缘走向中心,其实还是从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晚清“中兴名臣”开始。至此以后,有戊戌变法的谭嗣同、武昌首义的蒋翊武、同盟会的黄兴、反袁护法的蔡锷等这些中国近现代革命先驱,直至出现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共和国开国领袖与将领。湖湘文化所孕育出的人才群体从支撑晚清的半壁江山到推翻帝制到共和国的缔造,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就了辉煌的一页。
从“潇湘”而“湖湘”,这是湖湘文化一种质的嬗变,是湖湘文化由自觉而自信的开始,而其内在生命力其实蕴藏在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中,这就是“道南正脉”的湘学。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据传作者是清代学者王闿运。有道是,王闿运曾到江浙一带讲学,当地官员为试他的才学高低, 故意探问他的学问之流派、渊源, 他便随口而出,结果弄得语惊四座。其实这正是对乾隆皇帝赐匾“道南正脉”的绝妙解释。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理学的重要策源地,也是湘学的鼎定之所, 其源脉本自濂溪先生, 即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毫无疑问,“道南正脉”由皇帝钦定,其作用无非一是正名,二是勉励,三是鼓舞。湖湘文化至此便有了真正的“内圣外王”、“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文化自信。其实,就宋明理学——湖湘学派的实质而言,主要体现在胡宏的以“性”为本体的学术思想之中。他说:“天命之谓性,一性。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诏,必曰心而不性,何也? 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又说:“六君子尽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 胡宏以性为体,以心为用,认为性是心的本体和本原,心是性的表现和作用。二者的联系表现为“未发”为性,“已发”为心。只可惜在一时号称潇湘洙泗的朱张会讲中,张轼略输给了朱熹的博学多识与巧言令色的辩驳攻势,不然的话,中国学术史上的理学就应该叫“性学”了。但是湖湘学术还是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肯定,并御赐岳麓书院匾额“学达性天”。湖湘学术这种立大本、达至善,已经融入到湖湘学人的血脉之中。所以,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再一次对中国学术进行力挽狂澜的拯救,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呐喊,这是何等的气派与担当。王船山的手稿经过曾国藩的收集整理与刻印,从而他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历史中得到确认,为中国现代思想转型奠定了基础。有现代学者称王夫之的思想堪比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其实在我看来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正是由于湖湘学术有这样深厚的底蕴与气度,湖湘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卓越表现就不难理解了。说到底湖湘文化的本质还是在于强调立本求源,以“内圣”为本,以“外王”为用,不断探索与实践,锲而不舍,正如屈原所谓“吾将上下而求索”。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潇湘”到“湖湘”,从“道南正脉”到“湘军崛起”,这是构建现代湖湘文化的基本线索。很显然,无论是从“潇湘文脉”还是从“道南正脉”以及“湘军崛起”角度来看,当代湖湘文化的时代张显主要还是在于建立文化主体性的自信。这对于与“潇湘”有着更为直接关联的湖南当代山水画发展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植根于“潇湘”文脉之中的现代湖南山水画,本来就有着与中华文脉心气相通的美学基因,再加上底蕴深厚的道学正脉传承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开创属于这个时代的“潇湘画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