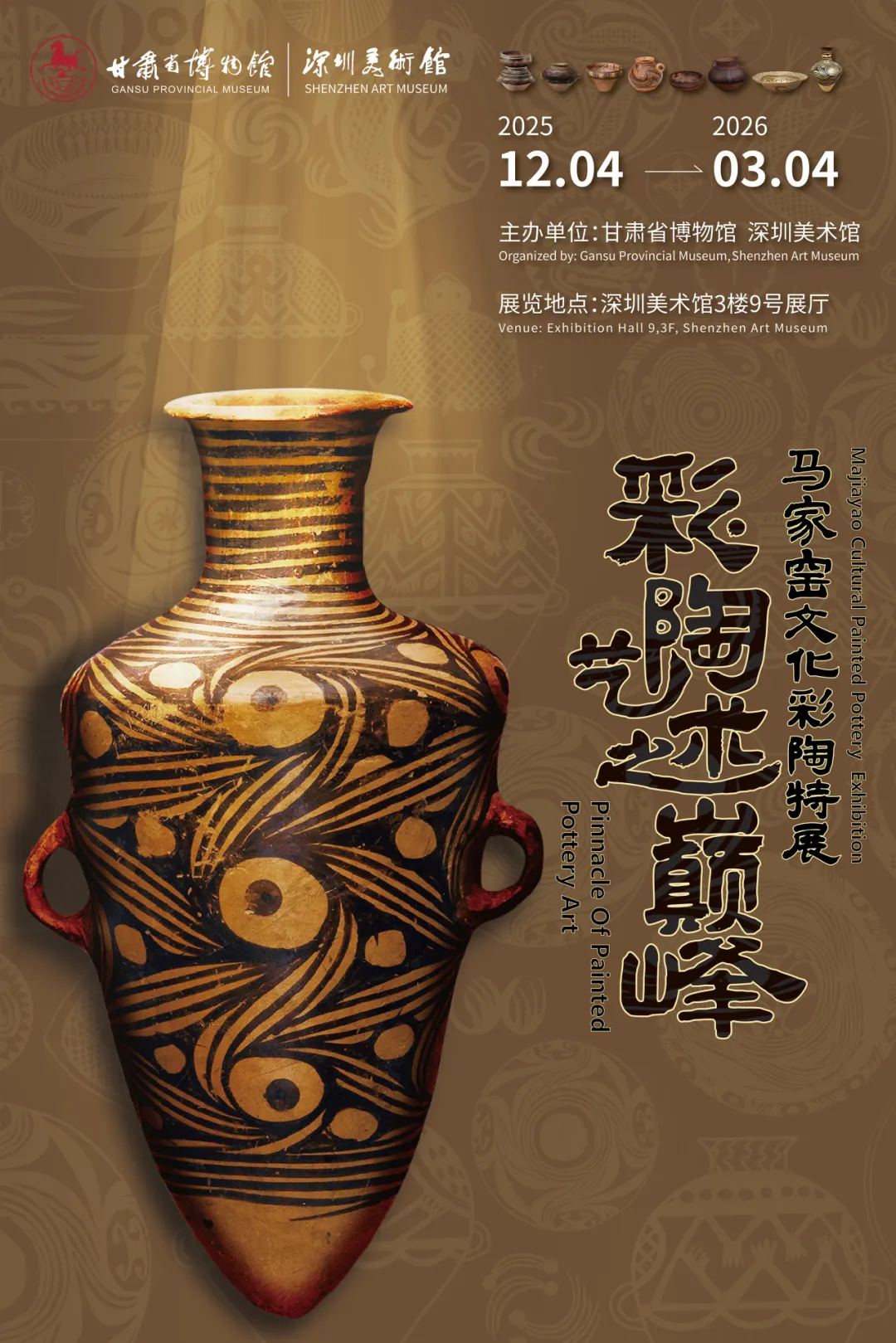此刻与那时——徐文涛的图像历史叙事
《此刻(thismoment)与那时(backthen)》是徐文涛自己给展览的命名,这一行为本身表明,徐文涛对自己作品的表达,有着思想和观念上的高度自觉,这正是徐文涛的特点,他是那种不仅艺术路径十分明确,也是思想十分清晰的艺术家。尽管如此,《此刻与那时》,仍然只是标明了展览所指向的时间或历史的维度,而缺乏展览意涵的指向。
因此,我们必须先对作品进行细读:徐文涛这次共展出了九张绘画(有两张是相同作品的并置),一件装置。我把绘画分成三组,《空舞》、《二月二》、《入戏》为第一组;《早春》、《入场式》、《鲜花》为第二组;《紫外线》、《做空》(两张并置总数也是三张)为第三组。全部九张都是场景绘画,当这些毫无关联的场景归并到一个展览时,就构成了一种有关联的图像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叙事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民族叙事、国家叙事、世界叙事。
第一组作品描绘了舞龙、舞狮、踩高跷三个场景,展示的是中国传统民间节庆表演,可以理解为在“中国龙”标识下的一种集体娱乐,因而是一种民族叙事。民族和传统、本土、民间等概念相关联。民族叙事是一种强大的叙事,特别是对于后起国家,民族叙事是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强大武器。但是民族叙事又必须有所节制,这里牵涉到民族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民族叙事一旦过头,会陷入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当今民粹主义的抬头,已经引起世界的警惕。中国当下,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未经反思的叙事语境下,加之大国文化复兴的宏大叙事的强化,民族叙事空前强大。从徐文涛的这一部分图像叙事来看,民族叙事具有自发的性质,基于朴素民族情感,并且以表演的方式来呈现。占据画面主体的虚张声势的高昂的龙头、纸质的狮子前兴奋的四脚朝天的舞狮人,还有虽然更高但牺牲了稳定性,踩在两根木棍上摇摇摆摆的踩高跷者。显然,他们不是历史叙事的主体。但一定是重要的底色和背景。
第二组由三张群众游行和社会主义集体劳动的场景组成国家叙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伟大领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呼喊声中,正是靠着这些仪式感极强,统一步调、整齐划一集体场面,凝聚了人心,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和社会共同体。新中国的国家叙事,伴随着一系列政治叙事,特别是基于近代史的叙述——中国一盘散沙导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致外敌入侵带来的屈辱历史的反复强化,衬托出集体力量、人民团结的重要性,由此凝聚了高度秩序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增强了爱国主义旗帜下的空前民族团结,奠定了今天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基础。作为60后艺术家,徐文涛对这些符号化的场面多少会有些记忆。他选取的图像也非常典型,集体劳动互助协作的经典场面、红旗飘飘昂扬向上的乐观情绪、手持鲜花排列整齐的群众行列,宣示出国家集体的力量。显然,在历史叙事中,国家叙事才是核心。
第三组是证券交易所和海边休闲度假,表现的是资本的交易场所以及资本带给人们享乐的场景。这是西方和中国的共同景观,因而是世界叙事,或全球叙事。改革开放以后,代表西方资本力量的证券交易引入中国,成为市场经济的象征之一,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活力,使得强国富民后的民众开启了休闲旅游的生活方式——中国加入了世界全球化的步伐。徐文涛世界叙事的图像,有意模糊了空间地点,造成一种无差别的全球化的假象,仿佛中国和世界已经同一。而事实上,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方式的同一,并不能消解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始终相伴而行。应该说,总体而言,徐文涛再造的全球叙事图像,表面上还是洋溢着乐观情绪:资本大鳄随意做空,证券买卖热烈,一派繁荣景象;河边拥挤着闲散的人群,世界一派太平。但我们知道,太平的假象背后,暗流涌动。消费社会引导着人们休闲享乐,但在消费的欲望主宰下,剩下的一切都被遗忘。这或许就是资本和消费主导下的世界叙事。这个叙事作为表象,只能是陪衬。
在民族叙事的背景下,在世界叙事的衬托下,徐文涛完成了社会主义经验下的大国崛起的国家历史叙事。
徐文涛的图像叙事方法,是对选取的图像进行再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重构,但徐文涛的重构方法十分节制,他对这三种叙事采用了等量齐观的方法,平行并置,没有显出价值趋向。用色和刻画上也非常冷静节制,在全部的灰色调的基础上,降低了颜色的的饱和度,九张绘画的手法也比较统一,倾向的隐藏给观者留下了思考空间。唯一的例外是《做空》采用了两张完全相同的大幅面场景并置,仿佛在提醒资本的强大与无所不在。
独立的九张图像并不能生产出意义,但是,三种叙事的同时在场,九张图像同时并置,就形成了意义生成的场域,不仅意义被生产出来,而且生产出多重意义,形成了复杂的图像隐喻和交叉重合的意义矛盾。民族叙事的本土性与世界叙事的全球化,国家叙事的政府主导与市场资本的原始冲动,民族叙事的传统文化自发与国家叙事的社会动员,国家叙事的庄严统一与休闲社会的个人消费,仪式感与随意性,乡愁记忆与世界市场,集体意志与个人追求,等等,全部交织在一起。投射出徐文涛在其展览自述中提到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平等主义与保守秩序,穆斯林与基督教,自由市场与政府调控……这些矛盾对立冲突的观点,与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取向纠结在一起,可以把不同实体空间的人们联合起来,也可以撕裂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机构乃至于一个国家。现实图景的混乱和不稳定性,使”历史终结“的乐观情绪正被某种不确定的普遍焦虑所代替”。这里,徐文涛表达的就不只是社会观察了,而是切身体验,是这个时代大家共同的经验。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视觉知识分子用图像思考问题所达到的深度。批评家冀少峰在徐文涛2016年的个展《身体叙事》前言中非常敏锐的指出:“由此亦可发现徐文涛视觉叙事的转向。他由身体叙事逐渐转向社会叙事的努力和勤奋,他由局部问题比如对绘画体制权力的质疑而置身对整个社会所普遍存在着现代化的现实终将被现代化焦虑所取代这么个关乎人类生存实境的思考。”在冀少峰看来,2016年前后,徐文涛的身体叙事转向社会叙事已经是一种事实,而在这次的展览中,徐文涛把他的社会叙事具体化为社会历史叙事,表明他的叙事策略不仅是一种基于社会经验的共时性观察,而且有了历时性的深邃的历史眼光。
当然,正如徐文涛自己所言,他在这里表达的一种“历史想象”,也许至多不过是伯格森时间哲学意义上的“虚假认知”。但在这里,正是图像化的“历史想象”或想象的历史,让我们走进真实的历史,它提示我们,以我们真实的生存经验去续写历史。
2016年的个展到现在,不过三年,徐文涛将笔触伸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图像历史叙事。其思考的领域的扩充,反映出他思想的日益成熟,也说明他对生活的观察深入到了社会的内部,堪称社会责任驱使下的文化忧思。为了使语言形式和他要表达的思想观念相匹配,他果断放弃了他擅长的写实技术,以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匹配其全新的叙事策略。首先,他放弃了画面三度空间的假象营造,回到现代艺术的平面性;其次,放弃了具体对象的形象塑造,采用了意象化的方法;画面还采用了散点透视的处理方法,画面没有视觉中心,引导观众从整体把握画面。但仔细观察,画面有一种渐变性的过渡处理:视觉重心在画面的下部,越往画面上部看,形象迅速收缩,到画面上部三分之一处,所有形象全部隐去,而当我们抵近画面观看整张画作,所有形象完全消解,只剩下不规则的大致相同的色块,如同所谓历史的碎片,必须统合,才能得到判断。显然,这样的处理,既有技术上的考量,也是思想表达的需要。这样处理的最直接效果是,画面设置了障碍,图像化的个人在画面中消失了,如果想在画面中寻找单个的人,我们必须后退。
同时,他还有意强化了材料的作用。为了达到所谓“用今天的语言材料讲今天的话,探讨今天的问题”的目的,在无法放弃油画材质的情况下,他减弱直至取消了了油画语言的固有特性,没有刻画,取消笔触,堆砌颜料,让材料本身的精神能量和观念能量最大化。
我们都知道,材料具有文化和媒介的双重意义,语言和材料的创新始终是和时代精神相呼应的。一直以来,受学院教育的惯性影响,当代艺术家大量使用传统语言表达当代内容,使语言材料和思想观念不够匹配,这个问题在徐文涛这里也显然存在。好在徐文涛是一个艺术史文脉十分清晰地人,也是具有强烈语言自觉的艺术家。但我认为,就他而言,以写实绘画来承载当代艺术观念,其语言的可能性已经被他榨干。而这一次,虽然他仍是戴着镣铐跳舞,基于表达需要和自身艺术特质,没有完全放弃传统媒材,但在语言风格上确实跨越出了一大步。
况且,为了加强作品的当代感。他采用了图像挪用再造的方法,强化了作品的图像感。他精心选用照片,用自己的方法复制再造。构图和场景与原图并无二致,但因为形象的减弱,色块的相互挤压,强化了图像表达的不确定性,为作品带来更大阐释空间。而大尺寸的画面和地形图似的肌理效果,也强化了观众的视觉感受和空间感受。
最后,我们还应该把目光投向徐文涛的装置作品。这次装置作品的呈现,一方面表明徐文涛在多种艺术表达方式上的尝试,以及作为当代艺术家对表达的材料和媒介的重视和探索。同时,作品以迷宫的形式呈现,迷宫探索者在时间之流中寻找出口的线性路径,以及出口的不确定性,也在内容上与墙上的绘画形成一种互文关系。
一个时时回望的民族,才不会迷失方向,作为一个一直对现实社会保持深度思考和关注的艺术家,徐文涛深知经由历史才能进入当下的道理。但经由何种历史?进入什么当下?艺术家以图像叙事的方式,给出了他的回答,尽管这种回答,要依赖图像的解析,并不十分明确,但他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让我们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无法置身事外,他已经做了艺术家能够做也应该做的事。
刘茂平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