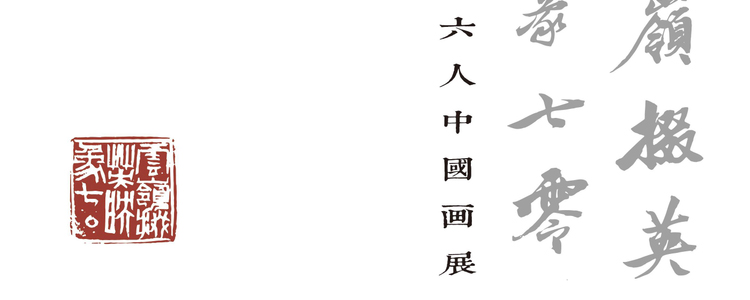
弁言——究竟这个展览
数月前,知满总、戴总、阿平哥、恩公、赵姐姐、朱平要联袂在昆推出一个画展。除却熟人情面的应承外,更觉着这是件好的事由,最起码看厌了完成任务的标准动作式的常规展览,他们的作品会有很多新意。
展览门可罗雀,这在云南办展稀松平常,当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方面确实是云南几无高质量的展览引入,像刚刚落幕的人气爆棚的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作品展,倘无高层领导的积极促成,万万是撬动不了云南文化艺术领域观展神经的。虽说不是网红展,微信朋友圈几乎都在新省博“打卡”,并有很多朋友来电希望能与省博的同仁疏通,希望看展尽量不用去排队,这样的罕事,说起来是好的,然而没有对艺术审美有认识和深度的领导以行政手段推行,高层次作品和欣赏审美的可能,或许还要有一段时间才会走进公众的视野。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的,在新时代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区域文化领域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展不平衡非常显而易见,艺术类展览“应景式”和“老干化”趋势严重,基础学术研究几乎没有,更与其他地域不同,自身艺术资源难以充分整合发挥优势。比如,从此次法国作品展,完全可以对云南油画进行结构性的梳理,并就云南油画的教育和当代性的一些问题展开研究,但自身缺乏必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展完了就展完了。
所以我想从一直在高校从事专业领域教学和美术相关工作的他们,对于展览,不仅仅只是采风写生创作、教学实验创作、国展创作、画廊商展的面目示人,所谓的学术除却有话要说之外更是有话可说,言之凿凿的更多是他们经年的学习累积,更或游学交流的感悟和收获。
当代美术,最喜欢用创新,但创新的思路和方向都很偏颇甚至极端。单纯以技术创新如科技,就是升级换代不断超越与否定之前。但人文领域特别是架上绘画,我个人认为不是。创新绝不是破和立的两极,是不断积累叠加的增长再创造与创新。
说绘画的创新,所谓风格的创新,当下很多都是从图示图像的概念寻找风格的方向,这个最后是视觉设计还是观念艺术?如果涵盖创作的过程是不是能够划到行为艺术的范畴?绘画,尤其是传统中国画、水墨的尴尬,就是一大波可敬的确是可惜的探索创新者终究走不通。
此路不通的终极原因是中国画本体土壤没有了,最主要是其环境的问题,文人的空间和环境没有了,哪儿还有文人阶层?没有了真正的文人也就没有正真意义的中国画。
现在问题是很多人依循着仿古,但作品有老气没有古韵,中国文人绘画的现代转化过程走到今天,需要时代的语境,所以他们依循传统但不因循守旧这就是新意。
做一个展览,一个有意义的展览,特别是在当下艺术市场低迷于消费降级的环境下,将名利场上的浮云摘掉,在市场调整的真空期,尽可以静下来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应酬,好好做一做专业,通过展览看看,让自己看看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也是今后展览要做的事。
在能静下来即便是不创作,读读书也是好的。自省后减少作品的重复制作,甚至从好的画材开始,尽可能用老纸、矿彩、研墨等等,从过程的一开始就注入人文性的创作思想与感情,在装池上也尽可能做到和作品的最佳匹配。做好自己,这才是这个展览过后的事。
几位画家,如今渐入中年,何必再取悦谁谁,再奉承谁谁。要知道做事不是给不懂你的人做的,而是要给懂你的人做的,即使懂你的人一万个才有一个又怕什么呢?
晚生杨瑾奉作
戊戌秋日于昆明百担斋旧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