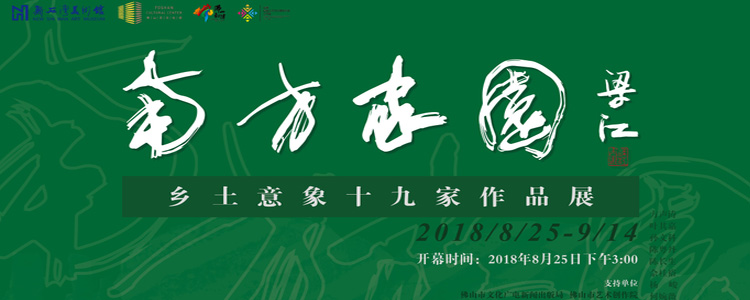
构筑理想的精神家园
——“南方家园”乡土意象十九家作品展有感
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组诗《回乡偶书》有两首,其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其二“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这两首诗一首写乡音难改,一首写物是人非,情真意切,非常感人。
然而时至今日,高速发展的社会里想要留住“门前镜湖水”来感慨一二,亦非易事。去年广东省新石湾美术馆举办“南方家园——2017珠三角水乡题材中国画作品联展”,梁江老师在《前言》里细说广东“水乡画派”的历史时,已经指出:“在当今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它们(水乡田园景致)越来越稀有,乡土与平凡不知不觉已变为一种奢望。如今,留下的或只是一种惆怅,一种无言的乡愁。”
今年广东省新石湾美术馆立足本土,继续推出“南方家园”系列展览。毫无疑问,“南方家园”系列展览延续了梁江老师在第一展《前言》里提出的问题,即面对家园的急速变迁,身处其中的艺术家如何获取新的体验和新的表达方式。这一提问,事实上隐含了一种期待,也就是期待艺术家能够跳出怀旧式的表达,而开创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的视觉主题和形式。今年以“乡土意象十九家”为副标题,同样也是想跳出“水乡题材”的限定,而试图呈现更为丰富的艺术创作。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有一句很有名的诗歌:“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如果我们将“南方家园”理解为一种“诗意的栖居”,那么我们在艺术创作里构筑的“精神家园”实际上应该有三个面向:一个朝向过去,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从容淡静;一个面对当下,看到那些“充满劳绩”的芸芸众生,而我们亦身处其中;还有一个应该面向未来,塑造一种理想的文化家园。从这个角度来看参展的艺术作品,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南方家园”,这个家园是我们熟悉的,但是又充满了让人惊喜的细节。何婉薇的工笔人物和花鸟以富于韵律的结构见长,设色清雅,富于水乡情韵;张健仪的工笔花鸟于细微处着力,一花一木一虫一鸟无不形神兼备;何海鹰的写生作品并不照搬景物,色彩古雅,构图精奇,颇有胸中丘壑;冼汉强的作品尺幅都不大,却于方寸之间尽显水乡风情;周志航的作品墨色淋漓,晕染出一方印象天地,时令节气的变化,和风细雨的润泽,尽在其中;叶其嘉的作品饱含情感,有一种深沉的爱和坚守,使他的画面意境开阔而又细节丰富;林亚谨的作品很有意思,他善于把控大场面,构图巧妙,用笔传神,将热热闹闹的民俗集会化入作品,远看有结构,细看有笔墨;陈长生的作品充满隐喻,水乡与女人这两个母题在他的作品里相融相生,又以对比强烈的色彩加以呈现;孙文科很年轻,但是即师古人,亦师造化,追摹先贤意境,书写南粤山水,墨色之间已见境界;封伟民的作品亦独具特色,一位陶瓷大师用国画表现自己熟悉的石湾公仔,一笔一笔摆出来,既有雕塑的质感,又有国画的韵律;黄展宏的山水写生结构严谨,构思巧妙,内里却又充满生活气息;佘桂裕的山水通过构图和设色,形成富有韵律感的画面节奏,有如一曲颂扬理想国的牧歌;方声涛多年游走于油画和国画之间,逐渐摆脱了技法上的桎梏,打破了画种间的壁垒,他的国画作品物象优美,对于故乡风物的情感自然而浓烈;梁伟堂的作品往往用饱满的色彩突出前景的花木,构图奇崛;陈粤丹久居曹溪,化韶关丹霞地貌入画,色彩浓烈,笔墨洒脱而有禅意;林沛锐画的开平碉楼,是南粤家园侨民文化建筑颇有代表性的一种,繁华与失落尽皆诉诸笔端;与很多人不同,杨峻并不回避城市化的进程,反而把城市作为大背景,凸显种田、浇水、垂钓等等主题,颇有大隐隐于市的感觉;莫肇生是土生土长的肇庆人,他自己营建的同古山庄可居可游,写于笔下不仅风光秀丽,还别有一份家园的感觉;黄泽森的故园系列作品,笔触潇洒,人物一颦一笑自有风采,却别有一番故园忆旧的萧索。
梁江老师去年寄语“南方家园”展,希望是新的起步,今年看到这十九位艺术家的作品,纷繁富丽,各具特色,但对于理想家园的热爱和憧憬是一致的,是相通的。这种情感是“南方家园”系列展艺术作品能够打动观众的核心,我相信也是这个系列展览不断为大家呈现更多惊喜的动力。
赵兴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广州美术学院教师)
2018年8月10日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