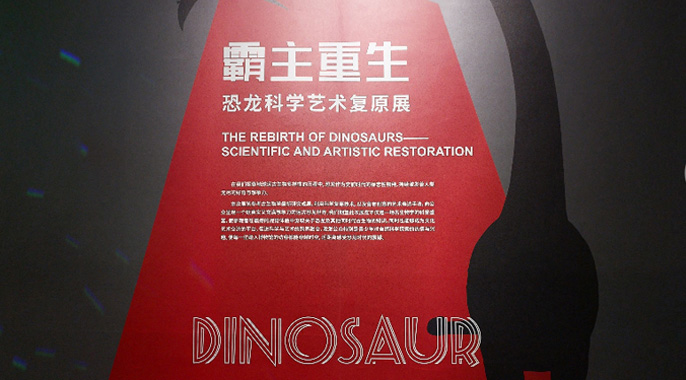我们只是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万物对我们缄默,仿佛有一种默契,
也许视我们半是耻辱,半是难以言喻的希望。
——里尔克
这次以“万物”为题的展览是高翔的第二个同名个展。不得不说,“万物”是一个“大词”,它总是和宇宙、世界、众生这些庞大的辞藻并列在一起,包罗万象、穷尽洪荒,这虽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美好愿望,但也表明了艺术家的心志和视域,也让人佩服他的勇气。
是的,勇气是解读高翔的关键词。我们在谈论勇气的时候,讨论的是什么,首先是选择的勇气,继而是行动的勇气,再而是坚持的勇气,这样的“勇气三部曲”也是成为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基础。回想对高翔的关注,也源于他的两次“有勇气的选择”。第一次他作为写意山水专业的研究生在毕业后的个展中以类似工笔的绘画方式呈现了他的“万物”,这在我的印象中能做出这样“出格”举动的国画专业的毕业生少之又少,和专业的细分化相伴相生的是个人的标签化,“一招鲜吃遍天”是很多人遵循的法则,更不要说严重的对老师的模仿,能够有勇气撕掉既有标签重新选择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对艺术创作而言更甚。第二次是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要离开南京去北京发展,当时他在南京已经小有名气,只以为他是说说而已,不曾想很快就在宋庄置办了工作室,开始了“北漂”的日子。对此,他说只是想换个环境,就像当初他不考本校的研究生而到南京来一样。敢于离开固有熟悉的环境,重新选择陌生和有更大未知挑战的生活,是高翔作为一个“行动派”艺术家的自觉。
如果说之前第一次高翔个展的作品还有些转型初期的生涩感,这两年高翔的创作已有了明显的变化,以“观物”系列来说,所描绘的仍是过往画过的水果等,却显然有了新的视觉体验。“万物有灵”,再日常的物品也有自己的性格,而好的艺术家能在作品中捕捉并传达出这种微妙的感觉,这是艺术家自身的技法、观念和心态潜移默化赋予的,不同的观看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义,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作品。作品是艺术家的镜子,可以折射出艺术家的心境与性格。数年的积淀不仅让高翔对这一系列的作品有了十足的把控,也体会传达出这些平常之物不同的性格。
除了“观物”系列的作品,这次展览还有其近些年创作的“蛰”、“昆虫记”、“器”三个系列的作品,“蛰”系列主要绘制的是各种“冬眠动物”,蜷缩在一个圆形中,安静的闭上眼睛,静谧之感尤生,同时又像一个生命,回归到蛋形的生命本体里,重新孵化。“一切景语皆情语”,蛰伏、静谧、重生,仔细想来,这不仅是作者的愿望,更是当下很多青年人的想法。“昆虫记”系列的作品虽然描绘的是各种昆虫,却完全不是“自然之物”,“绢本青绿大昆虫”更像是观念与材料的错置,而是充满了“异化”的特质,这不是法布尔笔下的《昆虫记》,更像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器”系列高翔更多进行了解构与附加双重的视角去审视,营造出自己独特的“器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