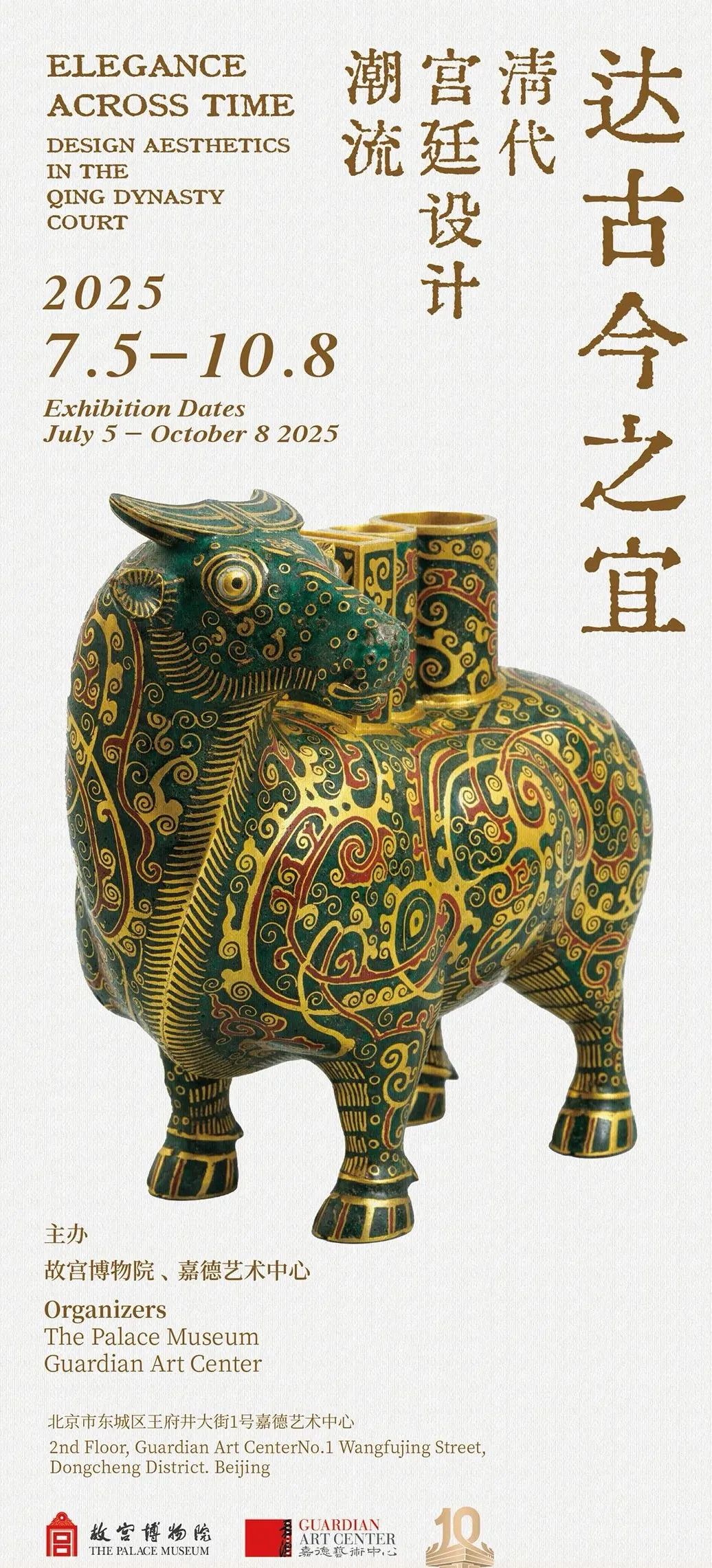无论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哲学的万物有灵,人与自然之和谐共生乃人类文明理念之共识。和乐生涯,最简单者莫过于亲手植一株树,栽一丛花,并从中感到生命的乐趣与真味。
稼轩词曰:“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诗人、文人、艺术家这些敏锐而丰富的心灵,似乎更容易倾向于寻找到一种草木与其相伴,乐之不疲,无怨无悔;反之亦然,那些不甘流俗的花儿,也终将遇见它三生三世的知己,人与花,彼此交付,互相成就。不单中国如此,西方亦复如是——所以有荷花与周濂溪,竹与苏东坡,向日葵和梵高,睡莲与莫奈。
黄山谷是酷爱兰花的一个人,然而却养不好,所以他心底很向往他的前辈王摩诘。传说王维是养兰高手,“贮兰以黄磁斗,养以绮石”,黄庭坚就在他被贬谪的地方修建兰苑,铺好石子,盖好亭子,把挖来的下山兰栽植个遍,结果兰草虽然养得不好,一篇《幽芳亭记》却千古流传。山谷还有一句著名的诗:“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说的是水仙,在我看来比之以兰蕙似为更恰。
不光山谷,被花恼的名流大有人在,比如现代的胡适之。胡适先生的小诗可谓家喻户晓:“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盼望花开早。”天天呵护日日察看,结果呢,却是“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兰草难养,所以他们最考验一个爱花人的耐性与坚持。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儒家精神里面,持之以恒是儒士心灵素养最基本的要求,折射到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皆能促使儒者格物以致知,齐家而平天下。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为士人推重的物事,兰草也好,笔墨也好,文玩也好,没一个好伺候的。
我伺候兰草转眼也已有十八年了。也曾疯狂而痴迷,也曾“被花恼”,现在过了七年之痒,有点相看两不厌,唯有兰与蕙的意思了——当全世界的别人都不待见我的时候,没所谓啊,我还有兰草!虽然,人到中年,琐事越来越多,除了血压,什么都不见提高,我还得继续写啊画啊,写作画画之余还得兰啊蕙啊,谁叫我浪得虚名,欠了兰花的风流债哪!
清明好时节,流连故乡栽花种草。今朝中良兄催我动笔前言,扔下花锄,草草而就。和兰花在一起,而非不以无人而不芳。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与人乐乐,和光同尘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