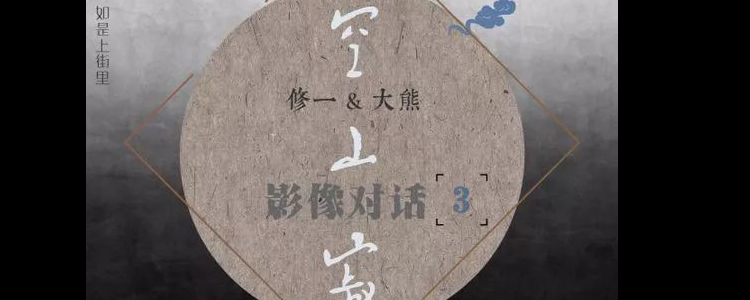
早在上个世纪,人类就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任何艺术的传播,都可以藉由批量生产的方式,进入大众中间。这固然是一种普及的方式,但是却不可避免地损伤了艺术的个性。
当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开始主动向大众审美靠拢。基于此,那些坚守自己创作理念的人,虽显得特立独行,却愈发难能可贵。
在此我们将要谈到的,是书画家修一和摄影师大熊——两人合作的“空山寂”艺术展,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当人们已经习惯从经验中罗织概念,我们不妨抛开那些先入为主的固有印象,重新审视两人的新作。
修一以纸笔水墨来呈现他心中的哲学观和宇宙观,大熊则尝试以手工蓝晒的方式,将摄影(或生活)重新曝光。
两人的共通之处,是以一种“不可复制”的古典精神,来拒绝现代社会的模式化平庸。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始终是艺术的重要命题之一。
从修一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一如既往的“古拙”中,看到一种更立体的情绪。他的作品正在逐渐跳出平面的局限,提高内心的诉求和认知的同时,亦是自我突破的过程。
而在绘画中,禅的主题仍在延续。尽管画作中的主角仍为小沙弥,但是对照修一之前的作品,可以发现,“人”的身影正在不停缩小,与此相对的,是天地的无限扩大。这是艺术家本人的自省,也是观念上的以退为进,是三千世界里的空明坦荡,也是“无我”和“有我”的相对相容。
大熊的摄影作品,削弱了忠实记录的成分,偏重于自我表达。他的镜头所捕捉的,与其说是日常的细节,不如称之为稍纵即逝的感觉更为恰当。空无一人的荒野、教堂的尖顶、黑暗中的星云……它们更像是被摄影师所虚构出来的现实,充满了寂静的诗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蓝晒的照片。
蓝色是脆弱的,忧郁的,像纳博科夫的蝴蝶;与此同时它又是无边无际的,代表着天空和大海。正是因为这种特质,最原始的手工冲印技法,反而带来一种奇异的美感。正如本雅明所说:“现实的那些非机械的方面就成了其最富有艺术意味的方面, 而对直接现实的观照就成了技术之乡的一朵蓝色之花。”
修一始终寻找着一个永恒的“所在”,而大熊则持续印证着不停变化的“瞬间”。他们在各自创造的同时,也在心照不宣地彼此影响。两人的默契与共鸣,一并构成了“空山寂”的独特叙事美学。
如此,虚空才有了内涵,山峦才有了高度,寂静才有了力量。
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提到:“阐释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而本次“空山寂”的作品,并不需要太多的阐释,它们传递出一种自信的沉默。
修一和大熊藉由这种向内的创作方式,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中抽身而出,或可说,这是一场完美的“撤退”——安静,从容,不卑不亢。
时至今日,空山寂已经成为属于修一和大熊的共同艺术符号,但是对他们而言,这个符号还在继续延伸,向更大的空,更远的山,更深的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