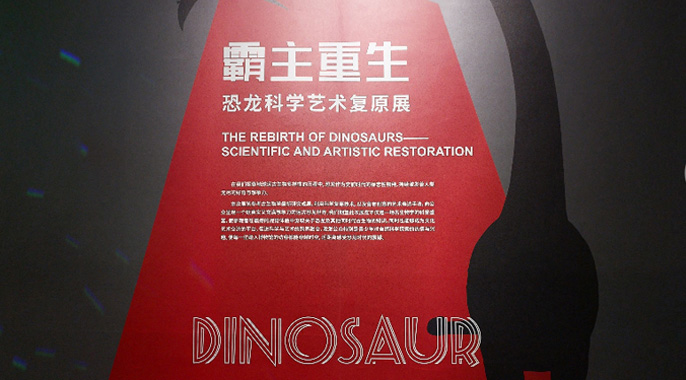画语心迹
语——是私语、心语,倾诉画者心灵之声。
迹——是足迹、画迹、心迹,是画者多年画画历程中足迹的记录,是画者个人在艺术追求过程中自己画迹、心迹的见证。
用语与迹开篇漫谈自己的画语心迹,创作来源于对对象的欣赏与兴趣,感动自己触动心灵。也许正如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谈到的,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创作的心迹正如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同时也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珍惜“语”在“迹”中的每一次呈现,也喜欢运用“迹”来抒写捉摸不定的“语”。我喜欢的语与迹也已经成为了也是我的画作品的名称《语》和《迹》。下面我从自己的角度去品读自己的作品,谈谈自己的创作心得和感受。
在我的理解中,画本身应该是活体的,犹如附有灵魂,每一幅作品的画面都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它们自己会向观者倾诉。好的画,应该是气韵生动,画面的构图与刻画的对象的造型与整体的形的关系也应该是共存于同一个时空里的。而画者在刻画画面时,虽然开始是对着是一张白纸,无中生有,一笔一笔描画出来,但画者与画的关系是互动与对话,是互为交流与感化。画作与画者关系非常微妙,画本来是画者画出来的,但画面呈现出来的又往往存在许多不定性和偶然性,也许正是因为画者的无法预知与把控,画作作为独立的个体反而有了生命,并指向无限与未完成。继续着永远的“未完成”是画自己可以与画者对话,也可以与观赏者对话,当画者停下作画进行观画时,画者也成了观赏者。新的关系的产生,画与观赏者的关系又变成了无限的可能。当然,随着时空的变换,不同的环境心境使观赏者处于一个变化的状态,也就是说,动态的观赏者产生动态的感受,因此与画的对话也就有了万千的变化。可以说,唯有画是活体的,气韵生动的,才能至始至终牵系着画者、画与观赏者三者并使它们在互动的过程中产生共鸣。
作为画者,有时自己画着画也会迷茫,特别在调整画面阶段,不自觉就会对某个局部着迷,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尽办法对其细节进行刻画,殊不知太投入或者刻画过分,就会是整个画面显得特别唐突不和谐,也就是说,由于过分在意细节而忘记了它也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最好是自己要觉醒过来并退出来思考:该怎么对画面重新调整?自然而然,这个母问题也会引发一系列子问题:画面的调整是否只单单停留在绘画基本的绘画语言上的推敲?形与型要对比吗?四边如何分割?空白如何取舍?绘画的基本元素点、线、面的位置经营吗?诸如这些,看似零碎的疑问就会紧扣着自己的思维,进入自问自答模式。这种思考的状态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就像我,有时瞪着挂在墙上的画看很久,看着看着……想着想着突然也会想到别处!又会突然想到与之关联的甚至是无关联的一些东西——比如想到曾经读过的一段文字,想到某个片段的对话,想到听过某曲……想到琵琶的、二胡的、古琴的……甚至想到不同乐器演奏它的不同版本。又如某个片段对比色彩的出现:当红豆跟绿豆洒在一起时,我会突然被眼前这红绿对比色的搭配给迷住了,色彩的对比使得红更红绿更绿,这让我无限遐想……刹时想记下这瞬间的美。同时也想起读过的《红豆词》:“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的春柳春花满画楼……”。情感体验似洒落的红豆一发不可收,在自己心里生根发芽。当然,画者拥有一种能力,就是他们的想念和感受可以借助图像作为载体,化作一笔笔的线条,或是缤纷多彩的颜色。这些线条和色彩受情绪的影响,有时可以是淡淡的接近平静的湖水,有时又是汹涌澎湃的波涛。当然,这两种对比强烈的体验一般容易让人感受到,而介于这两种间的那种似有似无的感受却是最微妙又最难捕捉的,正如《红豆词》里写的:“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那种欲言又止欲说还休道不明看不清,又会让内心有隐隐作痛之感。正如我的作品《潜》、《淋》、《碧》,这组画就是对这种感受的刻画。而技法表现在这组画的创新是工笔的各种染法和没骨技法的结合。画面上的色渍、墨渍、水渍所生成的肌理效果形成了一个活泼、生动、清新的画面,从情感上也正体现了画者内心的一种感受,所有甘如醇蜜、涩如黄连的感觉交织地在画者心中存在,让画者更清晰的看到自己。而另一幅作品《笑》是对比色强烈的工笔画,技法上采用了勾勒、分染、晕染、罩染,背景草绿色用了“撞水法”,繁茂细密的小叶组成了块面衬托出画面主角娇媚的百合花,用西洋红从花瓣的瓣尖染入,有如美人的纤纤指尖,用白色从花瓣边染入,又如美人的笑脸。整个画面就像一个佳人站在水边,对影自照,一张盛开的笑靥,是晨曦初现天际时映入眼帘的第一抹风景。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因为创作这幅作品时我的头脑里总是联想起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的诗句:“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当然,作为观赏者,每每观赏此画,随着心境的变化时间的流逝,画面所引起的感受又永远都是变化着的。
画者的情绪影响着画者的作画,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对画面的构图的经营到具体绘画再到勾线上色无不受画者情绪的影响。情绪的变化影响了线条的粗细和节奏的变化,也影响了画面色调的冷暖取舍,直接涉及到画面的气氛的把控。而心里对情感体验的敏感度也会影响画面具体描绘对象的形的造型。其实,各种染法也是在造型,所以画者在运用各种染法时也是画者内心情感体验借助染法在造形上的倾诉。所以当画者在对画的造型注入情感体验时,画自然而然也有了自身的生命,反过来画也与画者进行交流倾诉。比如作品《约》(入选国际有知名度的大型展览“北京国际双年展”的作品)的创作经历就是如此,可以说,《约》是一幅呈现生活中很多被忽视的空间和细节的画作,当然,它的产生可能缘于一个意外的偶遇,或者是时间的一个间隙,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源于偶遇和间隙的作品往往反而更让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约》的画面中间的木桌曾是闲置在某个熟悉的角落,精致的玻璃器皿零零散散插着干花与枯枝。桌面木纹清晰,显示玻璃瓶的质底透明清澈,也为了清晰地透出干花枯枝原有较好看的造型。画面正中仿似墙壁又仿似天边的浅灰色块,衬托出瓶中交叉依偎着的那两三枝干花;白云朵朵自在飘逸,与沉着的深蓝色天空形成对比;蝴蝶与瓶花相互对照和谐统一在一个巧合的空间,它们似乎也流露出一种有别于喜和悲的表情——也许是在窃窃私语,倾诉着一个似真似幻,若远若近的故事。所以每次观赏这幅画,我就会从画者的角色转换为欣赏者,角色不同情感自然有所变化,有时是情不自禁想哼起某段歌,有时是情不自禁吟咏某首诗,不管情不自禁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都是画者与画作再次的情感交流,是弥足珍贵的也是变化无穷的。《约》在技法上,画面左下方的木纹和插在玻璃瓶中的主体花卉,都是采用了没骨法 ,主要是“撞水法”。色彩上,主要用了淡淡的蓝色渲染,作为画面的背景色,一只活泼可爱的蝴蝶用的是重彩色调,与画面的主色调蓝色冷色调形成对比关系,整幅画表现出一种轻快、清新、淡雅的感觉。
也许修道的修行者是以日复一日的颂经抄经的形式修炼。而画者是以日复一日的一笔笔的勾线、分染的形式在修炼,对于画画也是以一颗虔诚的心如信徒般纯粹的,也是在修道。但修行者的修道与画者的修道两者有区别的,画者修道过程要读书增长知识让思想饱满,内心感受丰富,从而促进听、嗅、触、味、视等感知觉保持敏感不麻木,通过画面的载体表达出来,回馈给画者与观赏者去体验身体周绕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气息。所以画者必须有一颗敏感的心,不忘初心。初心应该是敏感的,也是所谓有感觉,灵感的源头。心是靠“修”与“养”达到明心见性。所以,我时刻不忘告诫自己,要心存信念,不忘“修”“养”,将一种看似简单的行为(如勾线、分染)持久耐心的坚持下去。记得某天看到一段文字大意描述也是如此,若要把顽硬的玉石变为润色灵性的美玉,是靠“养”出来的,如何“养”便是不停的抚摸,是养玉人日复一日重复简单的动作,就是手对玉石的抚摸。而画者也如玉石,应该好好“养”,在自己心与手的摩挲中“养”出各自的神采。感恩岁月际遇记忆中带给自己的感受体验,丰富着自己的感知觉,让自己保鲜着一颗敏感的心去体悟生活与生命的点滴,将心比心,慢慢感悟花花草草不同生命各自自有的活活泼泼的精采。
蔡谨蔚丙申年腊月于小景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