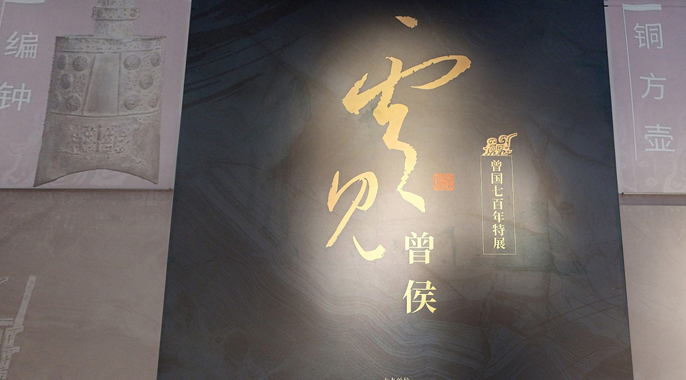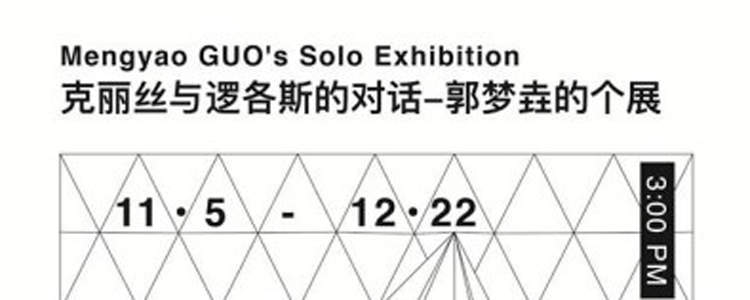
八大画廊将于11月5日至12月22日举办“克丽丝与逻各斯的对话-郭梦垚的个展”。
一直以来,郭梦垚对三角形十分着迷,三角构成是她作品中的唯一符号。对理性的持续探索也展现出这位年轻抽象艺术家的冒险精神。“逻各斯”源自古希腊语“lógos”,在希腊早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的理论中,“逻各斯”被描述为逻辑、秩序与理性的综合词汇;而“克丽丝”源于“crystal水晶”的音译,象征透明、光泽、渐变和冲突。在创作过程中,绘画工艺与材料的选择决定了郭梦垚作品透明光泽的属性,给人“克丽丝”的直观感性,而通过数学运算严格控制的尺寸,精确推演的色彩变化,无笔触痕迹的绘画方式,始终延续了艺术家绝对理性的“逻各斯”状态。郭梦垚的作品中,三角形构成矩形时会形成两个朝向,艺术家将相近色调整齐排列在相同朝向的三角形中,从而产生一种视觉冲突与错觉。同时,为了保持整体色彩的统一,艺术家在局部上色之前已用颜料在画布定出冷暖色调,这也使作品完成之后的色彩更加丰富饱满。
关于克丽丝与逻各斯的对话
在展览泛滥的时代,一个不错的展览名字承担着传播与学术的双重责任。我们也会常常讨论与质疑一篇前言之于展览的无用性,这里的无用性包含同质化与可替代的作品描述以及生僻词汇构建的语言奇观。在此将“克丽丝”与“逻各斯”作为展览的标题以及本文的论点则希望翻译过后的中文词汇能从字面的无意义转化为一种可被记忆的符号。
三角形作为郭梦垚造型语言中唯一的符号,如何在单一的特性中找到成立的自身逻辑与规律,这其中包含三角形的物理属性与艺术家理性架构的复杂表达。三角形作为所有多边形的构架基础,及许多复杂几何问题的理论支点,在艺术家看来其拥有强大的自身属性。因此三角形之于作品整体类似于雨滴与江海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种物理结构下的形态转换过程。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保持着一种绝对理性的状态,选择了一种数学运算式的创作法则,严格的尺寸控制,推演式的颜色填写及弱化笔触感的边缘线描绘。希腊早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率先将“逻各斯lógos”引用为哲学词汇,在他的描述中:万物源于逻各斯。并表示,杂乱无章的事物经过逻各斯的秩序整合连结后形成了所谓的智慧。因此在赫拉克里特的理论中逻各斯成为了逻辑、秩序与理性的综合词汇。将“逻各斯”引用并用于描绘郭梦垚的理性绘画,正是源于两者在关键词上的交集。
有别于“逻各斯”词汇的哲学意味与特殊指代,“克丽丝”源于“crystal水晶”之词前段的音译。在展览筹备期与艺术家的沟通中,提出了可用于描绘郭梦垚绘画颜色的一些关键词:透明、有光泽、有渐变,有冲突。而水晶的物理属性恰恰与这些词汇相关联,因此“克丽丝”与“逻各斯”一样可被看成是有趣或便于记忆与归纳的标签。谈及关于郭梦垚绘画颜色的关键词,透明与光泽是属于绘画工艺与材料选择的问题,而颜色的渐变与冲突则再一次回到艺术家对于绘画的理性控制之中。我们至少可以在其画中找到两条有趣的色彩逻辑,第一条跟三角形构成的矩形画幅有关,三角形若要组合成矩形必然分为正反两个朝向,而郭梦垚的渐变色或色相相近的颜色都出现在相同朝向的三角形中,这样的颜色分割从视觉上既可以凸显三角形的本来特性,也是人眼对色彩产生视错觉的构成源泉。另一条色彩逻辑则与郭梦垚的颜色底纹有关,如何让看似用三角形分割平涂的整幅作品保持色彩的统一性,艺术家应该在局部上色之前做过整体的冷色或暖色的颜色处理。这种做法在保持了色彩统一性的同时亦使最外层的颜色更为丰富。
去年夏天因为一次展览机会采访到邓箭今老师,在谈到教学时,邓老师一直强调并反对自己的学生像老师,对于郭梦垚的评价便是:一个具有冒险性的学生,是一个完全不像自己的学生。据我所知,郭梦垚进行三角形的抽象画创作与研究将近六年时间,六年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需要坚持过程。而在中国进行抽象化创作确实需要具备冒险精神。在非艺术专业或是非抽象画创作与研究的艺术领域会对抽象化的难度、出发点、造型语言、随机性表示疑问。这其中跟中国抽象画创作与研究的历史较短有一定关系,官方展览系统对于抽象画创作还处于半推半就的阶段,民众对于抽象画的认识依旧与装饰画很难进行有效的区分。本次展览选择“克丽丝”与“逻各斯”的对话则希望用看似轻松方式去回应我们面对抽象画与一个年轻艺术家创作中关键的问题的提出。
林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