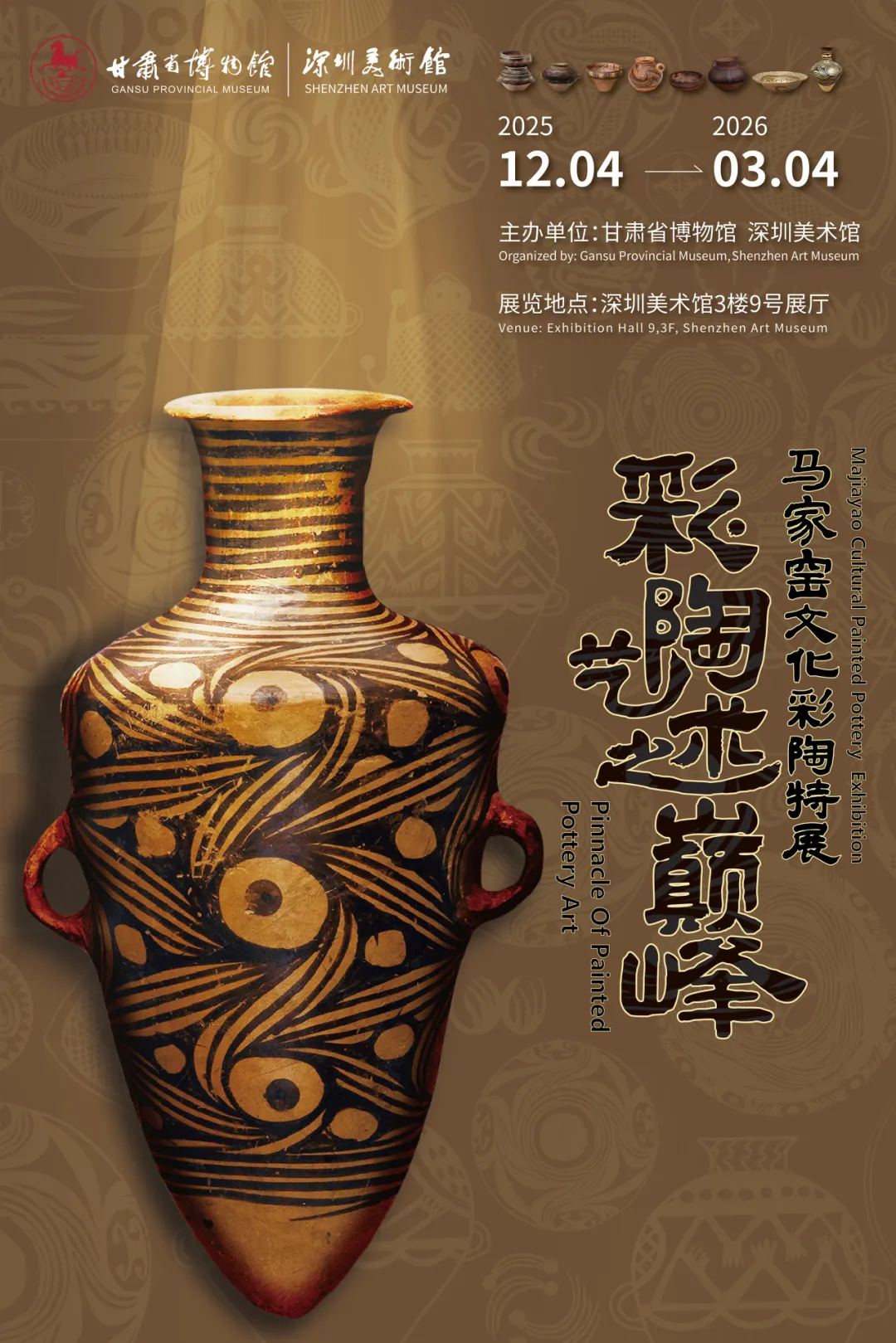2013年7月6日-8月22日及2013年7月24日-9月15日期间,由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主办,知名设计师朱锷先生担任总策展人及艺术总监的“隙间——隈研吾2013中国展”分别于上海证大当代艺术空间和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两个展场举行。本次展览充分利用美术馆的建筑优势,将展览内容分布于主馆(喜玛拉雅美术馆)及分馆(证大当代艺术空间)内,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审美及感官体验,并引发其对生活空间设计和共享方式的思考。
其中,位于证大当代艺术空间的展览部分,展出9件隈研吾的建筑作品模型及相关影像资料,包括“梼原木桥美术馆”、“太宰府表参道星巴克店铺”等;而在喜玛拉雅美术馆的空间内,隈研吾先生将两层楼高的1:1模型介入其中,在建筑内部分享当下社会逐渐普及的SHAREHOUSE概念,阐述如何在共享空间中保留独自发展的“隙间”。观众可以亲自走入此建筑模型中体验何为“共享空间”。
何为“隙间”?隈研吾认为,物与物挤在一起、没有缝隙的状态,不仅仅会显得透不过气,更重要的是难以应对环境、状态以及使用方法的变化。如何在建筑中酝酿出隙间,是隈研吾目前最重视的一点。20世纪为了追求强度和精度,建筑放弃了隙间,最终令其难以适应社会和生活的变化,变得脆弱、不自由。隈研吾用石头、木材和竹子在留出隙间的前提下打造建筑本身,希冀发现建筑的全新可能性,打造拥有隙间的建筑,令建筑重获自由。
提起隈研吾,大家可能很快地想到了他的“负建筑”理念——“在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不刻意追求视觉需要,也不刻意追求满足占有私欲的前提下,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建筑模式?除了高高耸立的、洋洋得意的建筑模式之外,难道就不能有那种俯伏于地面之上、在承受各种外力的同时又不失明快的建筑模式吗?”这是他对建筑发出的疑问和反思,我想也正是从这个疑问中生发出了他对建筑的重新思考和定义,至少我从这个疑问中获取了一个关键信息,也是我认为理解隈研吾“负建筑”理念的关键词之一——“去象征主义”。也就是说,当建筑的象征意义已经取代或者远远胜于建筑本身的其他功能性,变成了表现政治权欲或者经济发展指标的时候,这是否是人类对建筑所要追求的合理化发展趋势?这是否是我们想要打造的世界?各种奇怪的建筑拔地而起又不断地消失,正如隈研吾所言:“建筑变得越来越脆弱,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然而如何去象征主义?不再为了视觉背后的政治权欲和经济指标的追求;人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它到底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不至于变得“脆弱”?我想这是当下建筑师需要一直不断思考的问题。尤其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建筑已经摆脱了现代工业化时代的要求,转而追求适宜“人性化”的诗意空间,我们所倡导的“创造”不再是现代主义的“机械论”所理解的随心所欲的对秩序的破坏,而是在于“既带来自然秩序又带来社会秩序”(引自《后现代精神》大卫·雷·格里芬编)。这是后现代主义要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范式,同样适用于对建筑的重新解读,即“创造”一个建筑其实是在营造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不仅包括建筑本身的造型、结构、材料、设备、功能等是完美的有机结合,而且也包括建筑与人文生活、自然环境等是生态的有机融合。建筑作为我们的“创造物”,他应该是顺应且符合当下,像一个生命体。
隈研吾的建筑正是综合考虑了建筑的造型、材料、功能等自身构造加上和外部的自然、人文等环境的融合,就像生长在大地上的一个新的生命体一样。“格兰纳达表演艺术中心”是他为西班牙格兰纳达市设计的以蜂巢状外形的一座歌剧院。无论是整体外形上,还是其内部空间,均以六边形为单位。这让我们想到了神奇的自然界创造出了许多六边形的图形:雪花,龟壳,干裂的土地,长颈鹿的花纹等。六边形被称为能以最小量的材料占有最大面积,所以对于歌剧院来说,六边形正好实现最大化的容量,在结构上又实现了不依靠桁架和结构框架的巨大无支柱空间,让人又不失舒适感。有人说,这和格兰纳达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石榴"的粒子状结构很相似,它像是自然界创造出来的另一个六边形生命体。
他的另一建筑作品“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建筑了一个长270m的屋顶,像一条长长的鱼,正如鱼肚子里的各个器官一样,在这个细长的建筑物里也分布着各种“器官”功能,学生每天在这个“鱼肚子”里自由的、欢乐的穿梭,享受多重文化活动的集结,它像血脉神经一样连接着学院和学生们之间的脉搏,学生们在这里自由交流又像是加快了“鱼”的血液循环一样,让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想这也恰好体现了一贯的欧洲学院氛围。他的建筑能将自然、社会、历史、人文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建筑焕发生命活力,同其他生命体一样,共生在大地上。
我们不禁要问,隈研吾的建筑为何要这样去做?或许我们从他在接受《东方早报》的专访时的两段文字可以窥见些许:
如果把现在的中国和1980年代的日本做一个比较,确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大兴土木、拆旧修新,但也有一些不同。在1980年代初的日本,尊重地球环境、保留历史精髓这种意识还没有。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中国承担的历史使命比当年的日本更沉重。我现在在中国,包括在上海做的一些项目,也非常重视环境、历史。
通过这次灾难(3·11地震),更令人感受到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法左右的。正因为如此,反过来当我们重新审视“失败的建筑”时,可以试着去尊重自然,而非一定要战胜自然。通过这种方式,去创造出属于我们人类的真正的强悍。
他的这段表述,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建筑的重新认识,他的建筑是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自然的肆意破坏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重建和谐的生态系统,这就是区别于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建筑,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有机主义”建筑。正如大卫·雷·格里芬在描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特别推崇倡导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一样,隈研吾的建筑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有机主义”建筑,是后现代精神倡导下的“绿色建筑革命”。他的“绿色革命”并不是依托在物质主义下的时尚标语——提倡高科技能源的开发和消耗的“节能减排”,他的生态意识反而是遵从自然,回归到“有机主义”中。然而他的有机主义却又不同于现代建筑运动中的“有机建筑”派别,因为他又发展了“隙间”的概念,即在一个既有的建筑有机体里,“倡导在享有独立空间的同时,又与其他人相互联系,是这样一种融合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孕生出更多家庭、社会结构的可能性。我希望这种结构可以对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引自《东方早报》专访)
因此隈研吾的“有机主义”建筑不仅是对我们所处社会和自然环境所做出的生态性的创造物,而且也是建构社会人文主义的文化生活标本,一个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因此,我更愿意将他的“负建筑”理念理解成“有机主义建筑”,体现了后现代精神中的社会综合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