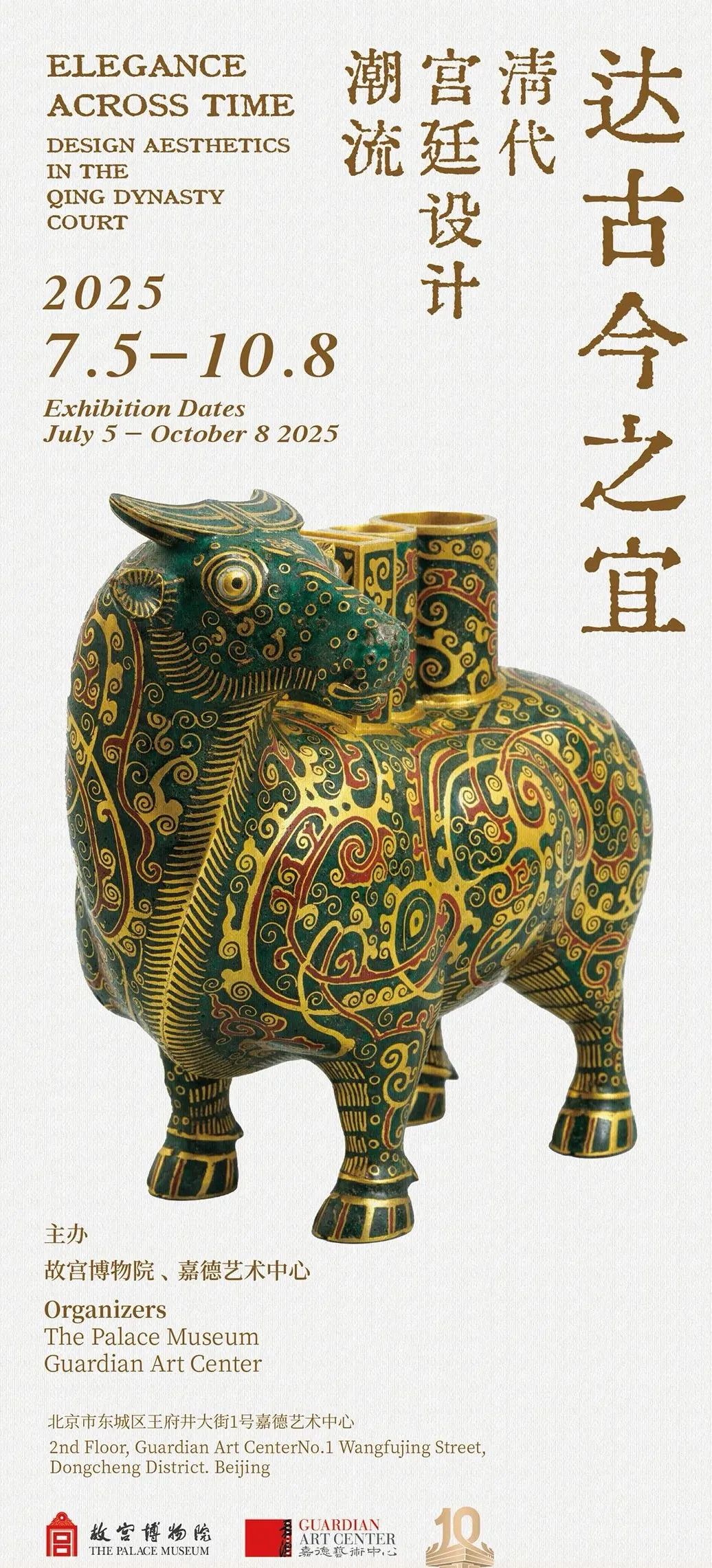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怀疑的悬置”最早由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及哲学家柯尔律治提出。概念本身很简单,但也很必要:假如作者能在叙事中包含一些读者亲历过的熟悉的元素,那么读者就会自然而然地悬置对故事真实性的怀疑,无论情节本身听起来多么荒诞不经。诗人提出这个概念,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作品,如代表作的《古舟子咏》 (1797-1798)和《忽必烈汗》(1797)等,并不是作者一厢情愿而无法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的空想。
尽管“怀疑的悬置”这个概念本身的文学价值在诗歌界里一直备受争议,但是争议的核心可能超越了文学,而起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艺术中的摹仿问题的哲学论争。
对于柏拉图来说,摹仿是艺术家的“阿基琉士之踵”。这位古雅典哲学家认为摹仿只是对现象世界的复制而已。他看不起摹仿,因为他坚信现象世界根本是虚假的。现象世界中的万物都不如与之相对的那纯粹的,形而上的理念世界高贵。现象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种劣等摹仿,而任何对现象世界的再现自然是劣上加劣。因此,无论艺术如何精湛地再现现象,它都与那个真实的,无法用视觉再现的纯粹世界相去甚远。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唯一能让悲剧感人的因素就是演员尽力再现生活中的劫难。一场演出越能真实再现生活,就有越多台下的观众能取得共鸣,从而起到释放和净化人们心灵的正面作用。
然而真正挑战柯尔律治理论的,却是现实生活中的虚构性有时候甚至比想象力走得更远这个事实。也许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悲剧作家才会把叙事削减到只剩下真实可信的情节的地步。也许他们明白,正是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造就了生活,尽管苏格拉底曾在别的场合贬低这种说法。总之,“怀疑的悬置”拥抱的正是这样相反的两极,一极是艺术中的真确性,而另一极则是生活中的超现实性。本次展览中许多作品毫无疑问是积极摹仿生活的,但与此同时它们又虚构如同小说。它们是某种隐匿在社会结构潜意识中的现实的双重显现。参展的艺术家来自丰富多样的艺术领域,他们的媒介包括摄影、影像、雕塑、纸上作品、行为艺术等,分别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了策展理念。
参展艺术家周文斗的雕塑是用卷尺缠成的一具形状诡异犹如肉体的作品。它并不协调,看起来有点像虫茧,但同时又有着一种优雅的混乱。卷尺千回百转,反衬出强调经验和量化的认知论的徒劳。数字、计量、实证主义最终均堕入西绪福斯的怪圈。一言以蔽之,精确最终要败给熵。类似的信息似乎可以在另一位参展艺术家阿道夫·多林相对平铺直叙的图像中找到。多林的图像乍一看很平淡,甚至是冷漠的,但却内有乾坤。它看起来像是某种现成的都市景观,可是很快却让观众意识到弥漫的黑影并不是数码制作的,而是对纽约2003年8月那次大停电事故的记载。图片中烂漫盛放得有点不合时宜的花朵为这个本来就有点哥特的场景添加了一丝不详,似乎被激怒的自然终于要向人类发起反攻了。在构图的最右边是一个隐约可辨的裸女涂鸦,它如同一种现代的拉斯科岩洞壁画,它将在未来记录着我们的现在,即未来的过去,记录美利坚大帝国衰落时这个大都会的境况。艺术家的痕迹在此并不明显,是消蚀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在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摆荡,或者套用弗洛伊德的词“诡异”(uncanny),逼迫人们去直面现实世界中偶尔的荒诞。虽然也有其他艺术家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去处理地理景观的主题,但他们的方式更加折衷。
参展艺术家弥古尔·罗德瑞格斯-萨皮瓦达的作品用墨水和哥伦比亚毒品战争中的受害者骨灰炮制出了田园牧歌式的哥伦比亚热带景观。作品的起源是这样的,艺术家曾旅居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号召民众参与一个悼念国家毒品战争中的无辜死难者的活动。他从这则广告中获得灵感,作品混合了两种材料,一是死难者的骨灰,二是当地旅游明信片中用来描绘哥伦比亚景观的墨水。作品既饱含诗意,又透着悲悯,旨在吸引人们去关注哥伦比亚社会中犯罪肆虐的边缘地带。另一位参展艺术家托马斯·奥绰同样带着政治批判的目光来关注土地。他的影像作品《阿里阿得涅PF-Z26》(2007)是一件单频道影像,影像从一条林中小径展开,似乎有什么物体在小径上移动,但又没有透露其真实身份,只能隐约听到沉重的呼吸声,直到行走停止。最开始的林中景观是用彩色拍摄的,但是渐渐化成眼镜框上的图像,该图像最终蜕变成一个黑白的,反乌托邦式的工业废墟。
另一参展艺术家斯图亚特·克劳夫特的《几团小火》(2007)同样探讨虚实之间的微妙关系,但是是在人造物的语境之下。这部影像作品由三个商业广告组成,推广的却是根本不存在的商品。三个推广的品牌分别叫“阿卡迪亚”(Arcadia),“斯达尔”(Stare)和“纽曼”(Newman)。“阿卡迪亚”逐户推销一种治疗失眠的药物。片头出现了一位穿着华丽晚装的女性,她一脸焦灼无法入眠。显然,这位女性的状态和片中所鼓吹的那种“阿卡迪亚”(古希腊神话中的田园)式的舒适生活大相径庭。事实上,与其说她是药物的受益人,还不如说她反映了当代女性集体经历的存在主义困境。如果说一条广告表达得还不够清晰的话,那么《几团小火》中所有广告加起来表达了一个总的信息,那就是无处不在的市场营销策略是如此混淆视听,让消费者手足无措。任何人都需要食物,水,睡眠等等,但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奢侈品。而商家却总是在刻意误导消费者,硬说这是一种需求,而不是欲望,因此我们纷纷沦为马克思所诊断的“商品拜物教”的牺牲品。
参展艺术家吉吉·塞罗尔的作品《魅影操》(2005)同样探讨了现存的视觉生产手法通过驱使人们的欲望以达到剥削的目的这个命题。《魅影操》这部影像既是关于性的,又是无性的。通过抹除了交媾双方的性器官,来创造了性或色情的对立面。这部引人瞩目的作品挪用了网络的色情视频,配以律动的音乐背景。身体的运动,明显的性交姿势频率与爆炸性的音乐节拍共同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张力。人们想通过观看获得感官的愉悦,然而碎片式的呈现却让人们的希望落空。马修·韦恩斯坦的《美国式哥特》(2003)同样表达了欲望所带来的割裂,该雕塑由几截手骨组成,固定在墙上,以45度角向外突出。手的主人仿佛在参加一场社交晚会,举着鸡尾酒杯中的小伞。该作品的题目取自格兰特·伍德1930年的著名绘画,画的是一名美国中西部的老父和他的老处女女儿很骄傲地站在一栋镶有尖顶窗户的仿哥特式房屋前,父亲手里拿着草耙。不过韦恩斯坦用鸡尾酒小伞代替了草耙。如此一来,韦恩斯坦将原本美国写实主义的象征转化为一种死亡象征。但死亡并不是韦恩斯坦的单一主题,因为鸡尾酒小伞不仅为作品平添了一分黑色幽默,还似乎有着观念上的指涉,仿佛这种饮品装饰是生活的必需品一样。同吉吉·塞罗尔一样,另一位参展艺术家费伦·马丁的作品同样吸引观众不时以艺术家的视角去看问题。
《模块》(2001-2010)是马丁一个持续进行的行为表演,曾在世界各地,包括纽约,马德里和迈阿密举行。其中一次于2001年末在纽约的圣约翰大教堂以及其他城市举行。这对于该教堂来说是特别的一天,因为那是个动物祈福的日子。如同动物的精神寓言一样,猫科、犬类、爬行类,各种各样的动物及花草汇聚在马丁的行为表演上,而马丁自己则头戴一个镜面立方体。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拉康的“镜像舞台”启发──超现实的,嘉年华式的镜子房间,世间万物都会在这里显现。在这种意义上,艺术家在独自探索世界的过程中试验了一种超现实的人种学。犹如某种自行移动的“块根”(rhizome)(译者按:植物学用语,被左派学者借用,形容理论和研究的多重性、非中心性、分裂性和相关性)一样,反映出主观与客观,中心与外围的二元对立性。我们看自己,如同艺术家看我们一样;而他看我们,又如同我们看他一样。人种学问题同样是参展艺术家提姆·马奇的双重肖像作品中研究的因素。比如他把一个脱衣舞娘和一个办公人员并置,把妈妈和女儿并置。这些图像涵盖了社会、家庭生活中的主体,揭露出不同人物之间的紧张感。尽管人物看起来轻松随意,观众却能隐约察觉出他们面对镜头时的刻意。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同样涉及到虚伪的肖像,比如艾瑞克·雅克尔用文字和图像描绘兰斯·阿姆斯特朗的绘画。
艾瑞克·雅克尔描绘阿姆斯特朗的系列绘画被命名为《睾丸》(2009)。阿姆斯特朗是一名世界级的自行车手,而他曾被诊断出患有睾丸癌,因此艺术家赋予了作品这个名字。雅克尔目前为止的众多作品横跨了多种媒介,包括雕塑、装置、绘画及综合媒介,对其作品的阐释也是多元的。他的创作核心是祛除流行文化身上陈腐的光环。他的创作方法包括具体化,滑稽化,他驾轻就熟地运用观念,为作品设定密码,只有解码他的观念,才能读懂他的作品。另一位参展艺术家威姆·德沃伊同样探讨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分,但是是在粪便学和科技的领域内探讨的。他的作品是装着粪便的装置《泄殖腔》。
《泄殖腔》原本是一架消化美食的机器。它包括了消化及排泄的过程中产生的排泄物。最终的成品是漂亮的亚克力盒子内装着真空包装的粪便。德沃伊的惊人之举一方面讽刺了“商品拜物教”,同时又讽刺了近来颇为流行的技术至上的观念。既然机器能够为人类代劳一切,那干嘛不干脆为人类制造点粪便呢?这种反叛的姿态同样能在摩吉·特内姆鲍姆的作品 《安慰剂 II》 (2010)中看到。《安慰剂 II》 是两联绘画,主角是一名淡蓝色背景中的修女。从右边看,修女仿佛悬浮在半空中,而从另一边看,修女则把法服倒穿,因此只能看到她的头部背面。该作品仿佛是贝尼尼的著名雕塑《陶醉的圣特蕾莎》与“慈悲修女”的结合。两联绘画交相辉映,在丰盛与哀伤,自由与禁锢之间摆荡。悬浮在此变成了空间的郁积,与另一位参展艺术家孙尧的具有催眠魔力的,纪念碑式的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孙尧的绘画似乎有种把观众吸入的气场,但这不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宏大,事实上,他的画面是精致优雅的,是万里晴空而不是万丈深渊。那种吸入式的品质来自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对话所形成的张力。其图形有平面化的特征,而背景则采取单一色调的模糊形态。更中肯地说,孙尧的作品通过某些类似幽灵与幻影的面容和形状召唤着观众。在他的作品面前,我们似乎悬停在精致的美与魅惑的丑之间。孙尧可说是画家中的画家,他如此不着痕迹地给时空划上了休止符。另一位参展艺术家斯特法诺•卡格尔的LED雕塑《9月11日》(2010)同样关注时间悬置的问题。
卡格尔的作品源于他生日日期的一个巧合,他恰恰出生在著名的911:纽约双子塔遇袭,多达3000人丧生。卡格尔于是以此为出发点追溯历史上同一天发生的事件。其中包括:9月11日,公元前9世纪─條陀堡森林战役结束;9月11日,公元1926年──刺杀墨索里尼计划失败;9月11日,公元1973年──印度古鲁尼姆·卡洛里·巴巴(教派领袖)逝世。这些事件之间除了日期之外似乎并无内在联系,但它们不禁让人联想到尼采提出的“永恒复归”观念。在刚过去的今年的9月11日,作品在世界不同地点于同一时间展出,于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与空间轴上创造出自己的悬置。
“怀疑的悬置”演绎了可信性及其对立面,并把二者视为对等物。确实,无论是故事、电影、动画,还是艺术品,听起来看起来越是贴近真实生活,观众的投入和信任程度就越高。然则现实生活却往往并非如此,我们都知道,它可能比虚构更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