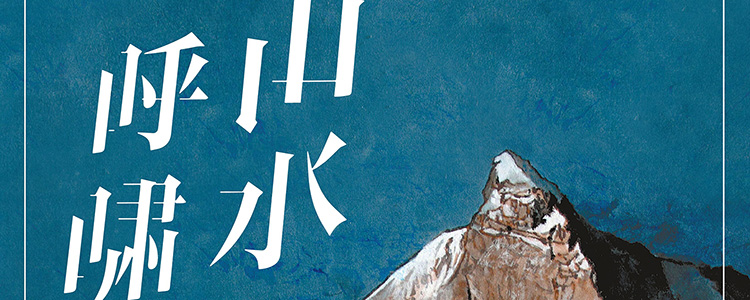
近代以来,在西风东渐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社会结构的消逝和西方绘画在中国的兴起,使得历经千年的中国水墨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度令水墨创作陷入尴尬的境地。然而危机往往也意味着契机,自彼时起,无数艺术家更新求变的努力,促使水墨画告别了孤芳自赏,开启了与世界的交流和对话,从而塑造了当代水墨的新面貌。其中尤其不能被忽略的,是那些漂洋过海的水墨艺术家。他们身处异域,却始终坚持对于水墨艺术的探索,同时,不管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艺术思潮的浸润——于是,他们成为中国水墨艺术在世界舞台上生发绽放的媒介。前有张大千、曾佑和,后有刘国松、冯钟睿,继之以谷文达、郑重宾等艺术家……,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他们远赴异国,相对自由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实验空间,在创作中他们不断打破陈规,随时而进,令水墨艺术在新的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面貌,著名中国艺术史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曾言:“现代中国绘画的创新,一部分来自于海外的那些艺术家。”意即在此。
刘昌汉先生正是这些开拓者中的一员。他自少年起开始习画,先后师从胡念祖、刘文炜、黄君璧,上世纪七十年代自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负笈远赴西班牙,开始漂泊异国的艺术生涯。刘昌汉先入西班牙费南度艺术学院学习壁画,数次在西班牙举办个展,又转赴美国芝加哥入瑞•沃艺术学校学习摄影,毕业后一直在美从事艺术创作至今。跨越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艺术领域一路走来,刘昌汉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流浪者”——这种流浪并非命运使然,而更似一种主动“选择”。对于作为其从艺起点的水墨传统,刘昌汉既有着深厚的理解与挚切的眷恋,同时又保持着一种警觉,他说:“传统对后代既是丰硕的资产,也是不可承受之重的负担,留给后继者定型的固化观念。”或许,正因怀有对“被固化”的担忧,刘昌汉才选择自我放逐于异域,置身他国及其他艺术领域,以一种“失根”的状态,有意保持与传统的距离,再经由其他艺术形式反观传统。这使得他对于水墨艺术的回归,成为一种剥落熟套,摆脱程式后的返璞归真。
多年来游走天涯,广大的世界令人眼界开阔,另一方面,漂泊异域也令人产生孤独。不过,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孤独有时反倒是一种催化剂。孤独使内心变得沉静和敏锐,世间也唯有孤独的心灵能够于静默中感受天地,体会个体与宇宙间的无声对话——这或许正是“流浪”赋予的心境。因此,刘昌汉的作品常常让人感到一种少有的苍莽与静寂。他笔下的雪山、飞瀑、云海、枯木乃至梯田和村落,常为阒静无人之境,即使偶有人影或动物出现,也往往是静默的独影。不同于传统山水画作为文人雅士对于山林向往的寄托而存在,刘昌汉的山水并不为人提供悠游其间的想象,而是以冷峻苍茫的山川形象映射庞大宇宙不息运转之一瞬,藉此而发的,是对于开辟天地、贯穿时空、源生万物的洪荒之力的赞叹,以及当有涯之生命面对无涯之宇宙时发自心底的感喟。观刘昌汉的作品,会让人不禁想到陈子昂的诗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种个体身处于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当中时,所产生的孤寂感是永恒的,也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无关古今中外。而刘昌汉笔下峭拔耸立的山川,绵延横亘的云海,带人们走到了独自面对天地的“那一刻”,在那里,地域的差异、文化的区隔都被遗忘,大山大水,大开大阖,静对默观,自能体味其中生命力与自然力往复不绝的震撼。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追求,刘昌汉十分强调艺术要“还原山川的本色”,他认为,一切过度诠释的艺术,都存在着使艺术沦为附庸品的危险。他更关注艺术作品关乎直觉的性质,避免过多文化属性和意识形态的介入,因而他能够放下成见,打破艺术形式和地域文化的界限,成就独特的艺术效果。壁画般的构筑手法造就了刘昌汉作品的气势,摄影般的构图和光影处理,明亮的前景凸显于暗色背景之上,为画面赋予了出色的光感和场景感。不同艺术手法的交迭运用,塑造出刘昌汉作品奇妙的视觉效果:近看时墨色蓊润,不乏中国水墨的气韵,远看时却只见光影明灭,具有油画般的丰富色调和凝重感。这种奇妙的效果同样体现在观众对作品内容的反应中:同是面对刘昌汉笔下的雪山,生活在北美的人会说,这是洛基山,而生活在中国的人会说,这是喜马拉雅。这种特点或许正反映出刘昌汉作品中对于生命和世界的体悟——山川、天地、宇宙本是同一,无关国界,不着古今,人生本是一场无边界的逆旅,艺术与人生,都是一场于流浪中不停寻觅的历程。
怀有“流浪”之心的人,是无法满足于原地踏步的。近四十年来,除艺术创作外,刘昌汉的足迹渐及策展、艺评、艺术教育及艺术研究等各个领域,先后在西班牙、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举办个展及参与策展,出版、编辑了《百年华人美术图像》、《游美国、加拿大•发现美术馆》、《北美华裔艺术家名人录》(英文)等著作,发表艺术评论400余篇,阐述自己对于水墨艺术、当代创作以及当代美术馆发展的思考。他既写严肃的学术文章,也以“刘吉诃德”为笔名写面向大众的艺术杂文,理性中肯之余,亦不乏幽默犀利。无止境无边界的探求与思考让刘昌汉的创作思维更加活跃,除了纸本水墨创作,他也尝试以水墨为语言,以影像或装置为媒介,进行更多样的创作。2001年,他曾与蔡国强合作开展以水墨为主题的当代艺术实验,通过观念、表演、录像等形式,探寻水墨艺术的更多可能性。
谈及海外水墨的艺术变革时,刘昌汉曾言:“从某种意义上讲,海外艺术家在异域的挣扎起到一种文化反刍与净化的作用,带来水墨画传承与接续的新的可能。”而刘昌汉本人正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者, 他笔下铺展的无限山川,展现了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历程。这既是刘昌汉个人的艺术之路,也是中国水墨在海外演变发展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