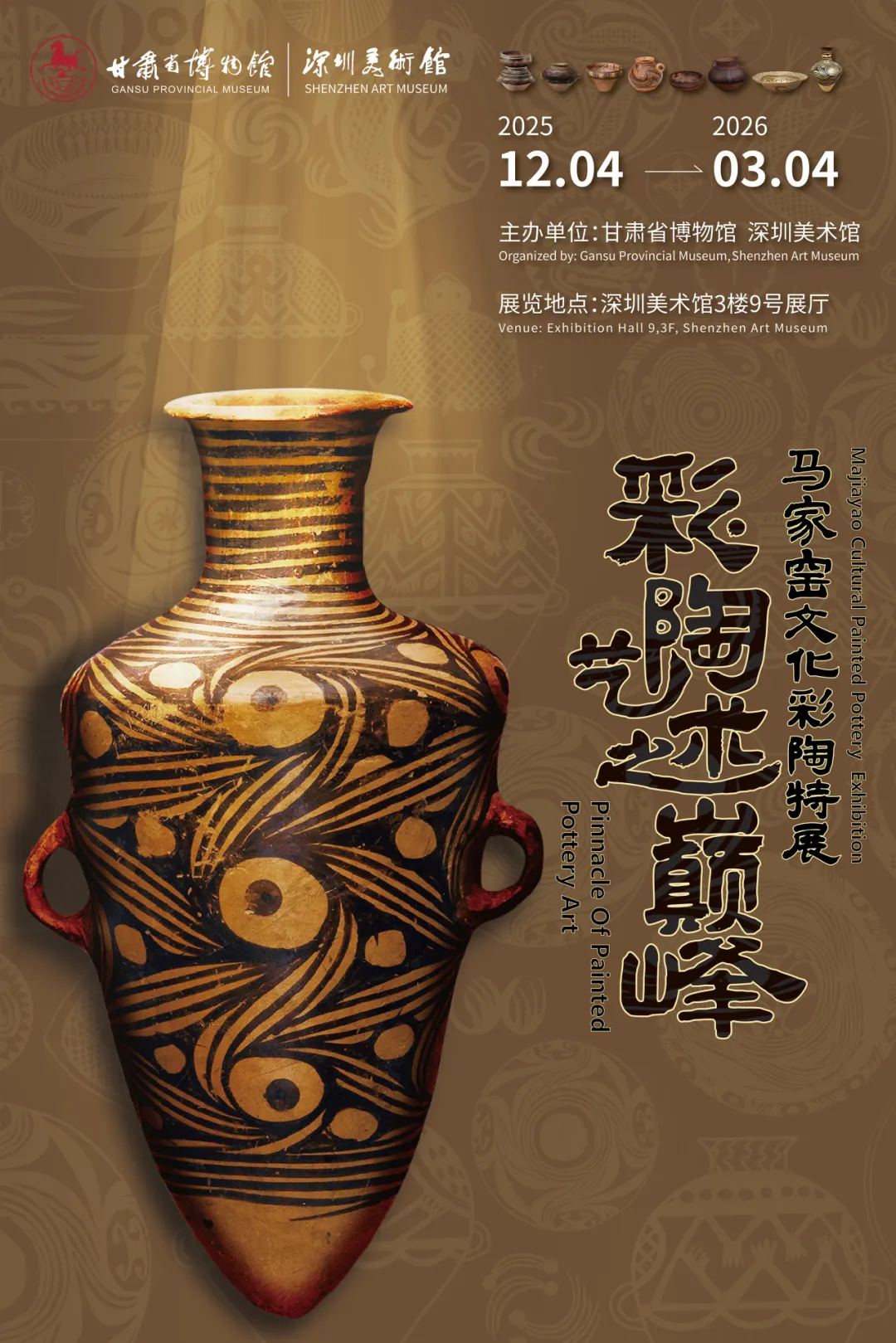山水花鸟,东方典故,看着让人恬淡适意、心生欢喜。远眺青山,鸟飞云海,假山虫语,院落人闲。叔夜在竹林里为清风流水拨琴,即便是休憩,人们似乎也已听到琴声,触到风凉,溅到水滴。还有惊飞燕子救了蝴蝶的会意之微笑,有山羊对汽车的破局之趣味,这分明,使传统人文山水的悠悠渺渺之外又多了几分智慧的生气。还有艺术家典型的剪贴印边、“毛毛人”笔法,的确让人感到了艺术那一点点神来之笔的妙处。
一回味,这艺术背后显然是顺天、中和、归真的东方人文价值回归。夏老的作品,让人见到了久违的、真正的中国气韵。近代百年挨打的屈辱,把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精气神都疼没了。很长的历史里,心性的淡定闲适、宁静致远几乎成了奢侈,艺术上也缺沉淀厚重、欠天真趣味。西方文化对力的崇尚、对人性的张扬固然有其美,但是,难以想象历史的高速公路上只有狂奔没有刹车的情景,难以想象世界处处是竞争冲突的张力而缺乏和谐、礼让的情景。达摩西来、鉴真东渡,东方文化终究是要度更多世人的。
夏老生于中国大陆,漂泊海峡、游历欧美五十多年,新世纪他随着内心简单却强烈召唤终于回归了家园。当然,他的艺术从来都是中国的,是东方的。他学艺于李仲生先生,李先生师承于日本现代艺术大师藤田嗣治,东方艺术的根系是一生创造的基础。不仅是精神气质,具体绘画语言也经常从中国绘画中寻找灵感。
夏老说,回到大陆,这一生感觉像倒吃甘蔗,越吃越甜。人生到了八十多岁,他脑子里却总萦绕着南京老家大宅子的模样——这里走出了夏仁溥、夏仁澍、夏仁析、夏仁师等文人士子,当然更有近代国学尊宿夏仁虎。只是,藏书楼的许多珍品还有自家刻的诗集雕版很多都毁于战火。夏老清楚地记得家里当时有一副对联,意境很近他堂婶林海音女士的作品: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栏杆倚处待得月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