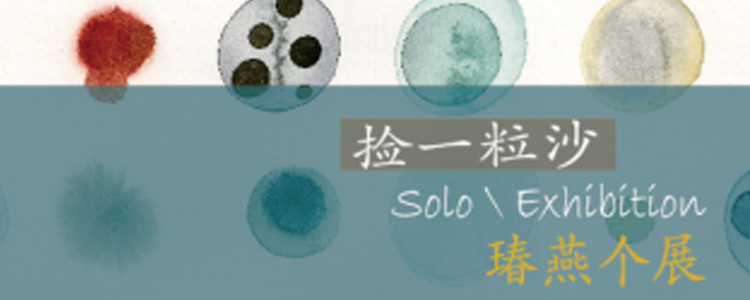
平淡之心
文\朱兴国
“回归本我自然,我再三创造”——《薄伽梵歌》
西方认知原理主要以视觉来感受世界,而中国文化则重意会而不可言传,以心来感知不可触及的无限虚空。于是“养心”一提再提,重建艺术游戏与修身的关系,可以塑造心性,从而改变生存质量,如同传统文人对诗意生活的陶冶和营造,也只有从修身实践与生活审美教化出发,才可能改变艺术对图像制作的依赖。现当代艺术要么过于观念化,没有心性的持久性,看不到凝想与内省的品质,而仅仅是观念的翻新;要么过于强调技术化的制作,没有亲近自然的怀抱,并不感人,更多的是挤压与宣泄。
瑃燕这个系列的作品,呈现出心性的平淡自然,材质媒介的日常性与呼吸性,迷人之处在于,不需要刻意经营,像念经书一样,与其说是创作生活,更像是一种修行——“它引领我进入一片纯净意识、纯粹感知的汪洋,但并不陌生,它就是我”,“感觉做事的喜悦增加了,直觉滋长,生命的欢愉愈加茂盛,负面能量则退却消散”。这种如同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体验,现代物理学称之为同统一场(Unified Field),越是往心性源头深处探究,就越有可能接近纯粹的至福(Bliss),积蓄的艺术修养因而漫漫显现,不再有迟疑或恐惧等诸多侵扰。“有时受到过去的折磨,有时又活在对明天的恐惧当中,绘画让我只是生活在现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能够专注而忘我,真正生活在现在,从中体会无常与无我,从而超越无常,进入无我。在明白生活的本质和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生活,看见希望,从这一点来说,绘画就是瑃燕抵达彼岸世界的方舟。
瑃燕平日里静静的,眼神怯怯的,说话弱弱的,画却尖锐。她画面中那一片优雅温暖的海面下隐匿着的孤独潮汐,会悄悄潜入你的心灵。她总喜欢把画面布置的满满的,以高度控制的色调、造型,丰富的意象以及浓稠的笔触,制造一片童话般的海岸来驱散现实世界的嘈杂。可是,画面越是热闹,越是能感受到孤独的深刻。画面因而变得充满力量,直指人心。毕加索的创造力体现在以暴力的形式调和情色的意图,八大山人以缄默的语言抑制内心的弥漫的温情。无论是瑃燕有意向她所仰慕的大师致敬还是内心需要的驱使,我相信,她的寻海之路一定越走越远。
——闫平、王克举
和许多年轻的艺术家不同,瑃燕从一开始就没有陷入单纯的图像表达与个人图像复制的泥潭。虽然她曾接受过系统的学院训练,但并没有沿着写实——再现的方向发展,也没有停留在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形式表层,她希望提炼自己的语言,形成个人化的风格,并与既有的绘画范式拉开距离。
——何桂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