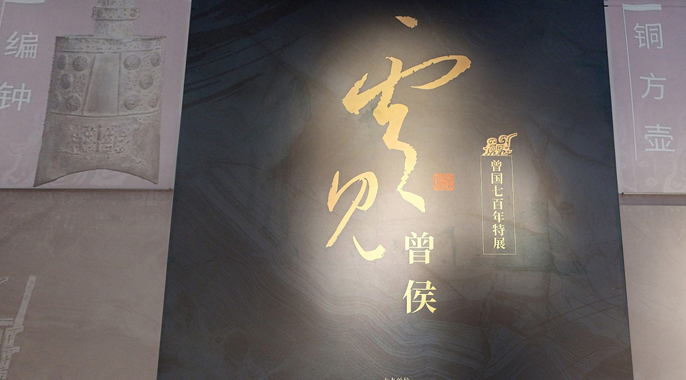继“这里发生了什么”影像档案馆开馆展之后,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推出了“地点上的时间”高世强个展和“没有世界观的面孔”董文胜个展。这两个个展试图将当代艺术最新的一些变化呈现给观众,即生于1970年代的艺术家开始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书写者:他们对媒介的使用更加宽泛,其中,影像和装置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语言方式;他们对历史开始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并流露出复杂矛盾的心态;他们不讳言自己对于传统的迷恋,并试图接续自身传统的文脉,这个传统包括古代的传统和现代的传统;他们以破坏旧的宏大叙事的自觉与勇气试图建立另一种想象之中的新的“宏大叙事”,并将承受其可能失败的命运;他们试图整合人文领域的各类知识,并对它们进行断片式的理解,呈现出某种独特的学者艺术家气质;对新价值的追索和确证充满热情等等。
高世强出生于1971年,现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1995年,高世强与陆磊、高士明组成了一个创作小组,展开了他们自称为“情境雕塑”的艺术实践。这一时期他们的作品与各种复杂的情境形成互文关系,被赋予了更多的心理的、社会的、以及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从而试图摆脱对观念性的过分依赖。1996年,他们以录像装置作品《可见与不可见的生活》参加“第一届中国录像艺术展”。几年后,高世强赴上海读研,直到2003年回到母校任教,开始独立工作的他与朋友陈晓云、陆磊、吴俊勇、孙逊、倪柯耘等一起开启了杭州影像运动,一个在今天看来极为罕见的群体性的“当代艺术运动”。同时,他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影像雕塑”阶段。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实验短片,基于美院的教育背景,这些作品与其说与实验电影史有关系,不如说它们是以当代艺术的方式被结构起来的,并在创作方式上呈现为一种“古典回归”。自2007年至今,高世强的创作进入到一个旺盛期,即第三个阶段,作品以电影为主。题材涉及古代传说在现代的变体(《十八相送》)、私人生活与历史记忆(《大桥》)、共运史的个人感怀 (《红》),以及剧场试验(《革命》)和具有人类学电影意味的试验(《晕氧》和《地点上的时间》)。在保持原有的实验性外,作品的形式向更传统的艺术电影回归,并呈现出某种精英主义倾向;在内容上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和体认较之同龄人显得更加广阔和复杂,并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高世强的作品摆脱了狭隘的意识形态纷争,折射出了后社会主义时代戏剧性的转变,即从国家与集体的综合体向以个人理念和目标为核心的空间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属于这一代人自身的传统和价值观被悄然塑造。
与高世强试图建构一个庞大的问题体系不同的是,出生于1970年的董文胜把目光聚焦于对江南美学的再发现。在我看来,这种再发现是对“后传统”社会中传统的认识与追怀,一定程度上是在进行某种意义的文化“复古”,从而避免一种陷于无望的“自我撕裂”。“江南”在当代艺术领域是一个看起来貌似地域性的课题,但它与中国传统文脉的联系最为直接,因此,它的价值和魅力愈来愈被重视中国精神传统的人们所关注。董文胜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都与他生活的江南小城常州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他的创作自由地穿梭于摄影、装置和实验电影之间,巧妙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如“园林”、“石头”、“刺青”、“骷髅”、“青苔”等等。从早期的后花园系列、静物系列一直到最近的以人体骨骼为主要媒材的系列摄影作品,他已经从对发生于特定情境中的神秘感、超现实性以及古怪的性活动的特别关注中走了出来,从而去思考更为抽象的问题,比如时间、存在、虚无等哲学问题。董文胜的实验短片则充分昭示了江南美学中阴柔的一面。作品《惊蛰》所流露出的对逝去传统的哀悼的情绪,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是受到了中国1930年代郁达夫小说中那些新旧交织的文人的苦闷心态的影响;而《梅雨》和《小暑》则是与性的初萌和生命的成长有关的两部短片,朴素的纪实镜头中充满了江南特有的濡湿诗意。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像作品《石沉记》几乎以自然主义的手法表达了传统文脉与当代社会全球化进程的纠缠,以及对现代化城市建设理念的对抗。值得一提的是,董文胜个展的名称“没有世界观的面孔”,出自于赵汀阳的著作《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在赵著中,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观的中国的“天下观念”被构建起来,这也正好暗合了董文胜企图建立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思想之上的新的价值观的抱负——这可能是这一代艺术家所苦苦追索的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