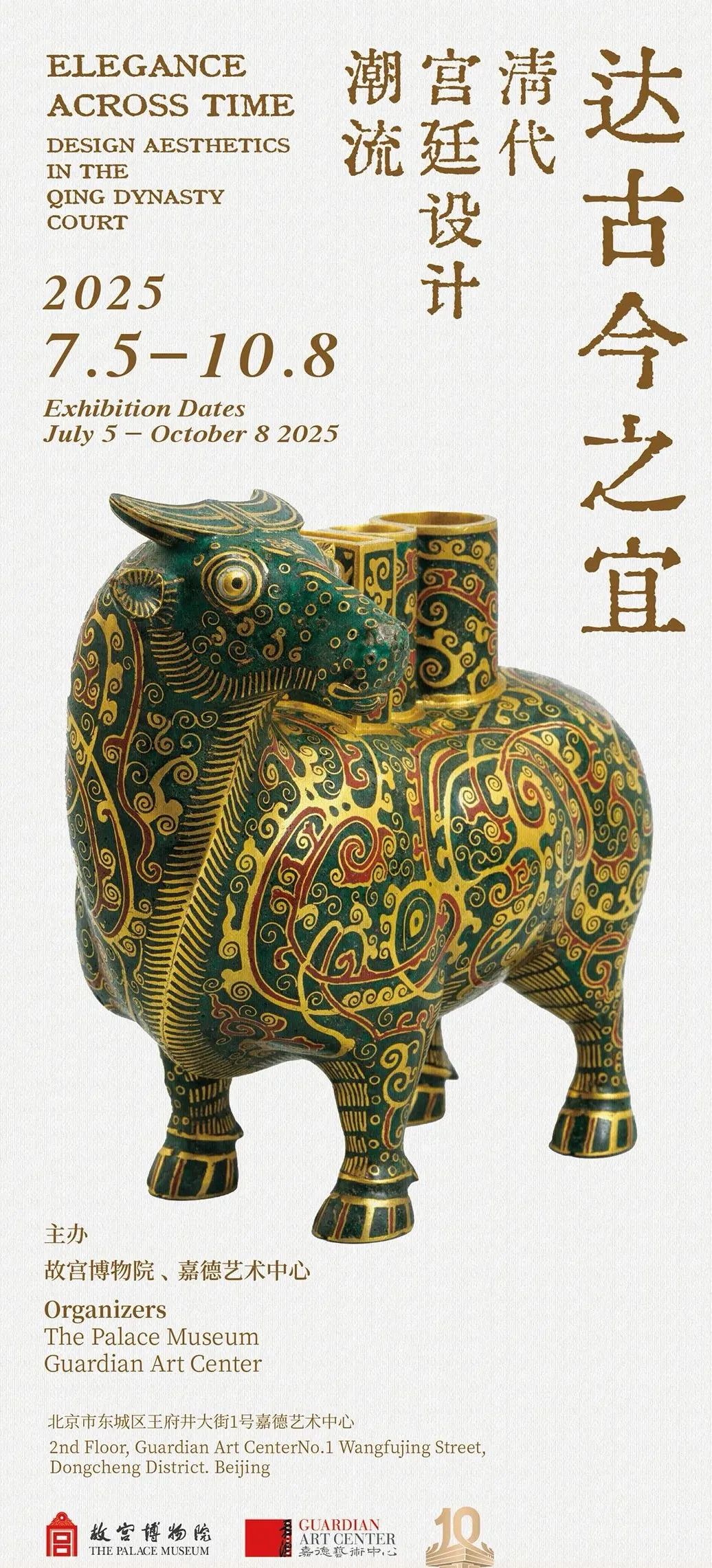前言:
文/李国华
当下,“身份”问题已经无法避免,它一会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闪现,一会又在我们身边悄然隐匿。当我们试图追逐它时,它又像一只被困的蝴蝶,停留在我们身后,但始终不能窥其全貌。正如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中篇小说《身份》描述的那样,“身份”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追寻——它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奇异荒野,时而像荒草丛中蜿蜒的小径,时而如同一面永远无法清晰反射的镜子。而这面镜子,正是我们的当代社会:一个超现实剧场中的倒影,它既真实又虚幻,既遥远又临近,它摧毁了我们固守的理性,迫使我们进入一种无法厘清的自我和他者的境地。
于是,当代艺术家们像是一个个永远无法找到自己归属的旅行者,漫游在无尽的迷雾中,追寻自我的“身份”,追寻一个似乎永远不可能到达的“自我”。他们的作品,在时代的冲刷下,“身份”也变得不再是固守的堡垒,而是充满张力与动荡的风暴中心,仿佛一场戏剧的上演,常常在我们意识的边缘闪烁,令人迷失又渴望接近。而这一切又涉及到种族、宗教、性别、国籍,因为进入工业社会后,人已经几乎不能脱离群体而生存——任何一种关于独一无二内在自我的叙述,都受到了来自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心理学的挑战。也因此,当今天的艺术家讨论身份问题时,通常都是讨论社会和文化,更为具体的是讨论在今天,作为个体的我到底是谁?在群体中,我们又是谁?我们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何工常年在国际间游走,他的作品仿佛是对当代艺术家,文化身份多元的艺术化呈现,当然他也试图揭示身份的多变与重叠。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几何化的艺术符号,让人看见了个体被现代社会碎片化信息的影响——那是一种无法被重新拼凑的断片,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和链接。何工的绘画也给我们呈现了一种极度张力的状态,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视觉冲击,正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身份焦虑的具象化;李勇政的艺术世界中,身份是一场永无止息的交锋,时而与他者亲密无间,时而又在一瞬间被抛弃和割裂。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人物的面部被模糊化处理,抽象与具象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他的绘画试图打破这种固有的界限,让“他者”与“自我”交织、重叠,无法被清晰分辨。
王彦鑫则通过其影像行为艺术,探索了具体历史语境变化下,身份的转折和剧烈的变动。在他的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在剧烈的历史、自然、人文情境变化中不断切换,反映了福山关于身份流动性的理论。他的作品也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身份标签中穿梭,并在这些角色之间建立起一种模糊的自我认知;林文通过对自我内心倒影的拆解,提出了“大荒漠”,这个提议类似哲学家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后续的困境:一旦镜像被破碎,个体如何在没有固定身份的状态下重新构建自我。
苍鑫将身体化作流动的文化场域,无论是中医的经脉,还是萨满的图腾,他试图用一种非常自我和偏僻的图像穿透日常生活,从而在现代性社会对个体身份意识造成的疼痛,进行仪式化的救赎。并且艺术家也以此追问:当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如同错位的穴位,是否还需要通过原始仪典来疏通被异化的精神经络?在科技祛魅的时代,艺术是否正在成为新的通灵术?
作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崔明明时常对他者眼中的自我产生质疑。她的装置作品《最终幻想》构建了一个关于身份、自由与存在的寓言。作品中的轿子既是物理空间的载体,也是精神困境的隐喻,折射出现代社会中女性身份的复杂处境。轿子也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它既是移动的家园,也是禁锢的枷锁。这种矛盾性恰如当代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身份困境。作品中的时间概念也值得关注,48小时的睡眠周期打破了自然的时间规律,暗示着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命节奏的强制干预。艺术家通过这些安排想要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于逃离,而在于在束缚中寻找自我,在规训中保持清醒;党蕊以肉身行走的方式,在西北的戈壁、河谷、白桦林等自然景观中穿行,这种身体与自然的对话,既是对个体生命经验的探索,也是对当代人精神身份多重性的诠释:《一路向西》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移动,更是精神层面的追寻。当然,她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浪潮中,如何保持个体与文化身份的独特性?因为这不仅是一次个人的精神之旅,更是对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的艺术回应。作品最终指向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精神家园的可能。
沈沐阳的绘画作品是一面折射文明进程的棱镜,在斑驳的颜料与肌理之间,隐藏着他对历史与身份的深刻思考。特别是在“文明往事”系列中,艺术家运用厚重的油彩堆积,创造出类似地质断层般的画面效果。这些层层叠叠的颜料肌理,仿佛是人类文明积淀的隐喻。画面中若隐若现的人形符号,在文明的褶皱中挣扎、变形,艺术家以此创造了一个虚假的历史情境,并以此暗示着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力;孟晓阳的创作聚焦于社会角色的扮演与转换。他的画面往往显得具有温情和回忆,但是人物似乎总是带着“面具”。他运用多层叠加的绘画技法,展现了个体在不同社会场景中的角色转换。画面中的人物戴着各式面具,这些面具既是保护,也是禁锢,揭示了社会规训对个体身份的塑造与扭曲。
朱小坤的“共生”系列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觉语言,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代人在多重身份中的生存状态。画面中纠缠的肢体、模糊的面容、交织的色彩,构成了一幅幅令人不安的身份图景,折射出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困境。这些人体共享着部分肢体,却朝向不同的方向挣扎。这种视觉隐喻暗示着当代人在社会角色、职业身份、家庭关系中的多重分裂。画面中的人物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抗,恰如现代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真实处境;
张钊瀛的绘画作品构建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视觉剧场,在这个剧场中,东西方美术史的经典符号被巧妙地拼贴重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跨文化对话。艺术家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元素并置,创造出一种时空错位的视觉效果,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艺术史叙事,也暗示了当代文化身份的混杂性。艺术家通过这种视觉策略,探讨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个体如何在多重文化影响中构建自我身份。在这个视觉剧场中,观众既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被邀请思考自身在文化交织中的位置与身份;明可的《三线记忆》穿梭于抽象与写实之间的视觉史诗,它以独特的艺术语言重构了三线建设时期的历史记忆。画面中,工厂的钢筋铁骨与朦胧的山水意象交织,既是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写实记录,也是对集体记忆的抽象提炼。它也展现了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的复杂关系:画面中若隐若现的形象,既是历史的缩影,也是艺术家自我投射的载体。这种处理方式打破了传统历史画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真实体验,以此让观者思考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
当我们站在这些艺术作品前时,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个体身份的倒影,而是整个时代的身份碎片。这些碎片不断被艺术家们拼接、重组,既暴露出身份的脆弱,也揭示了身份背后的巨大张力。身份的塑造和重构永远是一场永无止息的斗争,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斗争中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超现实剧场成为了这一斗争的舞台,而自我倒影则是这场戏剧的核心。在这面镜子中,我们无法看到自己真正的面目,因为那面镜子永远模糊、变幻。身份的"临近"与"疏远"交织,成为了无法逃脱的命运。正如拉康和齐泽克所揭示的,我们的身份不仅仅是自我认同的构建,更是外部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的重构。在这些艺术作品中,身份如同一个不断变动的影像,永远在临近与远离之间,无法触及,也无法逃脱。
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身份不仅仅是私人内心的挣扎,它同样受制于全球政治、文化冲突、社会阶层等外部力量的交织与操控。在全球化、数字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不得不在多重身份中寻找平衡,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困境。艺术家通过画笔,将这种困境转化为震撼人心的视觉图景。在超现实主义的剧场中,身份成为了一种流动的、可塑的存在。画面中扭曲的镜像、错位的空间、断裂的肢体,都是对身份不确定性的隐喻。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身份的流动性,更揭示了我们在寻找自我过程中的焦虑与困惑。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身份的"临近"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威胁。我们渴望接近真实的自我,却又害怕直面内心的虚无。艺术家的作品正是对这种矛盾的深刻洞察,它们提醒我们:身份的建构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是演员,也是观众,在超现实的剧场中不断寻找那个永远无法完全捕捉的自我倒影。